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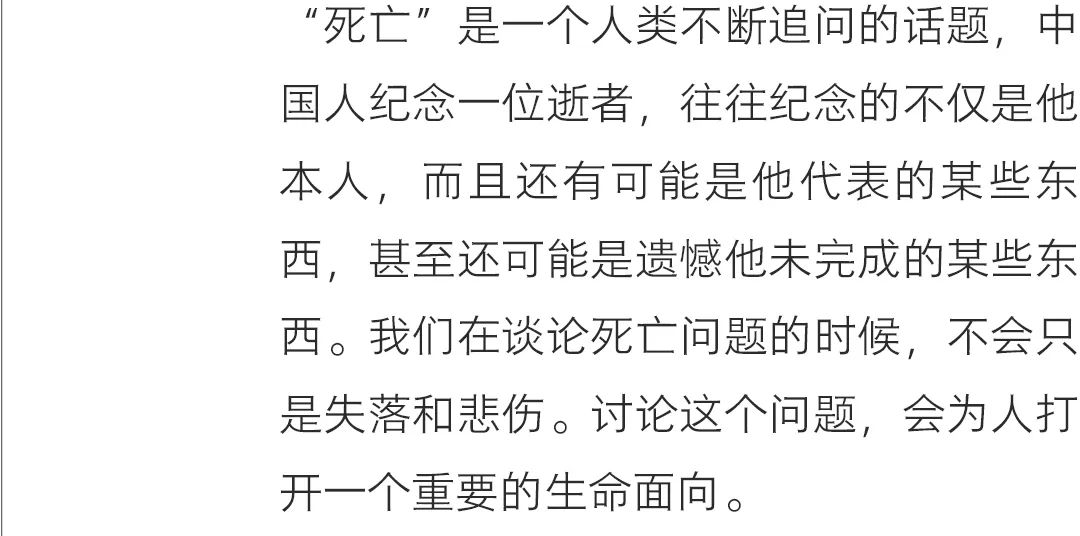
分 享 | 袁长庚 人类学家、南方科技大学助理教授
“孤老终身、突发心血管疾病、艾滋病、飞机在万米之上解体,死于空难”,2017年至2021年,袁长庚在南方科技大学开设了“理解死亡”的课程。他常常在课堂上提出一个问题:“你更愿意以上述哪种方式死去?”很多学生都选择了最后一项——死于空难。学生的解释是:希望自己不要承受长期病痛折磨,也不要和其他人有什么牵扯,最好就像烟花一样消失。“但是,如果‘死亡’真的就只是最后一刻肉身离开的问题,那根本没有必要多做讨论”,袁长庚说。
“死亡”之所以是人类不断追问的话题,是因为它直接关系到生者的价值体系,其中包括,一个人将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以及他(她)对亲密关系的构建与想象。对选择“死于空难”的学生,袁长庚常常会提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父母亲将如何面对这件事?”
4年间,“死亡课”影响了很多学生,甚至改变了一些人的人生重大抉择。袁长庚也从学生身上感知到了时代的脉搏:这些学生都是各省高考中排名前1%的佼佼者。要在高考的游戏中胜出,凭借的不仅是智商,而需要整体人格状态都高度匹配社会的赋值体系。在这种赋值体系的要求下,人们正在逐渐把自己从人群中割裂出去,并把“死亡”问题排除在生活之外。这一过程看似是排除了干扰,让他们毫无牵绊地奔着绩效而去,但巨大的危机正潜伏于此:人关闭了一个让自己反思 “如何配置自己的生活”以及“何为亲密关系”的窗口。社会正加速造就一批“单向度的人”。
“85后”石慧的工作就是具体地处理死亡问题。2012年进入殡葬行业之前,她是一名外企职员。2018年,石慧与朋友共同创办了摆渡人殡葬服务公司。在外人看来,殡葬行业充满阴郁,也有些神秘,但石慧说,每天与死亡打交道,这个行业的人恰恰会更乐观,更看得开。她对生命的感触、对死亡与仪式之间勾连的观察,也在工作中不断累进。
石慧:其实我不喜欢刚刚谈到的“强人”这个词。对我们殡葬人来说,逝者都是平等的,一个拾荒者与一个高官巨富,在死亡的时候都需要有最体面的告别,这是我们的责任。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也是如此,中国人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俗话说就是,“儿子看老子怎么敬老子,以后他们也会知道怎么敬自己的老子”。处理死亡,不是讲大道理,是一个在日常生活中的教化过程。从这一点上说,哪怕是一个从来没有工作过,也没有社交的人,他也可能给家人留下很大一笔人生财富,这样的人,在盖棺论定的时候,也是非常值得被珍视的。当然,所谓“强人”,他们的身后事可能会更复杂一点,有时候也会特别现实。在我处理过的企业家的葬礼中,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位人缘很好,也很受尊敬的企业家。这位企业家在公司有非常高的地位,权力很大,工作压力也很大,带的团队很多。当时,他的两个下属找到我,希望我们来操办他的葬礼。在准备材料的时候,我就请他们回忆企业家生前的事情,比如,他有什么缺点和毛病?在我想象中,很多位高权重的人会脾气比较爆,或者强势。但在两个小时的讲述中,两个大男人始终不停地擦眼泪,对我说了很多企业家生前的很多生活细节,比如,他总是力所能及地去帮助下属,对待下属亦师亦友,也从来没有发过火等等。最后,他们郑重拜托我们,一定要好好为他办一场追思会。听他们说完这些,我也很受触动。我能感受到,他的两位下属真的不是在乎他留下来的东西,或者在乎利益的人,纯粹是感激这位去世的企业家为他们带来的精神传承。我还记得其中一位对我说的一句话:“我现在就奔着让公司上市的目标去,我一定会做到,等上市那一天,我会再去他墓前好好祭拜他。”另一个我印象很深的是一场生前追思会。我们服务的是一位59岁的女老板,因为罹患胰腺癌,只有3个月到6个月的寿命了。她来请我们办一场生前追思会,以此与世界作别。她没有孩子、没有家庭,留下了大量的财富。在她人生末尾,她最想做的事情其实就是缓解之前和家人的矛盾,可能因为她的性格太强势了,觉得别人都应该听她的,导致亲戚朋友都对她有很多抱怨。虽然,她不吝惜为家族付出,但因为性格原因,她也会对亲戚造成伤害。后来,我们就以“家庭暖心会”的名义操办这场生前追思会。在会上,她状态特别好,她很爱美,准备了5套礼服,浓妆艳抹,还特地嘱咐我们:每一件都要穿。她说,她希望给亲人留下最好的样子,而不是没有头发的、化疗后虚弱的样子。整场追思会,我一直陪在她身边,她其实人都有点站不住了,需要我扶着她,她有时候会紧紧捏着我的胳膊,其实就是在借力,寻找身体的支撑。我们当时设计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以她与家人的矛盾点作为切口,让她与家人一次次化解怨气。这场追思会以后,她与几位亲戚就相互抱在一起,在会场中央痛哭流涕。大家也给她很多祝福和叮咛。暖心会以后,她对我说,她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她会走的特别、特别坦然。她还向我指定了她离开世界时候要穿的一件衣服。那是一件非常漂亮的露肩礼服。但我也看到过很多令人遗憾的事情。比如,虽然中国是“一夫一妻制”,但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越有钱的人,情人越是多。逝者走后,矛盾就层出不穷。在追悼会现场,也经常会发生吵架、抢家产之类的事情。还有人是出于对逝者的真爱,比如,要求我们背着妻子给他们一些骨灰。这时候其实对我们是一种很大的考验。在我看来,“强人”离世,分两种,一种是“家人为家人办葬礼”,一种是“家人为逝者办葬礼”。今天来参加闭门会议的,也有创业者或高管,这里我也想做一些忠告:人要在活着的时候多行好事,不要斤斤计较。因为,当你走的那一刻,很多东西其实不重要。现在想的赚钱、上市,真的到了躺在床上不能动的时候,都是芝麻绿豆大的事。最后阶段,人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活着,哪怕放弃我的公司,都完全没问题。这是非常真实的事情。如果一个“强人”生前很好地对待周遭的人,那最后一刻,人们会真心地向他告别。如果一个人生前在乎太多现实利益,那么周围的人肯定也都会有私心,都会要去抓住当下对他最重要的利益。袁长庚:中国人避讳谈及死亡,认为这是阴郁的、不吉利的事情。其实,我们对人的想象太过单一了。我们在谈论死亡问题的时候,不会只是失落和悲伤。讨论这个问题,会为人打开一个重要的生命面向。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有一个巨大的变化是,我们的社会已经成功地把“死亡”从生活景观中剔除出去了。仔细想来,1949年以后,我们日常生活中关于死亡的景观越来越少,人们也很少公开谈论死亡。从绩效的角度说,“死亡”是一种“污染”,一种异常状态,越早走出去越好,而停留在这个精神状态的时间太长,会被认为是一种懈怠,一种消耗。所以我们整个一套制度设计,就是把死亡尽可能排除在日常生活之外,快节奏地去处理。作为人文学者,我其实是很难相信一套进步主义的价值观的。明天并不一定会更好,如果你读历史的话,就会知道,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没办法保证子孙一定会比自己幸福。我觉得用40年时间来发展,接下来,可能要用更长的时间来处理发展遗留下来的问题,其中就包括,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非常粗率的、没有得出基本共识的事情。在城市里,我们把时间都花在了建设、挣钱上,或者用在单纯的享受生活上,却很少花时间来处理死亡。我观察到,很多家庭中的告别显得多少有些仓促和狼狈。这其实与购买力无关,纯粹是城市相对缺乏这样的支撑体系,整个社会还没有做好处理死亡的准备。在农村,红白喜事都是一个需要很大的人际网络支撑的事情。打个很简单的比方,在我老家山东农村,一副棺材300多斤,需要6个壮年男子抬着放到很深的大坑之中,也就是说,村里办丧事,至少需要找到6个青年男子。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细节。但现在返乡的年轻人可以说大部分是不懂得传统那套步骤的,也找不到很多人来帮忙。城市化的过程,把很多人际关系斩断了。当然,一个人有权利选择不与整个世界有太多牵绊,可以选择不结婚,没朋友,或者任何生活风格,但一个全世界公认的事情是,良性的社会支撑对一个人的福祉是非常重要的,没有任何人可以特立独行,没有任何人辅助而过好一生。我感觉,这些年,中国人开始重新学习跟死亡有关的知识。很多人都觉察到这个问题的空白,开始缓慢地重建。我自己还是有些信心,认为这个过程会持续下去。这也需要很多殡葬人的力量加入进来,处理具体的、技术性的问题。石慧:死亡的仪式在不断简化,死亡也成了一个越来越私密的事情。其中的原因,可能就是袁老师说的,生者不愿意讨论死亡,把这个问题封闭了起来。我们一生都很少有机会去想:我想要一个怎样的葬礼,我希望哪些人来送我最后一程?但其实这是一个应该经常思考的问题。现在,很多人的追悼会只邀请最亲密的朋友,一般的朋友连报丧都不会报。反而,这时候,在上海郊区,人与人的亲密感就出来了,村子里的人会想要在一起,好好送逝者走完最后一程。但在市区,上海的丧假也只有三天,通常是第三天开追悼会。整个过程非常快,作为家属,人的脑子是混乱的,懵的,反应不过来。往往人们是在追悼会结束,回到家里,看到长辈留下的衣服、生前用过的东西,那上面还保留着他的气息,这时候亲属才开始抱头痛哭。袁长庚:如果把组织比喻为一个生命体的话,他们的共同点可能就是:看很多实验室对死者的病理解剖,最终置人于死地的原因很多时候不是这个人生前最严重的疾病,而是一个他自己都不怎么知道的病。比如,一个癌症病人死于心血管疾病,他生前并不知道自己有这方面的问题,这个人就等于是一直怀揣一颗炸药,很长时间里没有爆炸而已。我为什么讲这个呢?我们应该了解人的脆弱性,人生本来就是无常的,你不应该完全总用一种秩序为基础去理解生命。从哲学的角度来说,无常本身就是人存在的基本状态。但在目前的组织管理学中,我们做的很多假设,都建立在有常的秩序之上,排除了一切无常。近几年,因为各地疫情,很多企业没有挺过寒冬,如果仔细探究,就会发现,这些公司的资金都在比较吃紧的状态,刚刚好维持平衡。当然从经济上盘算,不要把太多资金压在手里,是一种商业智慧。但这其实是一种非常荒诞的状态:是谁告诉你,一个企业可以长期在临界点上行走呢?另外,历史上很多王朝灭亡,导致溃散的原因非常小。一个人的死因也是如此。如果你的整个思考架构里,没有无常,你根本就不可能理解,最后这股毁灭性的力量打哪儿来?现在很多企业都讲“正能量”,我恰恰觉得,在培训中,适当引入“负能量”很重要。要做好面对“死亡”和“失败”的准备,这其实是在提高组织的韧性。这就像人一样,你现在去看很多优秀的年轻人,表面意气风发,但其实内心都有遗憾,都有没处理好的事情,都有一笔债。这些东西如果不处理、不面对的话,肯定会在将来某一刻爆发。一个人在20多岁因为意外崩溃,还能从头再来,如果50岁被击溃,那就真的很难了。也是从这一点来说,死亡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死亡总会站在人类想象的对立面,去提一些我们没有计划和准备的挑战。灾难和失败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关键是我们以什么方式去应对。在极端的情况下,是什么在支撑家庭?什么在支撑社会?我们有没有把这段经历作为一种最基本的生命体验给予保留。在我看来,上海是中国近代史上,经历最丰富的城市,也是最深刻实现了现代意义上的“世俗社会”的城市。上海在民国时期有一个“马照跑、舞照跳”的景象。这恰恰是上海丰富性的体现。上海是近代中国的资本之都,同时是左翼文艺之都。很少有城市培养出上海这样的市民社会的品格,它始终保持着对生活基本面向的尊重。上海很珍贵的一面就是张爱玲所说的“人间烟火气”。从“人间烟火气”这个角度来说,4月份以来的经历对上海是一个伤害。我做人类学研究,比较敏感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和智慧就像沼泽和蓄水池,外部的海浪冲击过来以后,落到每个人身上没有那么疼。一些上海朋友告诉我,他们家里没有做饭的锅,饭菜都是靠外卖。这意味着他们是没有生活的。在我看来,生活就是一整套劳作,不是完全的等价交换过程。生活的框架要自己搭建,过程要自己做。现在我们生活的质感,包括从这种质感上得到的对生活的感受都很稀薄。石慧:我很喜欢任正非,他是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他说过,冬天是可爱的,不是可怕的,如果你没有面对过一个冬天,总是飘飘然,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死”这件事情,如果我们经常去面对它,理解它,最终就能超越它。袁长庚:不要觉得死亡问题就是我们几个“老僧”坐而论道。理解死亡,处理死亡,需要做很多具体的事。如果家里很美满,没有死亡事件,可以去做志愿者。很多东西亲自操办过了,会有不同的感受。我推荐一本书,叫《好好告别》,作者在丧葬行业工作过,讲述了过程中许多非常复杂的体验。人在真正靠近死亡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在“理解死亡”这门课上,我会要求学生排练一个有关死亡的剧,要他们自己写剧本,准备道具。我的很多学生是在这个准备过程中才明白,在一个人躺进棺材之前,家人需要考虑到那么多的细节,这远远比他们原本想的要复杂得多。我们的父母总是抱怨孩子,不知感恩、自私,但人的品质不是天生的,是一个演习的结果,如果他们从小都不经历具体的事情,怎么会知道如何感恩呢?还有一点有关仪式的想法是,中国人对他人的讲述和坦白都太少了。我觉得,现在即便是社会精英,他们在死去之后也享受不到周围的人对他比较完整的讲述。这种讲述可以包括,他从哪儿来,他做了什么,有没有有血有肉的场景等等。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周围人能不能回忆起他一生中非常了不起的时刻?这些东西,在丧葬文化中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要用语言表述,创造一个场景,让大家进入这个人的生命过程当中。现在的葬礼,都太仓促,环节也很少。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是在遵循一些既定的东西,会有领导讲话,但很少有家属、孩子或者朋友仔细回忆逝者是个什么样的人。石慧:一个完整的仪式是非常重要的,对生者来说,这是一个接受亲人离去,寄托和放下的过程。我们在实操当中发现,在很多家庭,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遗像”。在送别亲人的时候,大家一般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好好选一张符合逝者性格的照片。所以,我们会交代家属:现在有时间,在病床边上一定要翻一下照片,不要去选身份证照,选一张活生生的照片。如果这个人爱笑,就选择一张笑得灿烂的照片;如果他喜欢旅游,那完全可以选择他在一个旅游目的地拍下的照片。在工作中,我也发现,目前殡葬行业存在一些乱象,比如,从业者不希望家属设灵堂,这其实是因为设灵堂对他们来说很辛苦,利润率却不高。在整个设灵堂的过程中,香不能断,蜡烛不能灭,家属需要全程陪伴。但我们会要求家属设灵堂,因为这是一个守孝的过程,是一个报恩的过程,也是逐渐感知亲人离去的过程。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这些传统在很大程度上丢失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很多人在处理死亡问题上,会回避孩子,担心他们受到创伤。但我要求一线工作人员一定要提醒家属:让孩子参与葬礼。孩子年龄再小,他们也有感知,对如何送走亲人,他们脑子里是有萌芽的,他们会记住自己如何送别了亲人。事实上,孩子没我们想象中那么脆弱,而是特别勇敢。我看到几乎所有孩子到了仪式当中,都是不会吵闹的,他们能感知到外界在发生什么,他们会安安静静地看着整个过程。参与整个仪式,这对他们很重要。我们新殡葬人对于仪式,会比20年前更加在乎和重视逝者的尊严。即便如此,我们的殡葬仪式还是要比日本、中国台湾落后至少10年。我本人进入殡葬行业10年,看到互联网给殡葬带来的改变。以前中国人忌讳谈论“死亡”,只有从医院这个渠道才能了解如何处理“身后事”。有了互联网之后,各个平台和渠道,人们就知道先打电话做咨询。很多人会提前做好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