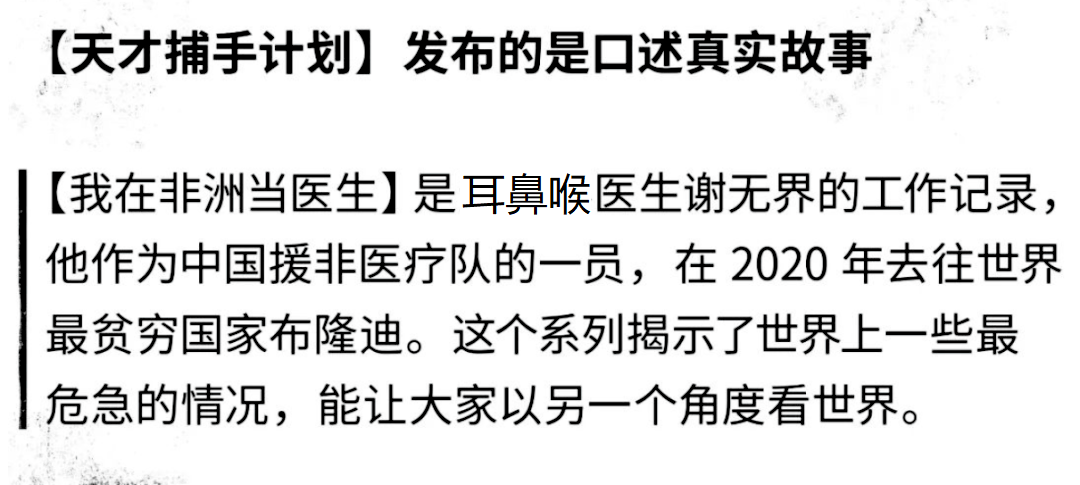
大家好,我是陈拙。
今天学到一个冷知识,它能在灾难意外面前,帮你迅速判断自己还有多久能得救。
在所有大型灾难现场,所有伤员都会被分配不同颜色的丝带。
如果被分配为绿色和黄色,代表没有危及生命,不需要为自己担心;
但如果拿到红色丝带,代表着有生命危险,会被第一时间抢救。
援非医生谢无界在两周前,见到了一种特殊颜色的丝带——
他因此在非洲这个大陆上,见到了一种最恐怖的伤痕,也必须以医生的身份做出最艰难的抉择。
同时也因为这种颜色的丝带,他得以结识一位最值得敬佩的本地医生。

从诊室的窗户看出去,我时不时会被一望无际的非洲大陆惊到,接着就会想到,我的父母、妻子、女儿,都在距离这里八千多公里的另一片大陆上。
援非的日子是孤独的,我所在的诊室只有我一名医生。有回我用注射器的针头自制出了一把叮咛钩,很得意,但是想到要炫耀给护士得翻译成法语,又觉得算了。每天饭点对我来说都很重要,医疗队队友们会齐聚在食堂,只有在这个时间,我们可以尽情地说中文,聊自己的故乡,也抱怨医院里的事。那天,我刚走进食堂,就发现氛围不太对。队友们边吃饭边聊着什么,眉头紧锁,怒气冲冲。我坐下后不久,妇产科的中国医生也来了,她手里没端饭,却提着一袋奶粉,站在门口墙边默默地抹眼泪。我听了一会才知道,她带的奶粉是自费买给一个小病人的。有个5岁的孩子被送到我们医院,整个人瘦得皮包骨头,嘴边都是烂疮,绿头苍蝇一直在他脸上盘旋。非洲医院缺医少药,很多检查都做不了,我们无法判断孩子的病因,只知道目前有重度营养不良、重度贫血。中国医生建议先给输血和深静脉营养,恢复起来再试探下一步治疗。结果这个方子被穆邦达省医院的外科主任盖伊医生一票否决。在他的授意下,医院仅进行了最保守的静脉补液治疗。3天后,孩子不治死亡。亲手抱过那孩子的中国医生一直在哭,其他医生也义愤填膺,指责那个盖伊医生是杀人凶手,边说边把手机里孩子生前的照片递到我眼前。 孩子的照片
孩子的照片
我不知道要说什么。就在走进食堂前一分钟,我还以为,穆邦达省医院的盖伊医生,是我在这片大陆上难得的志同道合的朋友。我还记得,在医院门口他叫住我,笑着自我介绍说,他就是盖伊。他跟我身材相仿,挺胖,但那天他还穿了一件绷得紧紧的墨绿色T恤,T恤背后用闷骚的桃粉色写着一行英文:我们曾经一起抢救病人,一起躲在走廊抽烟,吐槽看不惯的领导,他帮我撑腰。我以为我们是朋友,但到这时候我才发现,了解一个人,不是那么简单。在初来乍到的两周里,盖伊一直都是我们饭桌上的热门话题。院长曾经在欢迎仪式上花了半小时向我们炫耀,这是一位“全科医生”,“从妇产科的剖腹产手术到骨科的常规手术,包括耳鼻喉科的内镜手术,甚至彩超、CT相关辅助科室的工作,没有他不会的”。外科的队友说,每天早上他们做手术前,这位盖伊医生都会出现在手术室里,核查病人的基本信息、手术术式等。这本来是麻醉科主任的活儿,盖伊是自行加了一道检查,只针对中国医生。有时候我们排的手术多,他来不及检查完,甚至会强硬地推后乃至停掉部分手术。病人病情危急,术前还会做很多准备来调整身体以备手术,他说停就停了,耽误治疗怎么办?有时候中国医生在做手术,盖伊还会专门进来检查,碰到我们缝合做得比较慢,他就会边摇头边叹气地走开,但又不说你做错了什么。作为小专科医生的我,本来没有什么机会被盖伊“监考”。但有天上午,我正在看诊,突然被一名护士叫下了楼。护士把我带到了急诊区,一个孩子正在嚎啕大哭。孩子左侧脸颊上有一道血淋淋的伤口,从头皮撕裂至脸颊,孩子母亲正徒劳地试图用纱布堵住汩汩流出的鲜血。护士告诉我,她们找不到急诊科的医生了,所以只能来找我。我的火噌就起来了。这样的事不是一次两次,自从我们来了,本地的急诊科医生时不时就会溜号,任由护士找不到人,最终来求助中国医生。我们都有自己的活儿,也不一定会做急诊的手术,但要是不来,他们就敢让病人在急诊一直等着,从早等到晚。我们也知道,治这帮家伙唯一的办法就是坚决拒绝。但眼看着鲜血顺着孩子的下颌滴落在地板上,我再一次心软了。我赶紧给孩子做了简单的包扎,让我的学生带着家属及患儿去拍头颅CT,护士准备全麻清创缝合手术。趁着他们离开,我跑回诊室,花了一个多小时看完了正在排队的病人们,估计CT该做完了,又跑回来。我心里祈祷学生别坑我。也不是一次两次,我回来时会发现病人还坐在原地,学生已经躲到了某处摸鱼。但这次,护士却告诉我,患者已经做完头颅CT,甚至进了手术室有20分钟了。怎么这么快?我匆匆推开手术室的门,却在手术室里看见了一个一身白大褂的人。
抢病人在医生之间是挺不友好的行为,何况又是大名鼎鼎的盖伊。我想起队友们的抱怨,心里难免有点不舒服。但盖伊开口就是一顿彩虹屁:“很漂亮的判断,我和您想的一样,也是要在全麻下行清创缝合。”我准备全麻是为了防止缝合中孩子疼痛挣扎,造成伤口缝不好二次感染,是一种比较费事的方案,没想到盖伊竟然所见略同。我不愿意就这么走了,也好奇传说中的盖伊做手术究竟如何,干脆把手术助理赶了下来,自己戴上手套给盖伊做助理。一上台我就发现了个很恐怖的事情,孩子打了全麻,却没有插管,只扣了个面罩!病人打了麻醉后,负责呼吸的肌肉可能也会被抑制,如果不插管进行辅助呼吸的话,孩子很容易窒息。我慌忙问麻醉师怎么回事,麻醉师根本没理我。他在用听诊器监听孩子的心跳,因为这里没有监护仪。盖伊叹了口气,在一旁回答:“开台才9分钟,一个很小的手术,我保证在20分钟内完成。”速战速决,窒息的风险就不那么大。但他还是听劝地让护士手动测一下孩子的氧饱(血氧饱和度),一测,89%。就在这时,麻醉师突然举手示意所有人安静,突然,他把手中的听诊器往旁边一扔,开始给孩子做胸外按压。孩子心脏停跳了!不知道是因为窒息还是麻醉过量,总之就是停跳了,就因为一个小小的清创缝合手术!我还处于惊呆的状态,盖伊已经迅速从护士手中接过复苏球囊,一下一下地往孩子口中泵入氧气。一下、两下,两分多钟后,麻醉师的表情放松下来。孩子的心跳恢复了。整整三分钟的抢救,我竟然什么都没来得及做,只是看着盖伊忙乎。从头皮发麻的紧张中回过神来,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问责盖伊:“你怎么敢在别人孩子的身上这么做?”心脏停跳,有一半的可能就是因为他没有插管导致的窒息。盖伊头也没抬,好像没听见一样,已经开始默默地缝合伤口。麻醉师替盖伊解释:“病人家里很穷,盖伊老师想给病人省钱。”我也碰到过类似不得不压缩手术条件、冒险为病人省钱的情况,可是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敢这么做。因为钱省在别人兜里,手术出事风险却在医生身上。这是我的病人,甚至没有人告诉我这个病人如何强烈要求不插管,盖伊什么时候下了这个决定?
手术室里安静了一会,盖伊突然开口问我:“为什么这个小手术,你要选择全麻?”
盖伊的反应竟然是笑了:“瘢痕?哪有愈合不要瘢痕的?瘢痕就是告诉这个孩子,下次坐车时该牢牢地抓住骑车的人。”护士告诉过我,这个男孩受伤是因为从自行车后座跌落,脸着地。盖伊手上正缝到孩子的面颊,我拦住了他,接过他手中的线,小心翼翼地开始使用小针做减张缝合。盖伊默默地看着,7厘米的伤口我足足操作了30分钟,他没有再因为我的动作慢而发出叹气声。伤口缝完后,只留下了一条细细的红痕。我炫耀地对盖伊说,没见过这么缝的吗?盖伊说他会这种缝合,但接着他又神情莫测地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说:“不愧是中国医生,可以不计成本地去救治每一位病人。”我弄不明白盖伊这句话是夸是贬,可他已经扭头离开了手术室。我脱下手术服,正在擦汗,盖伊突然杀了个回马枪,看着我认真地说,20分钟是足够的。我回想了一下,确实,按他的缝针方法,20分钟足够了,如果没有意外,孩子确实不用插管。盖伊的心里好像有一把精确到毫克的秤,谁对谁错,一场手术花多少成本,都要放上去称一称。缝合时,我跟他提起了急诊科医生擅离职守的问题。我心想作为外科主任,他应该有权限治一治这帮人。我瞪大了眼,他继续说,如果你们医疗队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就举报或者制止,情况会演变成这样吗?我想说你是没看见孩子的样子,但盖伊没等我回嘴就说了,当然问题更大的是急诊科医生,他会去处理他们的。那天之后,急诊科溜号的现象一夜之间消失了。队友们摸不着头脑,我也没有说我和盖伊医生的对话。这成了我俩的一个秘密。盖伊工作的地方在东楼,我在主楼。每天早上,非洲医生们参与升旗仪式,我跑步路过时,会和盖伊打个招呼。有时候上班,我还会留意一下医院门口有没有他妻子的摊位。盖伊的妻子在医院门口摆摊,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盖伊时发现的。其实在合作手术之前,我们就见过一次。那天早上我去街上打牛奶,突然被一个黑人叫住。对方问我是不是援非医生,热情地自我介绍说,他就是盖伊。通勤车停在他背后,他刚从车上下来,跟我打完招呼,转身去接后面的人下车。她太瘦了。裸露在外的双臂没有丁点脂肪,眼窝深深凹陷着。盖伊很简单地介绍了一句“这是我妻子”,忙着搀扶住这个女人。他双手紧紧握着女人的胳膊,眼睛替女人看着脚下的路,神情无比耐心。夫妻俩在医院门口行了贴面礼告别,盖伊走进医院上班,而女人则慢悠悠地坐到了树荫下,摊开了一块花布,上面有做好的麻绳和做麻绳的材料。那时候我很困惑,在非洲,大部分有地位的女性都比较忌讳出门,以盖伊医生的收入,即使孩子大了,应该也不至于让妻子在街上摆摊。我心里闪过一丝不对劲,但还没有好奇到上前追问。只是跟着走进了医院,开始了又一天的工作。
盖伊工作的地方在东楼,我在主楼。每天早上,非洲医生们升国旗,我跑步路过时,会和盖伊打个招呼。有时候上班,我还会留意一下他妻子有没有在医院门口摆摊。
在我耳边吐槽盖伊的人,从队友换成了学生。学生们不肯从我这轮转去他的科室,说他太凶了,没有教学,做错了就骂,去他那什么也学不到。按照我的性格,其实多带一波学生也没什么,但想起盖伊又要板着脸说“你们也有责任”,我又觉得有些脸热。学生不轮转走,该跟盖伊学的东西学不到,对他们肯定不是好事。我狠下心,直接拿起学生的书包塞进他们怀里,把他们推出了门。门外一直喧闹,我等了半天不见平息,才发现吵嚷的不是被我赶走的学生,而是急诊科。我出去看热闹,才知道医院刚刚收治了一名大官,病症是头晕呕吐。就我看热闹的这8分钟,人已经吐了4次了。私人医院诊断为脑血管意外,怀疑小脑梗死,送来我们这里拍了个CT,正打算送去比利时医院进一步检查;还有人收集了他的呕吐物要送去警察局和检验中心,害怕是下毒,据说官员昨天吃饭的餐厅,负责人已经被控制起来了。同事补充了一个细节,要不是这位官员家的私人CT机恰巧坏了,人家本来都不会来我们这拍片子。一动就吐,这个症状听起来好耳熟,不是我们耳鼻喉科的耳石症吗?我拨开人群想上前给病人查体,但官员的随行人员立马拦住了我。我眼尖地发现盖伊也在转运车上,立马扬声冲他喊:“盖伊!这是耳石症!”盖伊看了我一眼,院长已经把我推开,抬着担架就要上转运车。我有点恼火,提醒道,耳石症最怕颠簸,比利时医院离这里100千米,“你们是要他的命?”我大摇大摆地回了诊室。过了一会,援非医疗队的队长跑来问我说话到底有没有把握。我还想问他怎么会说出这种话,队长转而暗示我,官员转走了没关系,要是在我手上治出个什么好歹,那就是外交事件,“外交无小事”。我立马举起双手宣布,我的诊断可能是错的,赶紧让官员去更好的医院吧。没想到盖伊没搭理我,径直在我对面坐下,压低声音说,现在病人在补液,“我们有5分钟的病例讨论时间”。几个问题之后,盖伊迅速认可了我的判断,站起身打开门,向我做了一个“请”的手势:“不是总抱怨我抢了你的病人吗?这次,我还你一个。”
治疗如我所料的不顺利。病人情况比较严重,一碰就吐,一吐脑袋就会动,耳石就又飘回去了,治疗迟迟没有进展。
耳石复位不用器械,不开刀、不拍片,就是扶着病人的脑袋转来转去,看起来很像跳大神。我感觉到周围的目光越来越不信任。如果在平时,我可能会缓一缓,让病人先住上院,等到第二天或者他不是特别难受时候再复位。但想到这位官员的地位,我根本没有退路。就在我无从下手时,盖伊俯下身,在官员耳边耳语了几句。不知道他说了什么魔咒,奇迹发生了。在接下来的诊断、复位,整个过程中,官员竟然真的忍住了没有动,甚至连手都没抬一下。我舒了一口气,突然发现身上的衣服全都被汗湿了。不得不承认,我紧张了,因为这个官员的身份。各种语言的感谢、道贺声传入我的耳朵。随行人员几乎是一窝蜂地冲上来,一拨感谢我,一拨拥向院长,赞美他的果断决策。没想到,盖伊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溜到了吸烟点,正抽着自己用烟丝卷的香烟。
他示意帮我做一根,我知道他们卷烟会用舌头封口,连忙拒绝了,蹩脚地自己学着做了一根。生烟不好抽,直咳嗽。盖伊看着我笑,问我为什么不去合影,“中国医生不是很喜欢拍照留念吗?”像往常一样,盖伊先叹了口气,接着说,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眼前的这个中国医生,是唯一一个把你当成病人看待的人了。”盖伊说,官员最怕的就是其他医生心里有鬼,想拿他的病换功勋,所以这时候鲁莽一些反而好。我不得不承认,盖伊比我更了解他的国家,知道怎么“救人”。如果只有我在,今天肯定要惹大祸。一支烟吸完分手的时候,我最后问了盖伊一个问题。我问他为什么不想教学生?就像以前一样,他给了我一个奇怪的回答,“我的人生观已经不适合教学生了”。就像以前一样,盖伊没有再解释。而这也是我们最后一次谈心的机会。在这之后没多久,因为两件事,我的医疗队队友们彻底和盖伊划清了界限。第一件事,是因为盖伊阻止中国医疗队给一个病因不明的5岁孩子输血,导致孩子在入院仅6天后就夭折了。这家的父亲因为车祸在医院不治身亡,本就不幸的他们却因还不上抢救费,被扣留在医院近1年的时间,只能乞讨为生。我经常看见那个大男孩抱着他的弟弟,呆呆地坐在医院门口。 无家可归的两兄弟
无家可归的两兄弟
有队友于心不忍,觉得这种方式也无益于他们还钱,只是医院泄愤而已。他们私下凑了30万布法郎(约600人民币),打算给这对母子“赎身”。没想到这件事又被盖伊阻止了,说他们医院的事不用我们管。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大道理能解释这种决定。我怒气冲冲地跑到了盖伊的办公室,直接将三十万布法郎摔在了他的桌子上。
盖伊好像早就知道我会来,因为他正对面的桌子上,摆着一根卷好的烟。
就像之前每一次对话一样,盖伊先叹了一口气。他将卷好的烟点燃递给了我。我没有具体提问,但显然他知道我在为谁打抱不平。他回答说,我有两个考虑。第一,医院的大门是敞开的,那对母子不走,是因为他们在这里还能乞讨,还能遮风挡雨,出去更是一无所有。“你们缴清费用真的是在救他们吗?还是在满足你们那份虚荣心?”盖伊也解释了他为什么不让我们给那个五岁的孩子输血。他问,你们能给出孩子的具体诊断吗?就算输血保住他一时性命,后续治疗能跟上吗?“如果折腾了一番孩子还是死了,那你有想过,所有这些治疗费用,要谁去承担吗?”盖伊说,他的第二个理由,正是因为他想解决这些问题。他当然可以凭个人的力量网开一面,或者让中国医生捐钱,先放走这对母子,但那条法律不变,其他的医院里还会有人在受苦。就像急诊科溜号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心软,有一个病人被放到晚上,事情闹大,后来的其他病人就不用在急诊室苦苦等待。在这一对母子的天平另一端,他衡量的是许多许多其他人。他问我还记不记得我们合作的那台手术?他说,他很羡慕我。中国医生可以花30分钟为一个孩子缝合伤口,只为了让孩子不留疤。他不是没有这个技术,可他没有这个时间。院长夸他是“全科医生”,那意味着他一直在被各部门借来借去,他根本不是真的在治疗病人,病人也没有得到好好对待。按这个逻辑,那对母子就该被关在医院里,直到布隆迪政府幡然醒悟,解决这一切。但是在走之前,我又忍不住回头问盖伊:“那两个被扣在医院里的孩子,你看过他们的眼睛吗?”我说,他们的眼睛里没有光。他们知道他家欠了医院的钱,甚至从来不敢和医院里的其他孩子玩耍。
大部分队友仍然因为那对母子的事在记恨盖伊,自然不会参加。小部分队友则在困惑,盖伊不是有老婆吗,在门口卖麻绳呢,怎么又结婚?但就在婚礼前一天,我在楼上抽烟时,远远看见盖伊坐在楼下长廊里,对着手机抹眼泪。麻醉师走过来问我要烟,我指了指楼下哭泣的大名医,打趣说,他是喜极而泣了吗? 在楼下哭泣的盖伊
在楼下哭泣的盖伊
麻醉师诧异地看着我说:“你没看请柬上的名字吗?哪是盖伊的婚礼?”我才意识到,因为过于讨厌盖伊,我们都没有仔细看过那张请柬,就丢到了一边。他告诉我,结婚的女人是盖伊儿子的未婚妻,新郎却不是盖伊的儿子。麻醉师告诉我,五年前,这里发生过一场严重的恐怖袭击,盖伊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都受了重伤,和另外10名伤员一同被送到医院。但当时值班的医生却被调走,去抢救一个“更重要”的人。就像本该在耳鼻喉科坐诊的我,被调到了急诊一样。那天的医院里,只有盖伊一个人。他独自战斗了整整15个小时。10个病人只活下来3人,包括他的妻子,不包括他的两个孩子。死亡患者的家属们来医院找盖伊闹事,一半人说他为了救活自己的妻子,抛弃其他病人;另一半人说他因为没有救活自己的儿子,拿其他病人撒气。麻醉师回答说不,他根本没有治疗。盖伊判断他们不可能被救回来,所以直接放弃了。他亲手给自己的儿子系上了黑丝带,标志着放弃治疗。即使那一刻,他们还在呼吸。那天晚上,盖伊不是只救活了3个人,而是因为放弃了包括他儿子在内的7个,他才有时间去救那3个。就在上周,我们医院也曾接诊了一批遇到小规模恐怖袭击的伤者。送过来的患者在楼下分诊,已经死亡或不可能救活的病人,系上黑丝带,危重病人系上红丝带,暂时稳定的系黄丝带。我清楚地记得,我曾亲眼见到一个被系上黑丝带的女人。作为一名耳鼻喉科大夫,那是我见过最恐怖的伤痕,她的耳朵被三道深可见骨的刀伤划开,伤口撕裂有两指宽。我手上的血还是热的,但我没有时间悲伤,匆匆放下她,奔向系着红丝带的病人。平均每个红丝带的病人,至少要花两三个小时去抢救,碰到严重情况,十几个小时救一个人也可能。但在后面等待的每一个黄丝带的病人,都可能随时变红,甚至变黑。我不由自主地想,如果有一次,没有分诊、没有其他医生,我要怎么做这个选择?我要怎么算,生命的轻重?盖伊必须精确、没有感情如天平,才能做出这样的选择。在牺牲其他人之前,他已经是那个被牺牲的。
那天中午,我正在看诊,诊室的门忽然被撞开。盖伊抱着一个男孩冲了进来。当时正在诊疗的我和病人都吓了一跳,我赶忙迎了上去,以为他怀中的孩子有生命危险。结果我却只看到孩子耳后有一大块擦伤,伤口虽大,连血都没流多少。当时我还在记仇他对急诊的那个孩子不好,呛他说:“哪有愈合不留疤的啊,这个瘢就是要告诉孩子以后小心点。”我以为盖伊这么紧张,受伤的肯定是他儿子,但盖伊却摇头否认了,说是路边的一个孩子,被他妻子弄伤了。盖伊告诉我,他的妻子在五年前遇到过一次恐怖袭击,幸存下来后,对暴力事件、聚集的人群和嚎啕大哭的孩子,都有一些应激反应。今天下午时,这个受伤的男孩在医院附近拿着玩具枪在欺负另一个男孩,他妻子一时激动,就把这个男孩重重推倒了。我才明白盖伊为什么把她带在身边。但我还是忍不住问盖伊,这么小的伤口,你怎么自己不包扎?不是说你也会那种缝合吗?盖伊没有回答,直到我完成缝合,要把男孩交还给他时,他突然向我鞠了一躬。他说,谢谢你,“现在的我没有办法给‘和自己有关’的人做手术,我会想起不好的事。”他眼带失落地呢喃了一句:“要是你们一直在就好了。”很早我就听说,盖伊想离开这家医院,但一直被院长驳回。麻醉师说,可能是上次我成功医治官员的功劳,帮盖伊如愿了。我以为盖伊将要调去更好的医院,但麻醉师说,听说是北边一家更破的医院,盖伊妻子的娘家在那里。那家医院也许无益于盖伊施展他的宏图大略,但对他妻子,无疑能得到一份宁静。他也听闻中国医疗队为那对母子和盖伊闹翻了,于是补充道,你们不知道,在你们来之前,是盖伊一直在施舍他们饮食。他还说,就在昨天,盖伊已经帮那对母子把欠款结清了,并且打点了很多人,让那对母子继续在医院住下去。麻醉师说,如果你还有什么不解的话,就尽快去跟盖伊医生说清楚吧。周一,我起了个大早。盖伊就在他的办公室里,那间办公室变得很空,他几乎都收拾完了,好像只在等我来告别。我有很多问题想问,但最终我只问了那对母子。我问,你为什么要改变自己的决定?他又叹了一口气,回答说,你说得对,“不应该让一些人成为燃料”。我想盖伊收下我们之前为那对母子筹的30万布法郎。他一个人帮那对母子还清欠款,想必负担也很重。我露出困惑的眼神,他笑了,指指心脏说:“这里富有。”他向我挥挥手,又走上了那辆通勤车。他竟然还穿着那件很丑的墨绿色T恤,背后写着“KISS ME”。他真的很喜欢这件衣服。

谢无界一直觉得盖伊“奇怪”,却说不上来哪里奇怪。直到要分别的那天他才明白,盖伊表面是个精英医生,其实跟他的妻子一样,没有走出那场灾难。
他的后遗症是,必须坚信治病是有代价的,要想着患者的医药费,要想着制造病人的法律。
因为他曾经无法支付代价,而放弃了自己的孩子。
但他忘记了,黑丝带意味着无法治疗,那不是放弃,只是接受现实。
那3个人的幸存,不是以7个人的死亡去换的。
该用什么衡量生命呢?ICU一天一万,布隆迪官员的一条命可以用几个人的去偿。
这个困惑,恐怕会伴随盖伊很久,但在故事的最后,他好像又作出了一些改变。
谢无界很希望有一天再遇到盖伊,遇到这个伤心的父亲、称职的医生、不知道困惑是否有被解决的人。
希望那时天气很好,盖伊还在笑,转过身,露出背后一句大大的“KISS ME”。
插图:大五花
本篇9528字
阅读时长约24分钟
如果你想阅读【谢无界】更多故事,可以点击下面的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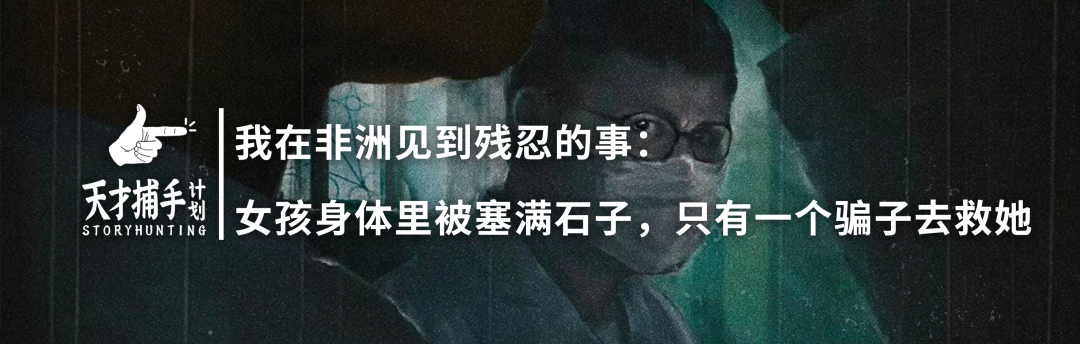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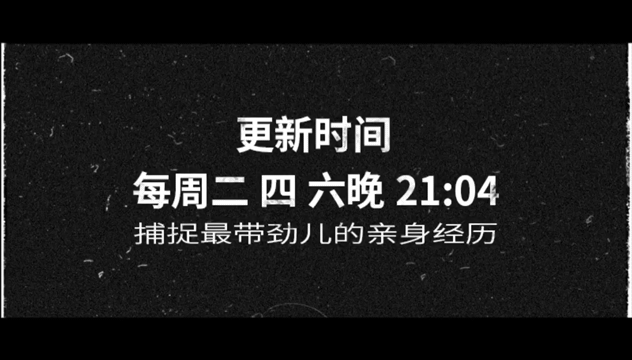
孩子的照片
无家可归的两兄弟
在楼下哭泣的盖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