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徐巧丽
编辑 | 陶若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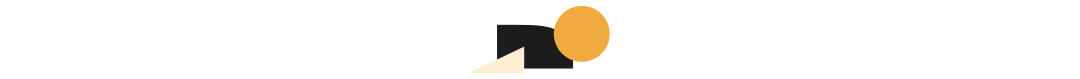
两个上海
来上海前一天,我妈恨不得所有的东西都带上,小到绿豆饼、刚做好的饭,大到电饭煲、电磁炉,还有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高压锅。被我和我爸成功阻止的还有砧板、碗筷、她喝茶的茶具。她也有她的道理,“做饭方便一点。”她做饭是清水炖一切,一道菜如果有调味料的颜色,那也一定是酱油的颜色。到了上海,我妈还是厨房的把关人,东西得用趁手的。高压锅是至少用了10年的老锅,中心已经焦黄,带过来的理由是煮东西快。用高压锅煮地瓜粥,每次我都觉得危险,不敢开,她会嘲笑我。我们老家盛产地瓜,每趟回家,她都要从老家带地瓜,带牡蛎,带蛏子,把老家的一切都搬过来,给我们做蚵仔煎。我厨房里只有一个电饭煲,是上大学的时候,偷偷买来在宿舍用的,10x15厘米,刚好两个人的量。不粘锅是我妈新买的,炒完菜她会先把锅洗了,还会特地叮嘱,不能用钢丝球。夏天小厨房里蒸腾着热气,她还要买一个小电风扇吹着。刚来上海的时候,在杨浦区的老破小,我们住在一个带阁楼的房子,一个月3700。楼梯是木头的,吭哧爬楼时嘎吱嘎吱响,拐角处电线乱缠,一不留神就会撞在我和我妈一米五多点儿的脑袋上。楼上楼下的也很复杂: 四十多岁的保安,二十多岁的保洁,一堆退休了没事儿干天天下棋的大爷、聊天的大妈。之所以选阁楼,是因为我不想没有任何隐私空间地跟我妈生活在一起。结果到最后我妈睡床上,我在旁边打地铺,阁楼变成了一个储物间,我俩变成了舍友。我妈有很多生活窍门。在福建看来,上海属于“北方”,树少,蝉鸣也少,但夏天的凌晨4点就有鸟叫,我妈嫌它们吵,拿晾衣杆也赶不走,后来她在抖音搜索小鸟惨叫的音频,对着这群鸟放,鸟也不听她的。隔壁八九点飘来很浓的油烟味,她就用纸板引导烟囱的风向,这倒是成功了。每天早晨,我妈就在旁边等着,等到我摆出一副要出门的样子,她就突然换衣服穿鞋,踩着点跟我一起下楼。下楼后我们就背对背走了,我骑小电驴去公司,她给自己搞了一个二手自行车,抄近路去买菜。她以前是图书馆管理员,短头发,喜欢穿红马甲这种饱和度高的衣服,给人一种很忙的印象——一坐下来,她就开始上杂志,接着编码,然后扫地拖地。退休后她就在寻找一种新的秩序。比如今天下雨,她去睡觉,又纠结不能睡很久,会破坏生物钟。她开始用时刻表,规定这一小时做什么,那一小时做什么。头发也开始留长,来上海的时候已经绑成了小马尾,背着促销赠送的水红色斜挎包。 ●小松拍下第一次看话剧的阿敏。讲述者供图
●小松拍下第一次看话剧的阿敏。讲述者供图
上海的一些现代化设施会让我妈感到害怕,自动扶梯好几次差点摔倒,坐地铁扫码过不了,要我隔着闸机帮她扫。到上海的第三四个月,她下载了boss直聘、今日头条、58同城,戴着老花镜眯着眼睛每天研究。很多岗位都不要35岁以上的,更不要50岁的,合适的岗位只有食堂阿姨、保洁。有一天她发现一个模特中介公司,找上镜的淘宝中老年模特零工。我陪她去杨浦区五角场附近的写字楼面试。她穿上裙子,涂上白白的粉底,画上眉毛,画上眼线,一路上挺兴奋,整个人鲜活了很多。到了一看,是个非常小的工作室,有三四个应聘者,一看就是高中生或是大学生,满脸写着“我还没毕业”。一个中年男子问,是谁来面试?我指了指我妈。他上下扫了一眼,让我们进房间面试,面试官让我们回去拍几套写真。回来后,我把我的衣服给我妈穿,夏天的港风皮衣,黑色的背带裤,那一瞬间我感觉很奇妙,像她不是我的母亲,而是社会意义上的另一个女人。我们在家楼下的花从草丛里找了半天最佳姿势,被蚊子叮了很多包,拍了好多照片。发过去再也没有什么后文。但我妈没有放弃找工作,又不知从哪儿找到了个复旦附属中学的餐厅后厨岗,成了“食堂阿姨”。每天早上醒来她已经出门,到了晚上,她就开始吐槽,工作真累,上司真凶,她想给学生多加点菜,上司会说少加点,还指责她手脚慢。另一个档口的老板就会过来安慰她说,“你别在意,他刀子嘴豆腐心。”我爸有点身份包袱,不赞同她去做这个。她来上海后,我爸每天晚上固定时间给她打一通电话,她下班要到九十点,就很容易露馅。露馅了她就有点惶恐,有点纠结,因为我爸算是家里拿主意的人。我就跟她说,我爸又不在,管不了她。我也有私心,想让她感受一下体制外的世界有多么残酷。我和她处在两个上海。一个是年轻的,摩登的,恨不得48小时都在跑步,要么赶着上班,要么赶着开会。我们参加吐槽公司的脱口秀,和年轻人玩剧本杀,走路看百度地图。一个是年老的,底层的,杨浦区本地人浓度低,都是外地来打工的老人,她就看这些老人聊天打牌,回来告诉我又认识了楼上楼下邻居谁谁谁,后来自己也成了一员。我们那个大厦里每一层都有固定的保洁员,有一次我看保洁阿姨在脑后把头发绑成一个球,和我妈好像,她也喜欢把刘海都梳得精光,把头发在脑后盘成一个球。我看着阿姨打扫卫生,在想我妈会不会现在也是在食堂做着类似的工作。一个月后,她拿石锅拌饭的铁板,不小心把手烫伤了,就把工作辞了。她第一次写辞职信,从网上找了模版,把名字改成自己的,再让我过了一遍。不久之后,我也经历了另一种残酷——裁员开奖。坐在办公楼里的人齐齐变成了两种模样:一种发了疯似的加班,打字的手一刻也不停;另一种从办公室消失。我没有在名单上,但带我的一个姐姐走了,那时我第一次意识到,公司是一个为了利益而存在的组织。2022年底,我先得了新冠,我妈照顾我,第二天她也阳了,就轮到我照顾她。这一年过去之后,上海下了一场雪,我妈很兴奋,跑到阳台看挂在树上的一点点小雪花,那是她经历的第一场雪。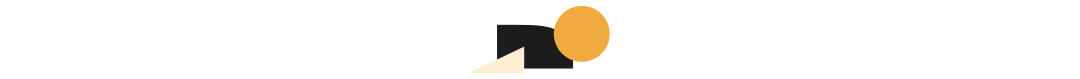
番茄,sei ang ki,fan ga
我妈对上海最熟悉的就是菜市场。基本上每天都去逛。刚来的时候,会在饭桌上对比这边的菜价跟我们家那边的菜价。她第一次见这么多品种的西红柿,2块5的,4块5的,7块的,12块的,产地不一样。一开始觉得菜价和泉州差不多,过年的时候突然涨了一倍,她就每天感叹买菜钱变贵了,生活费消耗变快了。她把一切都和老家的东西类比: 这里的地瓜干没有老家好吃,这里的街道也没有很繁华!她在老家的小姐妹,不是在收租,就是在带孙子,她原本也在家收租,现在变成租房子的人,和小姐妹打语音,她最常说的一句话是: 还是家里好,上海也没什么了不起。我带她去看开心麻花的话剧,看贰叁叁的脱口秀,想把她拉到我的世界,感受一下年轻的上海。看完路上我问她想法,她还是搬出那一套参照系,“我在老家也能看高甲戏、木偶戏。”2022年6月初,我研究生毕业,在上海一家互联网公司找到工作。那年也是她退休第一年,在家那边没啥事做。我是独生女,我家就盘算好了要我妈来上海陪我。不算我的,她至少带了三个手提袋,有一个蓝色的可以装下两个我。她拿了一个小推车,用绳子把三个袋子绑在小推车的拉杆上,从泉州运到高铁上,带到了上海,就这样一路推过来。最麻烦的是过地铁,没有自动扶梯,要一趟一趟上下搬。刚来上海,她要先去庙里拜一拜,搬家的时候,也要去庙里拜一拜。有一天她说菩萨给她布置了任务,要在今天晚上几点之前,把什么事情办好,比如说去买一个床单,或者床垫,放在家里的哪个位置。我在网上下单,得两三天才到,她就没完成任务,跟我说,“上海的菩萨不欢迎我”。后来我才知道,来上海之后,她经常睡不着觉,但我睡得死死的,她很多事情都没跟我说。她不太能适应大城市生活的节奏,人生前50年,都呆在泉州四线小县城,不随意请假,不经常出省。我们开车去厦门的路上,会经过她上班的路,她会介绍这条街通往哪里,这条路我年轻的时候走过几百遍,在我记忆里,这是她走过最远的路。后来下岗潮,粮站的工作没了,图书馆的工作是她毛遂自荐的。包括找工作、找对象,她很努力地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上。她是家里的老二,上头有哥哥,下头有妹妹,十六岁就被剥夺了上学的资格,去粮站卖米,工资要上交补贴家用。她和我爸是相亲认识的,她很早就预知到,家庭的资源会倾斜在哥哥身上,要想经济独立,婚姻多多少少是能够帮上忙的。我爸是长子,他以家庭为单位去思考事情,也会比较说教,应酬喝酒完嗓门就比较大,唠叨我作为家中长女要怎么怎么样,我妈就管理家庭小事。我对她的印象,就是中午放学回家,看到她一直在厨房......要么是背对着我们在择菜、切菜、炒菜,要么是吃完以后在洗碗或者收拾餐桌。出门去玩,也是去姐妹家打牌。她的忙,像是一个上了自动发条的NPC,每天定时定点在你看不到的游戏界面背面,按部就班完成各种事项。卫生间永远是干净的,她说“厕所是不是干净,可以判断这个家的女主人平时是不是懒惰”。她不在的时候,家里地板上全是黑色的脚印,床单也落了灰,爸爸都不知道整理。 ●小松和阿敏在上海租的房子。讲述者供图
●小松和阿敏在上海租的房子。讲述者供图
在上海,她也忙这些事,但会更多考虑自己。她喜欢用拼多多布置自己的家,厨房的小风扇,200块的无人机(我把它退了),还会买帐篷、买睡袋,冬天在睡袋里暖和,她还安利我一起睡。她也在重新寻找老家之外的第二种人生,而且是在完全陌生的土地上,就像打新的升级通关。借由菜市场,她认识了好多邻居。刚来第一天,她去菜市场买菜,楼下一堆大爷大妈聊天,她问哪里有菜市场,就有一个安徽奶奶自告奋勇说,我带你去,还告诉她怎么抄近路——实际上指的是小区围墙栏杆少了一角,后来她们每天从栏杆里钻出去,一块儿买菜。安徽奶奶之前在北京呆了十多年,后来又来上海,她住三楼,两个儿子都在上海打工。熟了以后,每天早上9点来我们家敲门,我一般在房间化妆,她们两个就坐在离我很近的地方,一个用安徽口音的普通话,一个用闽南口音的普通话,聊今天吃什么菜,聊家庭,聊过去。我是半懂不懂的,她们还能对上话,我妈经常展现出我意想不到的适应力。还有一个江西阿姨住楼上,50多岁做保洁,她和我妈去植物园玩,传授我妈去虹桥火车站的捷径。她在一个夏天搬走了,给我们留了家具。妈妈第一次经历大城市的离别,跟我说这个人可能以后再也不回来了。我们在一年以后搬家,从老破小搬到了二楼就不装防盗网的小区,上海人的浓度大大增加。她开始参加社区组织的活动,学视频剪辑课,看社区的电影,还开始学上海话,每天早读,从菜市场用语学起——玉米泉州话叫yomi,我妈学叫珍珠米;番茄用泉州话叫sei ang ki,现在就要叫fan ga。在这个小区,她交到了一个热心肠的阿姨,性格特别像她老家一位姐姐,那位姐姐得癌症去世了,我妈就在这个阿姨面前大哭。不过,有个70多岁的阿姨想开摩托车带我妈去跳广场舞,我妈就说不想跟她去,她怕跳着跳着,(对方年纪大)就出什么事情了。她社群融入做得比我好,对上海的路线也比我熟悉。我要看着百度地图走,她可以说出坐哪路公交比百度地图还快。今年五一,我爸也来上海,我妈就教他怎么坐地铁。做了一个月的食堂阿姨,她也懂得放黑椒酱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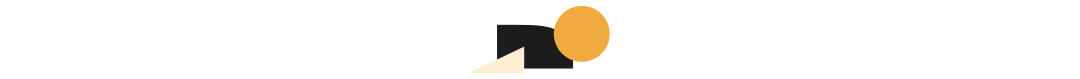
一个清晨
我妈在上海住了一年,之后回到老家经历外婆去世,今年又回到上海。在老家照顾外婆时,她有意无意说,还是上海好。我好奇她对上海的感受,在清晨吃早饭的时候,和她发起了对话。妈妈:害怕,以后要怎么在这个地方过养老生活?像幼儿园入学一样,一切都是零。我从抖音里看,一直跟我讲是魔都、魔都,我就想是不是像魔术一样变换来变换去的,让你追不到。还有说是压力大,很多人都梦想着做一个沪漂,能多往上蹦,但是又没有那个条件。我们老家来上海的都是比较出色,非常成熟,有家庭能力,但是到上海过来了,都变成是打工一族。我:那你又怎么决定来呢?我感觉我当时一个人在上海住着也行。妈妈:我想到了姥姥的一句话,孩子长大了,不要放飞太远了。像我一个同事,他花了几十万把儿子培养到美国去,后面他生病了,儿子都没来看他。他一直想不通培养这么优秀的孩子,选择了这样生活。你爸爸50%也是跟我一样的想法。我也从小到大也没出过一次,离开过家里一次。所以我也有点,嘿嘿,有点想尝试另外一个环境的生活。妈妈:我觉得也就那样。只要有个房子就是有归属感,一直借房子就没有归属感了。我也观察了周边的生活情况,就觉得上海这20年,哼,没进步。建筑还是有先进的,衣服,我们年轻那一代,特别注重衣着打扮。我那时候穿连衣裙,喇叭裤,还有叫塑形窄脚裤,还有葫芦裤,是专门请设计团队设计出来的,花了高价钱,跟上海比,我觉得是没差多少的。接触的环境,空间太窄了,生活质量也比不上老家。来上海的时候,我没想过会只接触个杨浦的中老年打工人,以为可以交上海朋友。上海人不大喜欢和外地人聊天,他们也不想讲普通话。我按照公众号去了很多景点,像宝山的沪松公园,国家森林公园、安徒生乐园、杨浦公园、黄仙公园、虹口公园,很多60岁以上的老人,他们问我第一句话就是,你和谁来上海的?多久了?借房子还是买房子?现在学上海话也是想跟上海人交流,听懂他们说什么,要不然没话说,憋得难受。我:那你从泉州过来跟我一起生活以后,有发现我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妈妈:我和你从大二以后交流就少了。现在发现你懒了,外卖多吃成习惯了,觉得妈妈的味道不好。一点都不成熟,这个是跟以前的比较。是你自己的生活环境和我们不一样,觉得和我沟通不了,和我思想有代沟了。我也想让你学习考试,抓紧时间考公务员。你现在的工作,我说好也好,说不好也不好。疫情过后马上有那么多人下岗,让我害怕这个工作随时被淘汰掉。我现在觉得给你足够的时间了,你应该继续考试。我:等于说上班两年,你觉得给了足够的时间体验生活,现在还是要回归正轨去考公务员,对吧?妈妈:考编制、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都行,毕竟大城市的高学历竞争太厉害了,这两年看的都是学历。还有最操心的事是赶紧把对象找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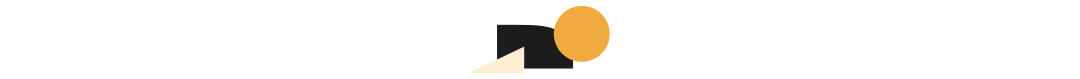
两个形状不同的人
一说到考公、相亲这些话题我忍不住想质疑她。我妈到处帮我张罗对象,她怕我错过这个窗口期,老是跟我说这段时间很珍贵。在今日头条上,她看到一个浙江阿姨写一些替儿子找对象的内容,就跟人家成为笔友,收集人家儿子的资料。某个夏天周末,她笑眯眯跟我说这个笔友带她儿子过来相亲。我穿了绿衬衫,黑色工装裤,没有化妆,态度一整个消极。对方是一个1米7,戴眼镜的男生。我们4个人绕着公园外墙走,男生总说自己的学生时代,多么努力,在这个单位认识了多少人。我问他,喜欢看什么电影,他说喜欢看动画片。后面我俩都没互相加微信。我妈也不满意。她还去人民公园给我相亲。有一次我也跟她去,地上摆了一堆纸条,纸条上有条件,我妈一个一个去看。看到一个金融男,我说金融男不行的,刻薄,爱钱,特别算计,容易被坑;她说或者体制内的,家里有几套房,我就说这人肯定是个妈宝。后来她又去了三四次。她自己也会遇到搭讪的。有个男的说她长得很好看,问她老公还在不在,要给她介绍对象。这件事她会跟我爸说,讲起来还有点小得意。她讲上海没有她年轻时候时髦,但她退休之后,变得臭美了,会穿裙子,捯饬发型,还要控制体重——退休后不运动,她胖了10斤。从她身上我又似乎能找到当初自己适应大城市的影子。前两周,我带她去听 LiSA 的演唱会,她舞着应援棒,学着其他人一起应援。和我说晚上回去得喝点酒,不然会激动得睡不着。 ●今年春节在老家看花灯的阿敏。讲述者供图
●今年春节在老家看花灯的阿敏。讲述者供图
有一天晚上我在厕所里面照镜子,她经过的时候,我就喊她一起来照镜子,她就说不要,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她就说,我已经这么老了,你又这么年轻,我嫉妒。我对妈妈的观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一个北欧女性作家写她跟母亲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我母亲经常嫉妒我,嫉妒我有天分,嫉妒我写东西写得好,嫉妒我年轻。”这段论述给我印象很深。还有伯格曼的《秋日奏鸣曲》,想在电影中达成母女想象中的和解,拍着拍着她发现没有办法达成,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这两个人开始吵架,就开始互相倾诉。我开始想到,我之前对我妈的视角也比较狭隘,只看到她母亲的一面,忽略她女性的一面,我应该把更多目光聚焦聚焦在她的另外一面。小时候带我是她的责任。她会骑自行车带我去图书馆,我会给她念我写的童话故事。她还操心我的身高,向每一个人询问长高的办法,带我去老中医馆,吃黑乎乎的药丸,还让我学游泳,最后我的身高随了她。十多岁我就一个人睡,后来她还问我要不要一起睡,我说不要不要!在日记里我写:她这么反复问我,其实不是突然良心发现以为我还需要拥抱,只是她自己一个人不习惯罢了。妈妈也是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因为没有人肯给,包括我。去北京上了大学,我离她更远了,忙着参加各种活动,去LGBT的线下交流会也不敢跟爸妈说。大一暑假回家,我的味蕾已经变成了外地的形状,对我妈清水煮一切已经不习惯了。我妈就开始叫我阿北子,外地人的意思。六七年的时间,我成了跟土生土长的她完全不同形状的人。因为太久没有住在一起,反而越来越认清了我们之间的差异。关于考公,关于相亲就是我们最大的磨合。我们的日常生活更多像搭伙过日子,有尴尬、生气的时候。每次吃早饭,考公啊结婚啊她都要提一嘴,吵完架直接出门上班。下班回来,她要是气还没消,就会白我一眼,要是气消了,就问我明天吃什么。房间没有客厅,她用帘子隔出了客厅和卧室。她朋友来,我就得拉上帘子,最尴尬的是我和对象打电话,得躲到厕所去——万一她知道我有男朋友,后果就很难控制,得往结婚走了。晚上睡觉,我睡地铺,她就和小时候一样,邀请我一起到床上睡,我还是拒绝,维持微妙的边界感。她经常对我有某种要求,却很少有完全懒散而轻松的相处时刻。我们的关系常常被责任和要求压过。小时候,我是“考学人”,她是担心我在学校表现不好的“母亲”。她床头柜里有我初一到初三每一学期的成绩单,纸张都有了毛边,她会研究我每一次成绩波动,安排我补习数理化。现在,我是“求职人”,她是帮助我社会化的“母亲”。安排我考公,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正轨。假如我去面试,早上醒过来会发现她萎靡不振,她会说“想到你今天要面试,我就睡不着了。”去年9月参加外婆的葬礼。有一天晚上我们烧她生前穿过的一些衣服,发现外婆在临终前一两年,买了很多很鲜艳的衣服,很少见她穿,但她会买,把它们收藏在一个挺整洁的地方。我就会意识到,外婆也有自己喜欢的东西。但在葬礼上的四个花圈,来自她的丈夫、儿子、高中同学、儿子工作的单位,讨论她时,我们在说她是妈妈,说她是外婆或者奶奶,我们都是她的亲人。我妈也是这样,只是一个家族里面的个体。如果说我最想回到母女关系的哪一刻,应该是三四年级我们一起午睡的周日中午。有时候会从12点睡到下午4点。有一次,又是一口气睡了四个小时,她醒来的时候看时间,惊呼,“怎么就睡到4点了!” 结果说完没有爬起来,反而在床上赖着。这是她很少见的赖床时刻。想念这个两人一起放空,既没有学业压力,也没有就业压力、生存压力的普通午后。版权声明:本文所有内容著作权归属极昼工作室,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形式使用,另有声明除外。


●小松拍下第一次看话剧的阿敏。讲述者供图
●小松和阿敏在上海租的房子。讲述者供图
●今年春节在老家看花灯的阿敏。讲述者供图
●小松拍下第一次看话剧的阿敏。讲述者供图
●小松和阿敏在上海租的房子。讲述者供图
●今年春节在老家看花灯的阿敏。讲述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