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周,可能是近20年来美国最大的一次宪法解释变动发生了,美国最高法院的一项判决初稿被泄露,“罗诉韦德案” 判例将被废除,美国女性的堕胎权将要被翻转。

“你无法终止堕胎,你只是在终止安全堕胎”
“罗诉韦德案” (Roe v. Wade)被认为在美国民权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73年对此案的的裁决确认了宪法赋予的堕胎权,且受宪法隐私权保护。
为何堕胎与否,会成为一项持久的战争?看似明白的议题,争议点到底在哪里?这一期的《思辨力35讲:像辩手一样思考》里,两位辩手——
庞颖代表提问一方(反方观点),詹青云从自己法律从业者的角度(正方观点),对这个议题的由来与影响进行了一场全方位的深刻辩论,问题不止涉及法律,关乎现实,也关乎一些最根本的追问。
💡 *此为经典辩题的辩论,并不意味着代表双方个人立场,请勿对辩论方人身攻击。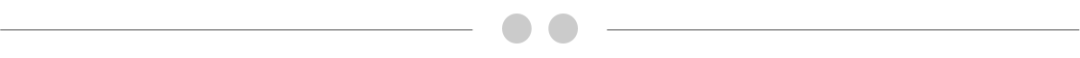
🗣
讲述 | 庞颖x詹青云
来源 | 看理想节目《思辨力35讲》
背景阐述:
判例被推翻后的蝴蝶效应
詹青云:近期,最高法院的一个草稿的判决书被泄露了出来,美国最高法院有可能会推翻“罗诉韦德案”的判决,影响女性堕胎权的保护。将近50年过去了,堕胎问题仍然是美国的社会文化战争中最重要的一个议题,可能仅次于持枪权利的争论。这些年里,保守派也就是共和党占领的红州,始终不渝地向堕胎权发起挑战。2018年,密西西比州政府通过了一个法案,禁止孕龄15周后的所有堕胎,哪怕是因为强奸导致的怀孕也不能。它就被当地组织起诉至了联邦法院,判决发布了一条临时禁止令,不允许这项法律在最高法院作出裁决之前在当地推行。这条法律被挑战,就是因为它被认为是一项违宪的法律,违背的是“罗诉韦德案”,因为后者确认了堕胎是一项宪法权利,不能通过立法的形式去剥夺一个人的宪法权利,这个官司一直打到了美国最高法院。现在美国最高院大法官里,保守派与自由派的人数比例高达6:3,很有可能会认同这条密西西比州的法律,推翻罗诉韦德案。最终判决原本预计在今年6、7月作出,但在上周草案意见以一种泄漏的方式被公布了出来,本来许多人猜测,最高法院确实会认同密西西比州的法律,但会进行一定的限制,或者是巧妙地避开回答“罗诉韦德案”是否仍然属于美国宪法这个问题,但出乎意料的是,没想到这份草稿如此坚决地完全推翻了罗诉韦德案。这个泄露事件在美国社会引起轩然大波,后来首席大法官罗伯茨站出来说,这份草稿确实是真实的,但它还不是最终意见。在最高院里,首席大法官会指定一位大法官去撰写判决意见的草稿(此次就由阿利托大法官撰写),再把这份草稿传给其他大法官浏览,大家会争辩、修改,最后坐在一起投票,有几位大法官在这份判决意见上签字,结果区分出最高院立场站在哪一边。草稿意见被有意地泄露出来,在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长期的辩论传统,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甚至最高法院的建制本身都受到了极大挑战。另一方面,去年12月在这条密西西比州反堕胎法的审判过程中,一位自由派大法官曾经警告说,如果今天最高法院要做出一个推翻罗诉韦德案的决定,这可能就会动摇最高法院建制本身。因为罗诉韦德案在美国成为宪法已经将近50年了,它已经被大部分美国人认为是一个理所当然的权利。虽然美国社会仍然在保守和自由派的分野上界限明显,且日趋极端,但在最新民调当中,超过50%的人认为罗诉韦德案是一个好的判例,认为它应该被推翻的人只有不到30%。正方观点1:
堕胎权是人的基本权利
詹青云:当年,“罗诉韦德案”是怎样的方式确认堕胎权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呢?是引述美国的第十四修正案,任何一个公民的自由,政府不经正当程序不能够剥夺。这种自由被解读为含有一种隐私权的自由,堕胎权之所以被宪法保护,是因为它属于人的隐私权。一提“隐私权”这几个字,大家首先可能会想到个人信息被泄露这方面的隐私,觉得和堕胎权好像隔了十万八千里。其实隐私权这个概念,是分成好多个类别的,它当然包括 information privacy,也就是信息隐私。还包括物理的隐私权,比如不想被人偷窥,我身体的一切,器官,血液、精子、卵子等等,未经同意别人不能取用。还有一项隐私权,叫做decision privacy,就是决定的隐私权,指的是在私人领域内,关乎个人生活方式的决定,不受政府或他人的干扰。而隐私权这个概念受到很多争议,包括罗诉韦德案本身的争议,因为美国宪法和宪法所有修正案里,别说从来没有提过“堕胎权”,连“隐私”这个词都没有。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美国最高法院就频频地用隐私权这个概念,来合法化保障一系列的个人的基本权利。70年代,就是今天要聊的罗诉韦德案,一位女性要不要堕胎,还是选择把孩子生下来,这属于她的隐私权。隐私权在90年代被用来认为人有消极安乐死的权利,到了2000年,隐私权被美国最高法院确认了同性性行为。
虽然隐私权这个概念本身一直受到质疑,但我的立场是,用隐私权合法化堕胎权是没有问题的,是符合法理也符合道理的。从法理的基础上来讲,我在节目(《正义与现实:像律师一样思考》)里聊过很多次:文字是有局限的,法律也是有局限的。法律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是具体文字的产物,不可能囊括未来时代里人们将要遇到的一切问题。所以,后世法官作为法律的解读者,一定是一直不停地用旧有的、有限的法律,去解决人们在现实生活当中面对的新问题,面对时代发展和变化。我们只能从过往的判例或者成文法律里,去理解法律试图保护的是什么,把它套用在现实的模板里。否则的话,就像阿利托大法官在这份的草案判例里写的,如果宪法没有明确地提出某项权利值得被保护,那就不能被保护的话,现在很多大家认为理所当然的权利,那都是不可能的了。美国的宪法修正案里虽然没有直接提到隐私权这个词,但是它是在很多地方隐含了“人有一块私人领地,不受公权力干扰”的理念。比如美国宪法第三修正案说,政府不能够无故地征用房子去给战争时期士兵使用,这个概念后来被很多解读成不同的层面,它基本上就认为不能够随意征用房子,因为房子是公民的私人领地,这也是一种隐私权。对法律的解读,从来就不拘泥于去看法律本身的文字写了什么,而是去看法律想要传递的,试图去保护的东西是什么。而既有的法律或传统跟历史里,从来没有提过堕胎这项权利是很正常的。曾几何时,堕胎没有被法律确认,但是也从来没有被法律禁止。美国法律禁止堕胎本来就是上个世纪才有的事情,而堕胎成为一项重要的需求,也是伴随着二战之后大量女性,她们不再仅仅留在家庭中做一个家庭主妇,所以她们开始选择性地不要孩子,或者是选择性地在某个时间节点再进行生育,这是在我们今天看来理所当然的事情。而同时医学的进步也证明了,只要是在一定期限内,在医生许可的情况下进行堕胎手术是非常安全的,对人身体造成的伤害是可控的。所有这一切条件成熟和需求产生,才是合理化堕胎这种需求出现的时机,所以它没有根植在现有的法律文本和历史传统当中,是很正常的事情。而一位女性,这就是老生常谈了,她应当有权利去选择她是不是要生养一个孩子。或者说,当一个女性被迫去生养一个她不想要或者没有条件生养的孩子,可能造成巨大的伤害,这都非常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应该是个人有权利去决定的事情。反方观点1:
“堕胎vs谋杀”仍需论证
庞颖:那些反对堕胎的人,他们的观点是认为,堕胎它不属于、也不能被隐私权保护,因为这其实是一种“杀人”,就像如果我今天谋杀了我的邻居,一个成年健康的人,它不能被我所谓的“决定隐私”保护一样。如果今天我决定杀一个肚子里的胚胎或者胎儿,在他们眼中,这跟杀一个隔壁的成年人是一样的性质,所以当这种决定相当于一种谋杀的时候,它自然不在隐私权保护的范围之内。而像同性恋或是跨种族婚姻,它对第三者没有危害,可以被隐私权保护。这些反对保护堕胎权的人主张“pro-life”,自己要保护生命的一群人。他们的核心和最强的论点就是在说,你杀死胚胎或胎儿,其实是一种谋杀,所以你这个时候说不是它是一种隐私,其实没有解决最核心最强的论证。在辩论之前,我也特意问了一下詹青云,罗诉韦德案的判词里面,有没有去论证为什么堕胎不是一种谋杀?她说当时并没有特别仔细地去论证,就提了一句话,虽然说人的生命权是受到保护的,但是没有证据表示胚胎能(享有)。我认为这是诉诸于一种推卸论证责任,(堕胎权)辩论的两方都互相认为,论证这个胚胎是不是人这件事的责任在对方,自己享有推定利益,也就代表在最核心的争议上,他们没有积极主动地去进行论证。可是如果真的站在人人平等的角度之上,这是必须要去面对的问题,胎儿的权利究竟是不是人权?所以罗诉韦德案用隐私权来保护堕胎,并没有积极主动地去论证和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挺大的缺陷,为后世带来了非常多的问题。这其中也留下了一种解读空间,仅仅是推翻了堕胎权不被隐私权保护,还是说推翻了罗诉韦德案,就代表所有受隐私权保护的都不再将要被保护?尽管写判词的阿利托法官,认为推翻罗诉韦德案不会影响到其他议题。如果今天真的不保护堕胎权了,也不是美国大多数民意的体现,它是特朗普借机把那么多的保守派大法官塞进了最高法院之后,出现的一个6:3的保守派占上风的结果,甚至非常有可能会做出与真正的民意不完全一致的判决。要保护堕胎权,不是只有判例这一个方法,其实还有其他可行的方法。比如说通过宪法修正案,通过设立联邦法律等等。可以不完全依赖罗诉韦德案的判决结果,而采取其他的立法途径去保护堕胎权。是否可以不借助隐私权,不完全取决于一个判例的判决,有可能会能更稳固地去守护住想要守护的东西?正方观点2:
这件事情很有趣,罗诉韦德案的判词,没有给人下一个最终的定义,也就是说,它没有勇气由大法官们去回答,一个其实没有人可以回答的问题,就是生命到底是从哪一刻开始的。但是直觉都会告诉我们说,如果要讨论堕胎权是不是一项应该被保护的权利,我们注定要讨论生命是从哪一刻开始的,这样才能说堕胎权是不是谋杀。如果它是的话,我们该怎么平衡两边的利益呢?可以被泄露的这一份将要推翻罗诉韦德案的法律意见,这份长达98页的草稿里,阿利托竟然完全没有聊生命是从哪一刻开始的这个问题,这根本不是他推翻罗诉韦德案的核心依据,他完全避免了对堕胎这件事情本身的任何实质讨论。这是一个联邦主义出发的判决,阿利托说,因为我们是一个联邦的国家,所有的基本权利都应该保留在州,只有那些被明确写进了联邦宪法的权利,才是州人民让渡给了联邦政府的权利,所以不该联邦宪法去管的事情,联邦的最高法院就不应该插手。正好讨论一下,当罗诉韦德案被推翻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当堕胎权不再是一项被美国联邦宪法保障的个人基本权利之后,一个人是不是有堕胎的权利,这件事情的决定权就被交回了各个州的手上。有的人说这才是民主,这才是自由,每个州都有权利去制定自己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很不负责任的,不是所有的偏好都叫做自由。今天决定要不要把一个孩子生下来,这是我的选择,这是我的隐私权。不能一个保守派的人说,我觉得你不应该堕胎,我有让你不自由的自由。一个反对堕胎的人,你可以自己不做这样的选择,你永远尊重生命,你认为生命在受孕的那一刻,就是上帝给的奇迹。但是你为什么能够把你对生命的理解强加到他人身上,以此为理由来剥夺他人的私权?我觉得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罗诉韦德案的确没有回答生命是从哪一刻开始这个问题,那是因为这个问题不该由法官们来回答,这是一个神学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是一个道德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这些领域内,对这个问题都没有确定无疑的答案。可是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不代表对这个问题是没有担当的,恰恰因为所有人对这个问题没有确定的答案,所以我们实现了某一种妥协。绝大部分的人,根据民调或者大家诉诸自己的直觉,大概率会觉得胚胎并不是生命,而一个已经成型的胎儿,在孕期后期的胎儿是一个生命。在科学上也有证据,孕前期的胚胎是没有知觉的,而即将出生的、孕期后期的胎儿对外界刺激会有反应,离开母体能够存活。这就是为什么罗诉韦德案做了一个三段论,就是把孕期分成三个阶段,然后它确定说,政府是有保护一个未来可能的生命这种权利,可以一定程度介入,但是这种介入是受限制的。这个三段论后来在1992年的一个判例,“凯西案”中被替换为viability,就是只做一个区分,如果胎儿离开母体不能够存活,就是大概在怀孕的前24周,州政府不能够介入女性是不是要堕胎的选择,而24周之后州政府可以介入,但不能够为女性创造无法克服的困难,导致女性不能够正常地行使她堕胎的权利。这个妥协尊重了民意,尊重了科学,我认为它是一个合理的妥协。而一旦把这个权利退回给每一个州,并不是每一个州立出来的法律,就是对的。民主也可能变成多数人的暴政。为什么一个国家要有宪法?因为宪法确定,人有一些基本权利是不可以被立法、不可以被民主的过程夺走的,防止出现多数人的暴政。我认为把权力退还给各个州,这种做法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而这就是阿利托整篇98页的草稿,没有讨论这是不是在杀人,没有讨论生命从哪里开始,他最想讲的事情,就是说这件事情我们(最高院)不想管。接下来第二点,一开始提到的隐私权这个概念,没有在宪法里明确的写,但是它对于整个美国法制社会的运转非常重要,因为有很多现代社会习以为常的权利,也是被隐私权保障的。阿利托的判决说,联邦政府有一些事情不该管,反过来是说,联邦政府只应该保障那些被明确写进了宪法的基本权利。除了言论自由,还有持枪的权利,这都是明确写进美国宪法修正案的,这些权利有坚实的基础,我们保护。而那些没有被写进宪法的权利,是之前的那些法官发明创造出来的,除非某一项权利在这个国家有根深蒂固的历史跟传统。他甚至跑到什么英国罗马法利去找历史跟传统,那当然找不到。一旦阿利托的这篇意见成为法律,它相当于明确说了,美国的宪法只保护那些明文写进宪法的权利,和在美国社会有根深蒂固的历史跟传统的权利,这开了一道非常危险的口子。美国国家历史只有200多,堕胎这项权利都已经有50年的历史,他还说这不是根植在我们的历史传统里的。既然近50年的判例都可以被推翻,那同性婚姻的判例还不到20年,何来的历史与传统呢?另一个问题,保障人的基本权利不是只有通过司法的形式,这话说得没错。在很多的国家,堕胎权利是通过立法,甚至像爱尔兰是通过公投解决。可是第一,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两件对的事情我们都应该做,不能说如果我做了第一件对的事情,大家可能就没有动力去做第二件对的事情,那第一件事情就不该做,这不是衡量我们该不该做一件事情的标准。第二,它确实最高法院通过司法的形式,保障了美国社会在过去的50年内,能够普遍的行使这项堕胎权利,而国会是基本指望不上的,因为美国现在这种选举团的选举制度,给了那些小州或是一些保守派过大的话语权。所以今天的美国国会根本没有可能通过联邦法律的形式来保障这项权利,哪怕绝大部分的美国人都认为罗诉韦德案不该被推翻。最高法院甚至是唯一的指望,而且确实在过去50年里,就靠着这个判例撑到了今天。甚至进一步讲,就是一个国家的最高司法机关,应该在国家的历史进程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最高法院应该是一个人的这种基本权利的捍卫者,不应该放任民主暴政可以践踏人的基本权利,甚至不应该只是一个民意的反应者。反方观点2:
核心问题不论证,是否会变得更极化?
庞颖:好,先回到一个更加本质的问题,就是堕胎权应不应该被保护。我在辩论辩题之前去看了一下那些反对堕胎权的人他们写的这些文章,当然他们文章里面有一些我不认同的点。但是他们也有一些观点,其实是让你觉得值得你去仔细想一想,你甚至要绞尽脑汁才知道怎么反驳的。其实最触动我的,或者我觉得最难反驳的就是他们认为,堕胎其实是一种谋杀。对我自己来说,“堕胎是谋杀还是不是谋杀”这件事情在我心中好像没有那么大的道德反应。但是如果想象一下,如果是一些比较传统的宗教信奉者,在他们看来,生命无论说是一个奇迹也好,还是说生命是上帝创造的,总之在精子和卵子结合的那一刻生命这个路程就已经开始了,甚至有可能有一些东方的宗教也认为,这是非常难地获得了一个做人的机会。所以可以想象到,对于某一种人来说,对于堕胎这件事情的道德厌恶甚至是恐惧,它是真实存在的。常见的区分生命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的为题,“pro-life”也就是反对堕胎权那些人,他们是有相应的反驳的,是用我们之前节目里讲的所谓推及或者说滑坡论证的方式来论证的。他们主张,如果你认为一个胚胎只要没有痛觉,就不能被定义为一个人,也就是说你可以合法地去剥夺他的生命权,这个逻辑成立的话,是不是如果有一个植物人也没有痛觉了,就可以杀了他而不负任何刑事责任呢?支持堕胎权的人,还会说没有知觉、还发育未完整的胚胎,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已经脑死亡的末期的病人。如果我们认为现在已经觉得可以用脑死亡来判定一个人去世了,那是不是就代表着我们在脑子未发育的时候的胎儿,我们堕掉他也不叫做杀人呢?相反其实不支持堕胎的人,他们也有他们的反驳,他们会说脑死亡这件事情还配合着未来它是一个不可逆的。如果今天我们知道有一个人是脑死亡了,但如果我们知道他两个月之后,他的脑子还是有可能活过来的,这个时候也不会“杀”掉他。反过来,虽然婴儿那时候的大脑还没有发育,但是再过几周你知道他是会发育的,还是有希望的,这个时候并不是一个不可逆的脑死亡状态。所以,真正的“pro-choice”支持女性对于自己身体的决定权,和另外一方“pro-life”认为这个胎儿的生命权是值得被讨论及保护的,他们其实各自都有各自的理由,这也是这个冲突非常困难的地方,这也是我觉得是所谓的美国人民群众心中真正在乎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到了最高法院之后却没有被解释。整个美国社会现在争论非常多,无论是法律人士还是政客,每个人都出来发言。但是这么多争论堕胎权的争论,却很少有真的讲堕胎这件事情本身,大家都在讲法律的合理性,应该最高法院还是应该州立。是否意味着法律没有解决和解释人民心中真正关心的问题,就做出了判例,这个判例就决定了大家可以去堕胎?前面提到,“人没有让别人不自由的自由”,这我是同意的。但如果用“你不能干涉我的自由,所以你不能干涉我的堕胎”;这个东西是不是你的自由,取决于这个胎儿是不是生命,堕胎是不是杀人;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直接就说这是你的隐私,你的自由,这是一种循环论证,begging the question,是把心中的结论当作了论据。也许在一个真正的宗教信徒的眼中,他邻居堕胎就跟他邻居在谋杀是一样的,他能不管吗?如果不试图去解决这个共识,大家都抱着自己坚信的这样的立场,而没有真正地去让自己彼此的观点进行交锋,这样的话,这个社会会变得越来越两极化,这是我们担心的一个问题。正方观点3:
詹青云:如果这些人是愿意讨论这个问题的,或许可以全民公投,讨论一下生命是从哪个时刻开始的。就像我刚才说的,绝大部分的人,他们的观点是in between的,生命不是在受孕那一刻开始、但也不是直到出生才开始,但我们现在还看不到这样的讨论。“罗诉韦德案”在美国社会引起了一系列的反应,很多人认为这是美国的政治开始两极分华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在以前还有支持堕胎的共和党人,也有反堕胎的民主党人,两边没有把堕胎这个问题抱成团,但就是从罗诉韦德案判决之后,宗教团体开始紧密地团结在共和党周围,形成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团体,两个党派一步一步地走向极化。我觉得他们不是在理性地讨论生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个东西已经在极端的政治化和两极分化。再来,一个号称说“我因为真爱生命,所以禁止堕胎”的人,他们真的是爱生命、保护生命吗?我一直又一个非常坚定的信念,就是爱具体的人,而不是爱抽象的形式。这个人博爱到连胚胎的痛觉都能够感知,难道感觉不到真实世界里许许多多女性她们真实的痛苦吗?我读到一个故事,有一个女孩,她被人迷奸后怀孕了,自从德克萨斯通通过了“心跳法案”之后,她又没有足够的钱到别的州去堕胎,她就不得不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她和她的男朋友本来计划结婚,然后在他们的婚礼上,她怀着一个因为强奸而怀上的孩子却不能够堕胎。还有的人,19周时羊水就破了,医生告诉这位孕妇,你这个孩子生下来很有可能患有先天疾病,或者出生会有很大的危险,导致你将来再也没法怀孕,但是她没有达到德克萨斯州紧急医疗里严重医疗状况的标准,所以不能堕胎。还有更多的人,可能这些故事没有那么极端,可是她们不是漠视生命的人。有现在的统计表明,在美国大部分选择要堕胎的人并不是那些初次怀孕意外怀孕的青少年,而是那些已经做过妈妈的人。这说明什么?她们不漠视生命。我觉得当有人特别坚定地说我们是 “pro-life”,我们为了生命就是“ban-it”,把堕胎这件事情禁止掉。当他们高喊这些口号的时候,真的在乎生命吗?连一个活着的人的具体的痛苦都不感知,他真的能够感知一个胚胎的痛苦吗?我很怀疑这件事。刚才举的那些例子,我们是不是可以杀掉植物人,杀掉一个脑瘫患者,大家觉得很荒谬,因为在那些故事里没有另一方。在选不选择堕胎的这个事件里,还有母亲啊,是女性要去生这个孩子,要去生一个她不想生也不能生、没有条件养的孩子,她要承受这她的人生和她的未来会被这一切改变。为什么没有人去问问她们呢?她们有没有这个里面的参与权?回到法律本身上来,法律还有一个基本原则:尽可能保持法律体系的稳定。如果说一个已经在社会里被认证了50年的基本权利,就因为特朗普上台以后任命了三位保守派的大法官,其中一位在接受参议院的盘问的时候还坚定地说“罗诉韦德案是国家的法律,他不会推翻它”,就可以轻易地颠覆一项这么重要的基本权利,我觉得这本身对法治社会的动摇是让人很害怕的。最后讲一点就是小故事,写将要推翻罗诉韦德的这个判例的阿利托法官,他在2000年代他是被任命进最高法院来接替退休的奥康纳尔。奥康纳尔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性大法官,有趣的是,当年她是被里根在1980年代任命进最高法院的,因为她是一个保守派的大法官。在80年代,曾经有很多人期望里根任命的大法官能够在当时推翻“罗诉韦德案”。可是奥康纳尔作为一个保守派,在进入最高法院之后,她的观点发生了一些温和化的转化。在很多重要的判例,特别在我刚才提到的1992年的“凯西案”里面,选择了站在维持罗诉韦德的核心判决这个立场上。虽然她改掉了之前的比如说把孕期分成三个阶段的方式,而是把它改成了以胚胎离开母体之后能不能存活作为那个分界点,但是她认同了美国《宪法》的隐私权应当保证一个女性堕胎的权利。在她主笔的这份判决意见里面,有一句很著名的话,经常被引用的话:“At the heart of liberty is the right to define one's own concept of existence, of meaning, of the universe, and of the mystery of human life. Beliefs about these matters could not define the attributes of personhood were they formed under compulsion of the State.”(自由的核心是一种权利,人可以自己去定义,关于存在、关于意义、关于宇宙、关于人类生命的奇迹的概念。如果关于这些概念的信仰,是在国家、是在公权力的强制下形成的,它们不足以定义人之为人的属性。)
一切回到我们最初的那个问题,谁有权利把自己关于这些东西的信仰强加到他人的头上?关于这个问题的信仰,关于这个问题的想法和概念,也许本身就是隐私权的一部分,因为你自己在定义你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今天我们面对的社会,已经极端到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去辩论,生命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该怎么去思考这个问题,而是你支不支持堕胎变成了一个人的政治标签、变成了意识形态标签,标签不一样的人根本没有办法对话,我觉得这才是这个时代最可怕的事情。

或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配图、头图:《坡道上的家》《女人韵事》《四月三周两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