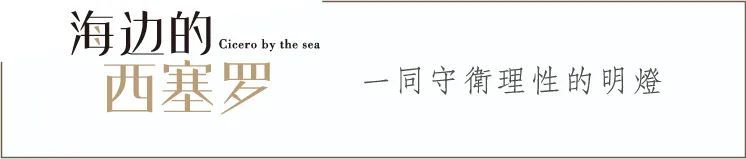
对有些问题,纠结、反复一下并不可耻,
可耻的反而是从没为此类问题纠结过。
有时候,想想会觉得有意思,如果不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近作出的那个最新裁判,堕胎合不合法这个事儿,恐怕很难在我国掀起什么讨论热度。
我最近看了一则材料,根据国家卫健卫生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我国在育龄妇女总量下降的情况下,人工流产量依然居高不下,年均维持在900万例左右(其中有一半是25岁以下的年轻女孩)。考虑到目前中国每年出生的新生儿数量马上要跌破1000万大关,估计再过上不久,堕胎数量与正常生育数量等量齐观、甚至反超的场景都可能会上演。
在日常生活中,你也能感觉到咱这儿很多人不把堕胎当回事——“无痛的人流”“今天手术、明天上班”“意外怀孕怎么办,到大铁棍子医院找童主任”在咱这儿都是段子。大多数中国人对堕胎的态度是比较随便的,立法立规约束一下都还没有列入讨论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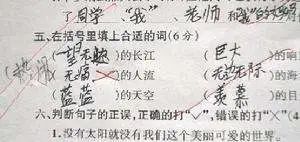
甚至“无痛的人流”在咱这儿都是一个梗。
像美国那样搞成一个撕裂全国的政治话题,就更让我们感觉不可理解。
所以最近网上又有很多人在说,美国人这一“开倒车”,世界上完全不限制女性堕胎的仅剩五个国家:“中国、加拿大、荷兰、越南、朝鲜——都是妇女权益较高的国家。”
但能不能以“允许随便堕胎”衡量一个国家女性权益的先进程度,我对这个事儿是持保留态度的。
因为如果你真以这个标准而论,上追个几千年,人类进入文明的“轴心时代”前,全世界各地茹毛饮血的部落们可能都算的上“很先进”,那会儿甭说孩子没生出来可以随便打,就算真生出来了,也可以遗弃、溺杀。
流经罗马城的台伯河上,有一个台伯岛,在古罗马时代,那里就是罗马居民丢弃打出来或者生出来的婴儿尸体的地方。
而在东方,民间甭说随意打胎,就是随意杀死新生婴儿(尤其是女婴),在很多穷乡僻壤,一直持续到了当代。而你总不能说这些地方的女权也“很先进”——因为很多这种地方,生孩子的妇女都是被拐卖来的。

电影《盲山》中被溺弃的女婴。
从历史上讲,认识到父母虽然生育了子女,却没有对子女随意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这其实是人类的一项伟大进步。它意味着子女终于不再被视作父母某种意义上的“私人奴隶”,而有自己的生存权和人身权利,即便是父母,也不可以随意剥夺。

把孩子当做自己可随意处置的私有物的典范——“埋儿奉母”
但,究竟什么时候将这种权利授予给一个人,这却是一个难题。最简单的方法当然是等到孩子自然分娩,就视为他已经算个人。但人们通过长期的观察发现,当孕妇腹中的胎儿已经足够大时,即便你用人工的方式把它“打”下来,它落地以后也会哭会叫了。这个时候你强行规定这个胎儿不是人,可以随意处置,似乎也与杀人无异了。
那怎么办?所以轴心时代的很多宗教(包括亚伯拉罕三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以及佛教)都有劝止或者禁止孕妇堕胎的教条。
但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医学手段的不发达,这些宗教教条最早所禁止的那种堕胎,指的一般是那些婴儿已经在腹中成型了的中晚期妊娠。
虽然基督教等宗教一直谴责“谋杀婴儿”,但一直到近代科学革命以前,胎儿究竟在发育几个月以后才被视为是一个人,是一个非常模糊概念,在现代专业化医学尚未兴起的时代,欧洲妇女们的堕胎非常普遍,最常见的一种,便是饮用芦荟汁调剂的一些药剂刺激身体引发流产。
欧洲真正第一次尝试界定合法与非法堕胎的界限,是在1803年,英国议会通过《埃伦伯勒爵士法案》(Lord Ellenborough’s Act),把胎动后的堕胎视为一种谋杀——这也是符合当时大多数人观念的:只有当胎儿被证明已经有了意识时,再进行堕胎,才是残忍的谋杀行为。
但随着近代以后人类技术手段的进步,麻烦的问题随之而来了——宗教教条的问题,在于它一旦被订立,就拒绝接受更改。可是科技却是不断进步的,概念是不断延展的,随着早期妊娠被更充分的认识,妊娠这个概念相较于古代,已被大大的延展了,人们认识到胎儿不是在胎动后才有了生命,而是在受精的那一刻,这个生命就已经形成了。
那么一个问题也就形成了:那些刚刚形成的胚胎,算不算是“人”,他们的生命应不应当受到保护?或者按宗教的说法——他们有没有上帝赋予其的灵魂?
这些问题,在古代乃至近代都是从未被讨论的,现代人必须为其重订规范,自己作出抉择。而这个争议,其实也就是美国堕胎问题的实质。
总结起来说,人类历史上,宗教产生了反堕胎的观念,初衷不是一种野蛮的压迫,反而是一种文明的进步——人类开始认识到哪怕是尚未出生的胎儿,也有值得尊重的生命权。但“反堕胎”在现代因医学认识水平的进步,异化成为一种不近人情的主张,这其实是一个现代性问题。
与我们的传统不同,美国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宗教传统的国家。早期北美移民中,有相当的一部分,其实都是被旧大陆驱赶来的宗教团体。这些宗教移民团体,往往都是内部教规十分严格的所谓“团契”(英文Fellowship),会对其信徒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全方位的指导。所以,今天很多在美国一些州(尤其是东部州)生活过的朋友会发现,某些州对你私人生活的干涉其实一点也不少,甚至个别方面,保留着宗教团契的严苛,原因就是如此:人家本来就是这么个团体。是的,很多北美早期的殖民点,本质上讲类似一种居民能结婚、能繁衍后代的“新教大型修道院”。也只有这种组织,能凭着其宗教信念,在北美殖民地早期那种艰苦的拓荒生活中生存下来。当然你会问,如果一个人,出生或者移民到了这样一个宗教移民团里,却不想完全按照其订立的规矩来生活,那怎么办呢?这件事,在早期的美国也好办,因为在19世纪末以前。美国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它的西部是面朝广阔的北美大平原的。那些不赞同原有东部居民点生活习惯的人,可以自己组团,向着西部地区闯荡,等到他们在西部某个地区站稳脚跟,他们自己又可以选举议会、建立政府,制定法令。也正因如此。1787年,当费城制宪会议召开,各州代表签署了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时候,美国的立法者们认识到这份宪法必须遵循“极简主义”、宜粗不宜细。因为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方式千姿百态。各州的法令都不尽相同。于是最初的联邦宪法,只是协调各州之间的关系,规定各州应该自愿上缴一些什么样的权力,以便大家一起组建一个联邦,搭伙过日子。至于各州境内的民众们如何生活,他们的私权与州政府之间的公权应该如何切割?这些问题,联邦宪法原本是不打算、管不了的。各州老百姓,你们自己在州议会里自己商议着办就行了。所以再强调一下,与后世所吹捧的不同,1787年美国宪法的初衷,的确本不打算保障人权——它只想协调州与联邦之间的关系。至于保障公民私权的事儿,美国建国者似乎觉得这个主要应由各州自行搞定。但这样一来,又有了一个问题——美国当年打独立战争,各州合伙造了英国国王的反,最重要“大义名分”是《独立宣言》里的那句话:“我们认为下列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直译应为“人人皆被平等的创造”),他们都被他们的造物主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给这句话背书,联邦政府似乎又必须对公民的个人权利提供直接的宪法保护——否则美国这个国家的合法性也就丧失了。于是1791年,在做过驻法大使、深受法国大革命理想浸润的杰斐逊的力推下,美国国会通过了对联邦宪法10条修正案。这十条修正案,又被称为“人权法案”。它们系统的提出,联邦承诺美国公民拥有言论权、拥枪权、人身自由权、接受公正裁判权等等一系列权利。人权法案当然是伟大的,如杰斐逊所言,只有加上了这十条 ,美国宪法才算向美国公民实践《独立宣言》中的许诺。其一,人权宣言的思路是与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中原有的宪法“极简主义”精神有所抵触:美国宪法原本只是一个联邦与州之间的协议。但现在“人权法案”要联邦越过各州,直接出手保障公民的权利。如果各州对公民的私权的界定与联邦的界定不同,那该听谁的呢?后来美国很多撕裂性的大灾难,都是这个BUG的衍生品——比如南北战争,联邦政府认为按照宪法精神,应该给黑人自由,但南方各州认为,黑人不算人,他们只是白人奴隶主的私产,奴隶主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你硬要侵犯,我就脱离联邦。于是两边就打了起来。杰斐逊声言要保障的平等人之间“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但他却忽略了,这几项权利之间的,有时是互相抵触的。反堕胎者认为:胎儿是人,有生命权,生命权当然要被保障。但支持堕胎者却提醒,很多时候,你们为了保这几个细胞的“生命权”,孕妇的人身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可就被牺牲了——甚至有时,孕妇的生命也会受威胁。你看,在这个场景下,孕妇和胎儿的立场就是对立的。要了一方的生命权,就要牺牲另一方的自由权和而这些权利,可都是《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人权法案》所承诺要保护的,那么请问,你优先保护哪个?《人权法案》连带着整个美国宪法,都没把这事儿说明白。于是成为了一颗定时炸弹。但在美国建国前一百多年里,“堕胎权”这颗定时炸弹,却从没有被引爆。首先,是如第一段所论述的,“堕胎问题”其实是个现代性问题。19世纪的各宗教组织压根无从讨论“受精卵有没有灵魂”的问题,他们只劝止孕妇在有胎动后的堕胎行为。这个主张,就比今天美国很多宗教团体的主张温和很多。其二,是如第二段所论述的,在建国的头一百多年中,美国地理上一直存在一个可拓张的“西部”。这个“边疆”的存在相当于一个社会的减压阀。大量不同意既有州社会秩序的“边民”可以通过向西部移民的方式来“用脚投票”。所以存留在美国既成社会规则内的反体制力量,与旧大陆诸国相比,一直相对弱小很多了。美国各州的社会秩序和法律于是总体能保持相对静态与稳定。第三,虽然宪法中已经埋下了州权与联邦权相抵触的“地雷”,但美国建国早期的联邦是相对松散的,各州总体上在人权等问题上都处于“各行其是”的状态——人权法案说了公民有这个权利,但具体怎么授予,基本还是各州议会“凭良心”。联邦最高法院很少会为类似问题判令州政府“违宪”。因为大家都知道,一旦联邦和州在这种问题上吵起来,就会掀起南北战争那样的灾难。这三个理由,相当于三把锁,锁死了这个争议。但在二十世纪后半叶,这三把锁相继都被打开了。首先是科学技术进步造成的妊娠概念的延展。美国的很多宗教团体,开始用“科学”的方式解释他们笃信的教条,强调“灵魂在细胞受精的那一刻,就已经被赋予了”,于是任何形式的堕胎手术,在他们眼中都成为了一种谋杀。激进的宗教团体要求将所有堕胎技术都视为一种犯罪。而这种主张,又反过来激怒了同期也在抬头的女权主义者,后者高呼“女性有自由处置自己身体的权利”。双方矛盾于是极度激化。其次,随着美国的版图扩张到西海岸,西部各州逐渐建立,为美国社会减压百年的那个“边疆”消失了。最迟到1929年大萧条开始,美国社会中对既成秩序不满的各种“边民”群体,就已经不能再通过“用脚投票”、开拓新边疆的方式去追求自己的生活。想要让自己生活的社会如己所愿,他们只能通过斗争的方式在既成社会里达成。于是种族、男女、阶层社会矛盾开始在美国激增。而这种社会矛盾的激增,又导致了第三点——受到民众压力的联邦政府和联邦法院,开始越来越多的越过过去模糊的州权与联邦权的边界,去插手原本各州自行处理的事物。联邦开始越来越多的教育各州——不行,这种事你不能做,否则违宪。1957年发生的小石城事件,就是这方面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阿肯色州的黑人学生因为种族隔离而将州政府起诉至联邦法庭。而联邦法庭判定州政府违宪。而时任总统的艾森豪威尔直接下令州国民警卫队联邦化,并派出空降兵到该州,强制推行联邦法庭决定。小石城事件,在美国历史上的影响可能不亚于南北战争。因为它让所有对自己所在州的法令不满,而又无法继续“西进”,另闯一片新天地的美国公民看到了一种希望:如果州的法令不符合自己希望,那么就可以绕过州一级,直接向联邦法庭申告其“违宪”,一旦官司打赢,联邦政府就有义务使用强制力逼迫州政府就范。梳理后你会发现,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几乎所有席卷全美的重大社会问题,都是按照这个流程进行的。而这其中,就包括了因此漫长堕胎权争议的罗诉韦德案。不知不觉,已经写的太长了,今天又太晚,就先写到这里为止吧。《美国堕胎案是与非》这个系列,我想我至少会写三四篇文章,今天这篇可能只能算是个序。美国堕胎案的问题,并不像很多人所嘲笑的一般,就是个简单的“开倒车”的事儿。实际上,与随意处置胎儿甚至新生儿的生命的这种古老而野蛮的人类习俗相比,反堕胎(至少曾经)是一种人类文明的进步,它标志着人类开始尊重人之为人的生命权。反堕胎思想的激进与不合理,很大程度上,是在其遭遇现代性之后才开始呈现的。而当代反堕胎与妇女堕胎权的争论,在美国,也至少包含了三个问题的探讨:第一,分权制政府中州权与联邦权之间的权力到底如何分隔,联邦可不可以绕开各州直接为公民立法、赋权?第二,胎儿的生命权与母亲的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之间究竟孰轻孰重?两者矛盾时该优先尊重哪一个?第三,我觉得也是最重要的,在科学革命后的今天,人类该如何理解和重新阐释那些轴心时代留下的训诫?比如人,在什么时候开始才应该被视为一个人?人的基本权利,又是何时才被赋予的?我觉得,人类,在这些问题上各执一词、纠结、反复,并不丢人,因为它们都是关乎人何以为人、文明又该向何处去的“元问题”。就像一个正常人会为“你妈和你媳妇掉水里了你该救哪一个?”而犯难一样。相反,我觉得:有些问题,纠结一下并不可耻,可耻的反而是从没为此纠结过。这就好比,你跟一个没学过数学的人,说哥德巴赫猜想的“1+1”问题是难题,他可能会说“很好解啊,不就等于2吗?”你觉得一个问题简单,没啥可纠结的,有时恰恰可能意味着,你还没有迈上解题的初阶。本文6000字,感谢读完,长文不易,若期待下篇,请给个三连支持一下,鼓励我尽早肝出来,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