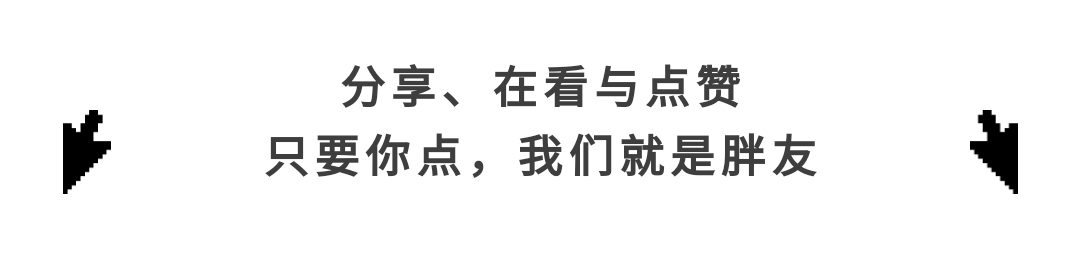凤凰网原创
这三年,电影行业经历了至暗时刻,也迎来了乍现曙光。一个行业过山车式的悲欢,更凸显了它的脆弱性。
来源:凤凰深调(公号ID:ifengdxw)
作者:燕青 傅一波
电影院像是坐上一列呼啸行驶的过山车,触底后突然再次进入了极速爬坡轨道。截至发稿当日,2023年春节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亿元。春节档票房前三分别为《流浪地球2》、《满江红》、《无名》,实时票房分别为6.65亿元、6.09亿元、2.26亿元。而距离大年初一还有3天,预售开启仅5天,春节档七部新片预售总票房已经突破2亿元。“春节档是每年的第一大档期,电影院回血的时刻。”山东天悦影管公司总经理田甲提到2023年的春节档,有些激动,“今年春节可能是近几年来,中国电影阵容最豪华、质量最高的一届了。”而就在两个月前,电影院还躺在谷底。截至2022年10月底,中国停业影城的数量累计超过47000家,其中还包括知名连锁影院英皇UA电影城在上海、深圳等地开设的7家门店。“自开业以来最艰难的时候和挑战,议决不再对其额外注资。”该影城在申请破产通告中这样写道。“《阿凡达2》算是提了一口气。”田甲告诉凤凰深调,挺过断断续续暂停营业和无片可播后,电影院们背着高昂的房租,等待已久。11月底《阿凡达2》定档后,随着75%上座限制令解除,影视业内曾做出30亿票房的乐观估计。“现在看来,20亿都有些乐观了。”田甲说。
广东某电影院老板表示,旗下一家影院在《阿凡达2》上映当天上座率终于超过50%,但随着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城市迎来大规模感染,电影口碑也不如预期,并没有迎来想象中场场爆满的景象。
2022年3月起,这位老板曾连续两个月内陆续关闭、拆除了手里的四家影院。拆除现场时,他亲手用锤子一块一块敲碎影院墙壁,用折叠小刀划破价值约十多万元的IMAX影厅荧幕。“卖了也没人用得上。”他边划边大声笑的视频在社交平台上引来围观。11月,成都莱纳星影院发起那场令人心酸的自救活动,面向上班族推出不到20元每人的电影院午睡服务,午睡套餐包含蒸汽眼罩和热饮。海报一度登上微博热搜,网友替电影院感觉泪目,“过得太难了。”
|11月,成都一家电影院午睡服务海报,来源:成都莱纳星影城公众号
这样的经历让经营者面对春节档预售票房时,笑中也带着泪。无论是观众,还是从业者,要重拾信心和对未来的预期,除了票房以外,或许都需要某些更确定的东西存在。
最近,田甲时常翻看电影院经营数据,对比近几个月来的票房情况。今年是他从业第13个年头,旗下有六家电影院,集中开在二、三线城市。2023年1月刚过不久,其中一家在三线城市的电影院,排片场次就超过570场,观影者超过3400人次。这是12月全面放开后,《阿凡达:水之道》带来的客流。而此前,2022年11月,这家电影院一整月排片不过590场,分账票房只有2.5万元,观影者未达800人次。田甲告诉凤凰深调,虽然不如预期那样,有“救市”般的票房表现,但电影院还是能靠着这部全年唯一的海外大片,续上久违的一口气,撑到春节档。眼下,观众重新回到影院的速度已经超过他和同行们的预期,他没有料到,在经历大规模感染时,这座城市的人们出门的积极性如此高涨。在一线城市上海,元旦当天下午,市中心一家电影院静安大融城寰映影城里,票价最高的IMAX观影厅座无虚席。该影城副经理鲁赟舜表示,《阿凡达2:水之道》上映以来,IMAX厅的上座率平均在70%以上。在宣布定档的时刻,《阿凡达2》立即成为电影院手中稻草的原因,因为“太久没有米了”,田甲说。影片是电影院维系生存的核心,质量高的影片加之合适的排片,能够带来观众,有了客流量才能接收益更高的广告。他粗算了一下,囊括房租、电费、人员工资、设备维修等费用,一家二三线城市的电影院每月的开支在30~50万元间,2020年以前,正常的卖票收入刚好能支付每月开支。然而,2022年一整年可播的影片数量刚刚超过300部,只相当于2020年疫情乍起后的半年数据。据万达影视数据中心、灯塔专业版公开数据,前三季度,已经定档待映的影片包括《长空》、《深海》、《中国乒乓》等38部撤档、换档。除此之外,新片储备捉襟见肘,国家电影局公布的2022年前八个月备案、立项数量显示,4、5月立项备案的电影数量均同比下降超过70部,6~8月备案数量均同比减少超过50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电影少到根本不用花心思排片。”田甲表示,2022年,能在电影院放映的影片屈指可数,12月前,漫威、迪士尼等进口片一部也没能上映,经常能见到一天只有两场电影可看的情形。无片可播是一方面,随时配合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停业时间,又是另一种困境。田甲算了算,他管理的影院2022年总共暂停营业了8次,每次时间1周到3周不等,每家店累计停业时间有2~4个月。“每回遇到人流量大的档期,比如五一、十一、清明、端午、暑期,无一幸免,都停业停过去了。”在两重困境之下,影院收入同比下降了3~5成。田甲影院的员工们大多数面对的是空无一人的放映厅,和依然需要开启维护的放映机器。好消息一个接着一个传来。除了春节档的7部华语片外,春节前夕,1月18日,漫威的两部电影《蚁人2》和《黑豹3》宣布定档2月。“这是继2019年中国内地上映2019年的《蜘蛛侠》后,三年来第一次引进漫威电影。就在上周五,未来定档上映的电影已经陆续排到了5月份。”元旦档刚过,田甲憋在心里一年的一口气终于舒展开来,他通知员工开一次年终会议。会上他告诉大家:“最艰难的时候过去了,我们会越来越好。”据电影业人士介绍,像今年这样稳定的情况许久没出现过,2022年大多数影片都是“火线定档”,甚至临近上映前几天才定档,“提前几个月定档,给电影足够的宣传时间,就能让观众更了解影片的情况,电影院的票房自然会好一些。”事实上,制作电影的周期通常长达1~2年,疫情期间,不少制作团队延期甚至取消拍摄计划,而这样的影响没那么快消除。而且,嗅觉敏锐的投资人感知风险后,早已四散而去。厚德前海基金董事长、合伙人陈宇键曾在2021年北京电影国际节表示,国内一年如果立项的电影在1000多部,其中只有一半的电影能拍完,30多部电影能够上映,仅十几部能收回投资。业内一位出品人告诉凤凰深调,2020年后,在诸多不确定因素叠加影响下,投资影视制作项目更是成了“赌局”,愿意投入的资金越来越少。“比如,因不可抗拒的政策调整,导致拍摄地点临时更改,周期大幅延长,受档期影响,原本定好的演员也会不断调整,每一次变动对于电影制作而言,都是成本的堆积。”他表示,近年来,观众未能看到的影视作品背后,多有这些难言之隐。聚本影业创始人王鲁娜告诉凤凰深调,三年以来,上游影视制作公司面临业务停滞,时间成本和现金成本大大增加。“大体量的项目无法开机、无法出国拍摄,有些影片有特定的自然环境需要,也无法临时改变计划,换场地或是缩短拍摄时间。制作时间无限期延长意味着会错过一些好的上映时点。”“如果没有疫情的话,现在王玮瑛应该在项目开机现场,或者在新的地方勘景。”2022年5月底的一天,28岁的影视宣发王玮瑛即将离开重庆,回到北京。坐在前往高铁站的出租车上,她给朋友发了上述一段话,紧接着,又写了一句“熬不住了,我回去就辞职,转行。”此前三天,本该开机的项目地点因疫情原因不能使用,总制片一大早就来电通知,原来的拍摄计划取消了。王玮瑛从南京艺术学院毕业后,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够做制片人。她从电影宣发开始做起,为一部电影从投资到上映的每个阶段设计宣传方案。进组后,要做的工作很多,一个人掰成两瓣用,除了宣发,她还要兼职剧务,跟进电影项目中,从出品、剧本、立项、选景,再到导演、演员的进组、拍摄、成片、宣传、上映的每个环节,处理日常事务。“这是因为电影项目预算越来越紧张,要节省人员开支。”王玮瑛说,即便如此,这些她都能坚持,因为这就是通往制片人的职业路径。但,2022年接连取消的拍摄计划,压碎了王玮瑛的梦。就在她摩拳擦掌参与一部总投资过亿的项目后不久,又被通知“拍不成了”。这是她2017年从业以来遇到的最大的悬疑电影项目,编剧就阵容强大,资深大编剧手下还有10个小编剧加班加点调整剧本——显然,这部电影的工作会给她的简历添上一笔光彩。然而,甚至来不及沮丧,她便要开始一系列的工作,“劝退”到场的剧组工作人员:申请公司的备用金,为导演、摄像、演员等31名工作人员定票,安排返程。不少有名气的演员经纪人急切地抓着她问:项目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临时取消?后续的该怎么调整?档期被耽误了之后,怎么补偿?当天深夜,剧组订票返程的事宜才算告一段落。第二天,王玮瑛和制片、摄像还需要到拍摄现场处理场地租金、清点仓库内的设备并装车发回北京。“有没有可能先不动,情况有好转再回到现场?”她问道,毕竟租金不能退。可从2020年开始,类似的情况经常发生。“有时整个拍摄组的设备会因为种种原因滞留长达几个月。如果此时其他地方可以开机,也会延误整个拍摄进度,造成巨大的损失。” 王玮瑛告诉凤凰深调,选择打道回府实属无奈之举。看着一辆塞满设备的厢式货车离开,王玮瑛拍下照片发到工作群后,马上转回酒店处理下一件事。王玮瑛遇到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2022年全国各大影视基地受疫情影响,均有不同时长的关停措施。国内最大的影视基地横店曾公布,2022年4月在场剧组数量比去年同期下降近50%,剧组无法开工的原因主要有二:主创人员因封控,团队无法顺利开工;出品方直接撤资,无钱可拍。2022年6月初,王玮瑛失落离职。而在她之前,还有不少原本电影从业者,迫于巨大的不确定性带来的生计问题,兼职或转行。比如,影视编剧。杨恺在编剧行业工作了11年。行业内常有的一句话:“三年一小限,五年一大限。”意思是,一般小编剧入行至少要熬上五年,才能出头。他很幸运,2015年就写出了一部院线电影剧本,跃身成为小有名气的知名编剧,虽然那时一部电影剧本的稿酬只有7万元,他还是很得意。好景不长,第一部之后,接连几部戏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法上线:一部戏中,主演涉及犯罪,另一部戏是题材涉及到敏感问题。2017年前后,杨恺所在的企划公司参与的几部电影,因为剧本审核不通过,立项失败,公司损失惨重,不得不缩减人员。他成了第一个被裁员的员工。他回到了贵州老家,成了父母眼中的“无业游民”。后来,他只能兼职接一些剧本撰写工作,好歹还有一些存款,他不愿放弃靠写电影剧本谋生。2019年末,存款耗尽,他也赚不到够生活的钱了。由于经常拿不到尾款,行业内的年轻编剧迫于生存压力,只得给人当“枪手”,非但得不到署名权,还拿不到应得的费用。他开始接各种各样的工作,写广告剧本、儿童剧本、MV剧本,运气好时一个月能有上万收入,但大部分时间每月收入维持在5000~6000元。2022年,杨恺等来一个机会,以第二编剧的身份参与一个电影项目,计划年底开机。不幸的是,临到开始工作时,出品方却告知拍摄计划取消了。他托人辗转问到,是投资方觉得“苦难”题材容易出问题。“几千万、上亿的资金下去,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杨恺苦笑,2022年,因为疫情等不可控因素,大部分他接到的电影项目都停留在“PPT”阶段,他自嘲甚至能够站在资方的角度看待拍摄计划取消这件事了。事实上,电影拍摄的不确定性在五年前就已经初露端倪,许多拍摄技术人员不再把电影当作工作重心。参与过新少林寺拍摄的灯光师李炜已经从业二十年。他还记得入行拜师时,喝的一碗拜师茶是什么滋味。那时,电影行业蒸蒸日上,像一架无人可挡的马车,人人都想上车入行,年轻人们扎堆拜师,灯光师被剧组敬一声“灯爷”,他一边仰望着师傅,一边干活。几年时间,他从搬动器材、调整拍摄灯的助理,一路做到拥有设计能力的大助,八年前成为能带领团队、独当一面的灯光师。2018年开始,原本与他约定好拍摄时间的项目,经常被通知“无限期延迟拍摄计划”,或是因为不可抗拒的力量取消。那一年,导演戚健的团队找到他,希望他负责一部戏的灯光设计。制片主任把他拉进统筹工作的群里,开始排期工作。当李炜空出自己的时间准备进组工作时,群里却发布了一条取消拍摄计划的通告。“原因是不让拍,限制这个限制那个的。制片主任就告诉我们,下一个项目再汇合。”他说,像这样的情况往后越来越多,有些项目虽然不明说取消,但一通知延期就是整整一年,“我的其他时间也需要用来工作,每一个项目都需要事先把时间空出来准备好,突然延期和取消都会影响到我下一个工作,也会影响我的收入。”此后五年内,他接到了超过十个临时延期、取消的项目。2018年,李炜连续一年没有收入,为了节省生活成本他只能回到老家。妻子看见他没有工作,成天催他出去干活。他每天只能装作上班的样子,不敢在家久留。“我只好联系各种朋友,求他们帮忙介绍一些别的需要灯光师的活,比如小微电影,甚至是短视频。”有一天,他意识到,再也无法依靠电影为生了。“世界好像正在改变。我以前觉得参与电影拍摄很酷,现在别人能叫你一声‘灯光老师’就不错了。但我不在乎了,好像为了生存也无所谓。周围依靠电影的技术人员,比如摄像、道具,也要么转行,要么开始做别的种类的拍摄了。”他在剧组认识的一位道具,在2022年时回老家接受父亲的工作安排,做起了绿化设计相关工作。2020年疫情初起,李炜开始踏足不熟悉的广告圈。在他看来,比起长周期、不确定性极强的电影项目,参与为期1~2天,最多1周的广告拍摄,更稳定。从那时起,参与电影项目成了他的“兼职”工作,与电影拍摄有关的工作一年不超过2个。
|电影《满江红》剧照
04、电影圈看起来还是欣欣向荣?
两天前,影展官方公众号发布了一篇题目为“第六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定于1月14日开幕”的推文,以此宣布影展经历推迟之后,即将重新开幕。“在第一轮感染正在步入后半段的时期,平遥影展的突然宣布回归难免让人觉得意想不到,但如此的举动也给‘大病初愈’的各位电影人、电影行业一丝未来的曙光,平遥影展的回归或许也代表着从2023年开始,自2020年以来受影响的各类社会文化活动,尤其是电影类活动都有回归、复苏的可能。”影展官方公众号如此评述,与以往不同的是,“作为以往每年热度最高的国内电影盛会之一,这一年的平遥影展就好像被公众所遗忘了一般。”
|平遥电影展
正式公布开幕日期前,王玮瑛的前同事提前一周发来邀约,让她一起去现场放松一下。王玮瑛有些心动,半年的时间里,她只进了一次影院,没看什么电影。来回拉扯没几句,她便决定到现场去。当晚7点,影展的欢迎派对开场。她见到即将在春节档上映的电影《无名》的导演程耳,还在出入口看到了一身朴素装扮的王传君。王玮瑛拿着茶点站在一旁,看着越来越多的人聚集起来。贾樟柯最后这样总结:“怀抱热情,拥抱电影,这就是平遥。”似乎电影圈看起来还是欣欣向荣?王玮瑛心里打了个问号。影展期间,她每天在电影宫看五六部电影,直到凌晨才回到民宿休息。平遥很冷,晚上气温有时到零下7、8度,街上空无一人。走在路上,她想,毕业后的几年里,追求的“电影梦”是什么,她有些犹豫,还要重新回到电影行业吗?她订了回湖南的车票,想先回老家和父母一起过年,她买了春节档的电影票,想和父母一起去看电影。“一家三口人坐在电影院,我坚持让他们在座位上坐到片尾,给爸爸妈妈指出字幕里我的名字,在银幕里向上滚动过去。”这是王玮瑛一直以来的工作动力,今年春节档的任何一部影片都无法实现这样的场景。“不知道,也许有一天还会实现?”王玮瑛的问题,最终还需要靠时间来回答。凤凰网财经官方微信 ID:finance_ifeng喜欢此文,欢迎转发和点在看支持凤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