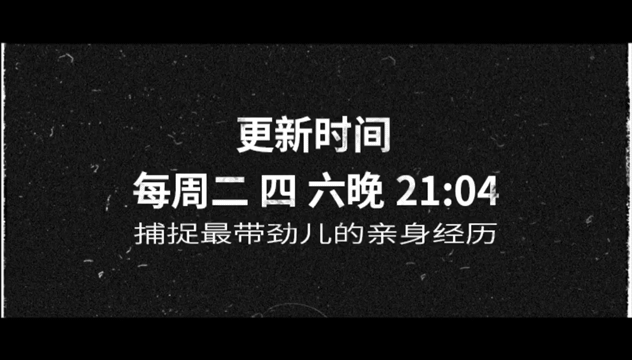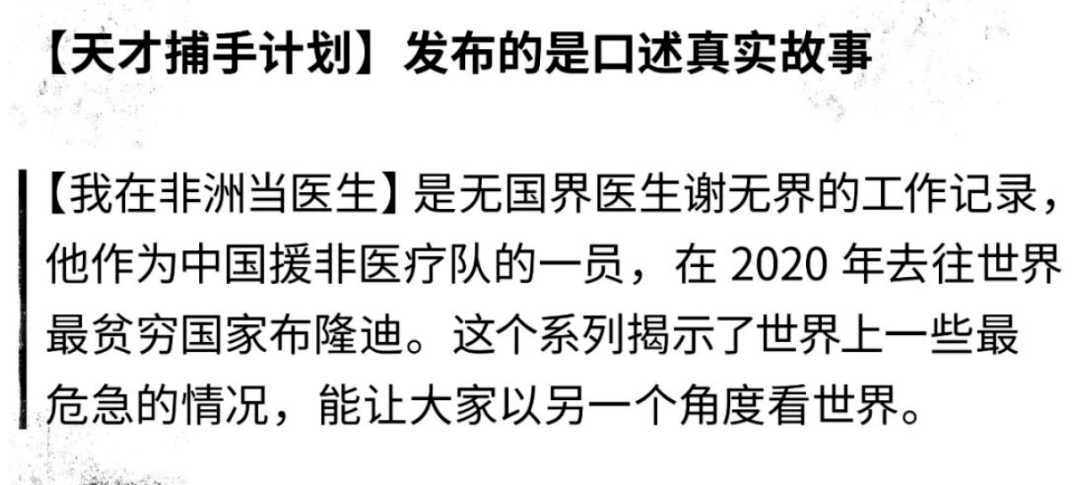
大家好,我是陈拙。
先给你看一个我们身体上的器官↓

这个东西叫“悬雍垂”,俗称小舌头,长在我们舌头后面。
一般来说,它是用来保证你吃饭的时候不呛进鼻腔里的。
但援非医生谢无界告诉我,在非洲,有很多巫医都盯着患者这个器官,没事就想割掉它。
因为小舌头切掉以后出血贼多,看起来是个厉害的手术,但伤口又很好愈合。
巫医宣称做了这个手术能治咳嗽、发烧甚至偏头痛,其实全是扯淡。
但谢无界见过最离谱的,反而是一个病人家属。
有个父亲拜托谢无界,帮忙把他儿子的悬雍垂割掉——
他说这能治他儿子的不听话。

来布隆迪当援非医生之前,有前辈再三提醒我们,说到了非洲一定谨言慎行,否则一不小心,那都不是医疗事故,而是外交事件了。之前有一个医疗队的队长,想给自己队员买救命药。药店不认中国医生的处方笺,那队长情急之下就把药店的门给踹开了,抢了一盒药回驻地。结果第二天,布隆迪的外交部跟着卫生部,直接找上中国大使馆了。事情最后具体怎么解决的,我不清楚,只知道国家大使出了面,那个队长跟对方道了歉,应该还赔了钱。但当我被一个黑人父亲冰冷的目光上下打量的时候,我忍不住又想起了那个外交事件。就在刚刚,我给他儿子瑞纳开了三项检查,花费5万布隆迪法郎,相当于当地人一个月的伙食费。这个黑人父亲一语不发地站在旁边,一米八的大高个,有种说不出来的压迫感。我不禁想,如果中国医生在非洲被医闹了,大使馆会帮我吗?最开始,我没听太懂瑞纳父亲说的病因,护士告诉我,他说他的儿子“呼吸的声音太重了,一个孩子不应该有这么重的呼吸声”。我推断说的应该是打呼噜,还想再询问几句病史,瑞纳父亲就指了指桌上的检查器械,示意我,应该先查体。但我的手刚碰到前鼻镜,瑞纳便像受刑一样发出了尖叫,同时拼命地在椅子上将头后仰。几乎同时,瑞纳的父亲立刻蹲到了椅子后,熟练地用双臂紧紧地勒住了瑞纳,让孩子把嘴张开。我赶忙把手里的前鼻镜换成压舌板,配合瑞纳的父亲,把孩子的嘴撬开。瑞纳还要挣扎,父亲吼了一声“瑞纳”!就像咒语一样,孩子被定在了椅子上,只剩身体还在诚实地抖个不停。他的眼眶里还有眼泪水在打转,好像在哀求我不要把器械放进去。
我一面安慰着全身僵硬的瑞纳,一边迅速完成了检查,没有发现任何可能导致打呼噜的异常。
在我看来,这种情况应该是问题不大,可以先吃点药,进行实验性治疗,后期再随诊。但瑞纳的父亲没说话,拿起我刚放下的前鼻镜仔细观察了一下,甚至捏了几下把手,露出了失望的表情。器械检查看不到最重要的鼻咽部,非洲能用的只有X线。但就非洲的人均收入来说,X线可以说是相当贵。所以这是一个比较鸡肋的项目,大部分病人到这里就没有下文了。在非洲医院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开出了三个以上无阳性结果检查单的医生,是要受到处罚的。这是由于医疗花费对于普通非洲人来说实在是太贵了,他们得预防医生坑病人的钱。我十分紧张,拿出了最高的“国际会诊”规格,给国内的影像科同事打了个视频,找他们指导本地医生配合我拍片。但片子结果出来,我颠来倒去看了好几遍,还是没问题。
不是扁桃体发炎,不是鼻甲肥大,也不是腺样体肥大,还能是什么呢?我凑近瑞纳看了又看,甚至把耳朵贴近了仔细听了起来。“听到了没,就是那个!”瑞纳的父亲突然喊了起来,甚至面露喜色。我以为自己聋了,又仔细听了一会,好像真的有,几次呼吸当中,会有稍微重一点的一声。“呼吸声重”,原来说的不是打呼噜,就是日常呼吸中这么细微的一丁点区别。我甚至有点佩服瑞纳的父亲了,虽然我也有孩子,但是真的要我从日常生活中,找出这么细小的问题,我可能永远也做不到。我问瑞纳,是否有鼻子不舒服导致你用力呼吸的情况?你可以对此打分,0分是一点都没有,10分是非常严重,无法忍受。他父亲就像刚才那样,除了用严肃的目光盯着他以外,没有过多的动作。我长舒了一口气,确诊了,轻微的鼻翼肥大导致孩子会用力呼吸,呼吸声就会有点变化。我给瑞纳开了一瓶鼻喷激素。临走,我又追问瑞纳的父亲,你觉得瑞纳应该打几分?瑞纳的父亲回以微笑:“我不清楚孩子的感受,但我觉得,孩子出现问题一定要尽早治疗。”晚上回到驻地后,我和同寝室的袁大夫聊起了这对父子,没想到袁大夫告诉我,他们也去了眼科。瑞纳的父亲说孩子总是不自觉地看右下或者左下,袁大夫诊断为间歇性斜视。袁大夫同样觉得瑞纳父亲很细心,管教严格又舍得花钱。“就是好像不太相信我的技术,总是催着我用器械给他儿子检查。”没想到刚过了两个礼拜,我竟然又在耳鼻喉科看见了瑞纳父子。瑞纳的父亲用近乎控诉的音调说,他儿子总是在不自主地咽口水,“喉结移动的频率像个变态”。但他好像失聪了一样,径直走到我的身边,很自然地在消毒好的器械里翻找了起来。我反应过来想制止他,结果瑞纳的父亲居然在杂乱的器械堆里,翻出了压舌板和间接喉镜。我有点恼火,让他离我的桌子远点,“我知道该怎么检查,不用到你来教我。”这一次,我可以清晰地看见瑞纳的喉结确实在频繁地上下活动,甚至可以听见咽口水的声音。而且,呼吸声重的情况变得更严重了,基本每次呼吸都伴随着鼻翼扇动。瑞纳的父亲又一次麻利地控制住了儿子。瑞纳不像上次那样挣扎了,可是看到我清理喉镜,泪水还是滑落了下来。他似乎知道这个检查会很难受,是还在别的地方做过检查吗?但没有病历看,我还是只能配合瑞纳父亲,用手拽住孩子的舌头,把喉镜塞进了他的喉咙。布隆迪没有专用的麻药,喉镜强行塞进喉咙深处,还要上下左右不停调整角度。我想起上次做X线的时候,瑞纳在拍片区一直小声地啜泣,似乎是怕黑。X线拍片区只有一台机器,光线不好之余还很狭窄,孩子进去一般都会害怕,多数父母就会主动要求陪着孩子。但我数次用眼神和招手向瑞纳的父亲示意,让他穿上铅衣过去,瑞纳的父亲却好像没看见一样。自始至终,他都是表情严肃、一动不动地站在玻璃那边盯着瑞纳,看着他流泪,看着他拿脏兮兮的袖子擦着挂在脸颊的泪水。我还没反应过来,就见他猛地挣脱了父亲,抬手捂住嘴,呕吐物从指缝中流出来。瑞纳试图用双手接着,同时立马跳下座椅向洗手池跑去,但还是有很多东西溅到了我的衣服上。瑞纳抱歉地看着我。刚才那一推,应该就是他怕弄到我身上。他越懂事,我越心虚。因为刚才这一通检查,我又什么都没看出来。
“头晕吗?头疼吗?眼睛不舒服吗?你近期受过外伤吗?喝了很烫的水吗?”我几乎把所有可能性都问了个遍,瑞纳一直摇头,最后我再一次想到心理问题。瑞纳的父亲听到这里,突然上前一步,反问什么是特殊的事情?我说就是以前不常做,但最近一直做的事情。瑞纳吞口水的情况是新出现的,可能是近期生活中出现了什么刺激源。瑞纳的父亲若有所思地嘟囔着,接着突然双手合十并向我表示感谢,然后就拉着瑞纳匆匆地离开了诊室。我本想追出诊室问他想起了什么,但后面病人堆得太多,我也只好作罢。晚上回到驻地,我立马把今天看诊的情况告诉了袁大夫,他也渐渐觉得有些不对劲。我们讨论了一晚上,不得不承认,我俩有可能误诊了。瑞纳的身体就是没病,他的症状应该往心理甚至精神方面找原因。我三更半夜地打扰了国内一个心理学的师弟,最终得出结论,如果把呼吸声大、斜视、清嗓子等症状并在一起考虑的话,瑞纳可能是抽动秽语综合征。这种精神系统疾病可能来自遗传、脑损伤等原因,如果不尽早干预,后期可能会极大地影响患儿的智力发育。而他父亲虽然严厉,在带孩子看病这件事上,确实一点不马虎。是我辜负了他们。愧疚感一直萦绕在我心头,我四处打听,想再见到这对苦命的父子,把诊断结果告诉他们,看看还能不能帮上什么忙。结果,我没有在医院再见到他们,倒是医疗队的厨师高师傅听说我在找人,神神秘秘地说,要带我去个“好地方”。那是一个被铁栅栏围起来的二层建筑,门口有草地,摆着许多塑料椅子,有点像当地举办婚礼之类大型聚会的场所,但又插着美国国旗。我们三人一块上了楼,楼上是一个阳光明媚的阶梯教室。今天似乎有演出,舞台上坐着一排人,老的少的、黑人白人都有,都穿着很体面。
还没来得及跟他打招呼,屋子里突然响起了热烈的舞曲。瑞纳就坐在靠近音响的位置上,我担心地看向他。抽动秽语综合征的孩子,是很容易受到大噪音的影响,出现异常反应的。但我看到的瑞纳不但没有发病,反而跟着音乐跳起舞来。他甚至有一段独舞,舞蹈动作既美观又富有力量,眉宇间透露着我从未见过的自信。
我们一行人在不远处静静地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本着不能漏诊的原则,我特意加长了观察的时间。
跳完舞又唱歌、和朋友们聊天,足足半个小时,喘粗气、斜视、咽口水这些症状瑞纳一个都没有,更别说“抽动秽语综合征”了。看来,我们又一次误诊了,我们的小病号根本什么毛病都没有。回去的路上,袁大夫告诉我,他原本是听当地人说这里可以唱歌放松,来了一次,偶然发现了瑞纳。后来他们前前后后又来过4次,每次都能碰见瑞纳,每次都和这次一样,舞姿潇洒,看不出任何有病的症状。想想有两次活动正发生在当地的农忙时节,也许,瑞纳就是个因贪玩装病逃避劳动的孩子罢了。想到同样被瑞纳蒙在鼓里,还几次带他看病的父亲,我气得念了一路“小兔崽子”。我想告诉瑞纳父亲这个真相,没想到几天后,瑞纳的父亲又带着瑞纳来看病了。瑞纳的父亲不知道从哪听说,切除瑞纳的悬雍垂,可以治疗瑞纳现有的症状。悬雍垂就是人的小舌头,可以避免食物呛进鼻腔里。有的人悬雍垂特别长或者长了肿瘤,也可以切除,但是它跟鼻息重、吞口水之类的症状,没有任何关系。
更何况瑞纳根本没有病。
我不好直接揭穿说你儿子在装病,只好试探地问他,上一次说到的心理问题是怎么回事?瑞纳的父亲见我并没有极力反对手术,一下像找到了战友,抓着我开始滔滔不绝。他说瑞纳早先是个特别听话的孩子,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并且十分仰慕身为父亲的他,“我就是孩子的榜样”。说到这里时,瑞纳的父亲不自觉地昂起了头,背也挺直了;而瑞纳却正相反,头比任何时候都埋得低。瑞纳父亲丝毫没有觉察到气氛不对,继续自顾自地说着:就在最近半年,瑞纳去参加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学校”,变得不像以前那样听话了,还开始“用一些奇怪的话”顶撞父亲,“甚至连我的拳头也不怕了”。上次问诊时我说病因可能在于“特殊的事情”,瑞纳父亲立刻意识到,一切的源头就是那个“学校”。就像撕吧待宰的小鸡仔那样,瑞纳父亲一把将儿子拽了过来:“看看你现在被这些无聊的东西弄成什么样了!你究竟要花掉我多少钱!”当着我的面,他狠狠地给了瑞纳一个耳光,鲜血从瑞纳的嘴角渗了出来。鼻翼扇动、眼珠向下、吞咽口水,之前说的症状一一开始出现。瑞纳没有装病!他的病根,不是那个“学校”,而是他父亲的暴力。
小时候我成绩不好,人还很调皮,有一次趁老师不在,在自习课上带着同学们捣乱,结果被抓住了。老师没有体罚我,只是让我当众唱歌。我不明所以地唱了。唱完老师就皱着眉头批评我唱得难听,接着挨个问班上的同学,他唱得好不好听?这一次之后,我突然“不会”唱歌了,一张口就不知道怎么发声。见到老师手不知道该放哪、路不知道怎么走。他根本不是来我这看病的,自始至终都不是。他只是不满意儿子为什么不听他的话了,就觉得儿子有病。从最开始,他就迫切地催促我们用器械检查,不管瑞纳怎么挣扎哭泣,都板着一张脸——因为这就是他惩罚孩子的方式。而我因为怕找不到病因、怕被质疑,一次次地给孩子增加检查,也成了瑞纳父亲的帮凶。我已经长大了,还是一名医生,可是我的权威也不能说服这个父亲,他只相信自己认为的正确答案。我想了想,板起脸告诉瑞纳的父亲,这个手术我在中国常做,而且完全免费,只要准备一晚,明天你就可以带着孩子来。我让护士起草了一份手术同意书,让瑞纳和瑞纳的父亲签了字。接着,我和袁大夫就穿着白大褂,把瑞纳领到了手术室里。瑞纳像打摆子那样抖个不停,眼睛一直瞟着手术床边寒光闪闪的手术器械。我和袁大夫对视一眼,我摘下了口罩,对瑞纳说:“我不喜欢你的舞姿,你的胳膊太僵硬了,不灵活。”袁大夫紧接着也摘掉了口罩,解释说,我们在那个学校看见你潇洒的舞姿了。他甚至学了几下,笑吟吟地跟瑞纳说,喏,你的胳膊就是这样的。我一屁股坐到了手术床上,用白布盖住了盒子里的手术器械,告诉瑞纳说,我们今天不给你做手术。“因为你不需要做这个手术,你没有病,病的是你的父亲。”昨晚,我和袁大夫商量好,要一起给瑞纳做个“假手术”。以他父亲的自负,我们光拒绝他,他只会找别的医生,甚至巫医去做,到时候对孩子的伤害更大。我们本打算把瑞纳迷晕,睡够时间再推出去,但今天看到他,我又改变主意了。我能做一场假手术,下次呢?瑞纳父亲会不会继续认为,只要找医生切掉孩子身上的一个什么小东西,孩子就能永远听话?我要把一切都告诉瑞纳,让他自己做决定,自己保护自己。袁大夫喊着风险太大了,要和瑞纳做“碰肘礼”,以免瑞纳出卖我俩。瑞纳绷着小脸,高高地举起胳膊肘,碰在了袁大夫的胳膊肘上。我们两个大人,一个小孩,在手术台上并肩坐下,等待“手术结束”。瑞纳小声说,父亲确实很烦我,因为我的母亲就是我害死的。
最初他不明白什么叫做“害死”,后来邻居才告诉他,他的母亲是为了产下他死在了手术台上。家里也找不到一丁点母亲的东西,据说是被父亲都烧了。而父亲也不允许瑞纳说自己害死了母亲,每当他提起这个话题,父亲就会抄起棍子狠狠地揍他。父亲是村里私塾的老师。瑞纳白天在私塾听父亲讲课,晚上又跟着父亲回家。不像国内有义务教育,布隆迪学校很少,只有不到一半的孩子能上学。有的地方就会自己攒一个私塾,选村里比较有声望的人当老师,把剩下的孩子送进去。小到餐桌上刀叉摆放的位置,大到瑞纳该交什么样的朋友,瑞纳的父亲都有指导。早上下床的声音过大会挨打,吃饭吃得过快要挨打,甚至连上厕所的时间过长也会挨打。但被打的最惨的一次要数那次在酒吧里。他本来是去酒吧找父亲回家,结果因为看见父亲时“没有低头”,被打到了昏迷,甚至进了医院。瑞纳犹豫了半天,说,也许因为他看见父亲喝酒,埋怨了一句:“皮埃尔说得对,黑人真的懒,所有的钱都用来喝酒了。”瑞纳的眉毛和嘴角一下就飞了起来,他说,皮埃尔就是那所“学校”的负责人,他是一个白人,懂英语,会唱歌,从来不打他,还教了他好多东西。自从皮埃尔和那所“学校”出现,村里的孩子们都不去父亲的私塾了。父亲原本没有什么意见,可是当瑞纳兴冲冲地跟他说皮埃尔教了这个那个,他又总是很反感的样子。瑞纳说,也许是因为自己总能从学校领回去奖品甚至是奖金吧。我和袁大夫表示希望帮助瑞纳寻找专业的机构帮忙,但意外的是,瑞纳拒绝了。他说他和父亲相依为命,本就失去母亲的他和父亲一样,不能再失去彼此了。在那所“学校”里,除了英语,瑞纳还学唱歌。其实他并不喜欢唱歌,说是为了唱给父亲听。他也明明记得,之前父亲那么吃力地教着他们英语,“总是在教我们字母”,课讲得慢,发音又奇怪,上一节课要花十倍的时间自学。自从美国“学校”来了,父亲虽然不喜欢皮埃尔,甚至打他骂他,可从来没有阻止过他去学英语。我猜,这个父亲也希望儿子走向更远的世界,只是又无法面对孩子走远以后的失控,和他自己孤独的生活。
预定手术结束的时间快到了,我拍了拍瑞纳的肩膀,让他必须牢牢记住我接下来说的注意事项,因为这是决定这个骗局是否成功的关键。“你不用瞎编我们的手术过程,只需要告诉你父亲,刚刚喝了点药,嗓子麻麻的然后就睡着了,现在除了嗓子疼,并没其它特殊的感觉。”我告诉他,他必须鼓起勇气,克服那些见到父亲时不自觉出现的小动作。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转移注意力,感到害怕的时候就偷偷数数,从1数到100,甚至在心里做数学题。“知道吗,外面的世界真的很精彩,就像你想的那样。也许你可以带着你那暴躁的父亲一起,出去看看。”我打开手术室的门,带着瑞纳走了出去,瑞纳的父亲就在门口站着。他还是板着那张脸,可是也一步没有离开门口。门一打开,他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遍瑞纳,确定完好无损后,立马向我们双手合十微微鞠了一躬,一句话没说就领着瑞纳要离开。我叫住了他,清了清嗓子说,其实这次手术并不是免费的。我说,这个手术用的是我们医疗队的科研经费,只要他配合我们完成术后医嘱,实验成功,我们就不要钱。否则需要3倍赔付手术费用,约1000美元。一,瑞纳必须要去唱歌,因为手术是在声带上做的,不唱歌会出现嘶哑、饮水呛咳的现象。二,必须得给瑞纳找个母亲,瑞纳的病来自于压力导致的内分泌问题,他必须减轻孩子的压力,更不能使孩子处于惊惧恐慌中。瑞纳的父亲签字按下手印就离开了。望着瑞纳父亲远去的背影,袁大夫问我,咱们这个医嘱有效吗?能保护瑞纳吗?我离开非洲时,把这个秘密交给了下一任医疗队,叮嘱他们不要露馅。瑞纳还在,还是那样笑着跳舞,比之前跳得要好很多很多。或许,曾经那双把孩子按在检查椅上的大手,现在已学会如何去拥抱他。
我问谢无界,瑞纳的父亲是个怎样的人?
谢无界说,最开始,他以为这是一个通过不断带孩子看病,让孩子听话的父亲。
但谢无界也注意到那些细节:瑞纳的父亲熟悉仪器,是当地罕见地愿意花钱给孩子做检查的人,为了孩子更安全,他选择了更贵的医院,而不是巫医。
但他也仅仅是一个太贫穷的父亲。
他无法教授孩子英语,无法带孩子走向更远的地方,甚至不知道毒打以外的教育方式。
他在用错误的方式“拥抱”孩子,以至于孩子见到他,就会因为心理原因,出现各种各样的毛病和失误。
遗憾的是这样的父母很多,而这样能给父母“治病”的故事太少,或许这句话应该让更多人知道——
有时一个孩子心理出现了疾病,那么在这个家庭里,他可能是病得最轻的。
插图:酒仙桥桥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