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子在挣扎

肩负理想面对现实,这届新闻系的毕业生们,正在用脚投票,给出属于他们的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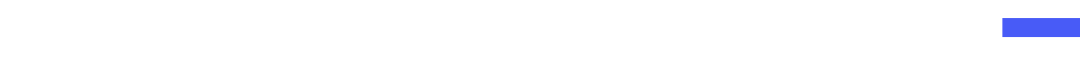
文|徐嘉 编辑|石灿 来源|刺猬公社(ID:ciweigongshe) 封面来源|IC photo
肩负理想面对现实,这届新闻系的毕业生们,正在用脚投票,给出属于他们的答案。
封面来源|IC photo
南方城市一所高校的演播厅里,几百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们身上。
台上是新闻系的学长学姐。他们花费数月完成、聚焦中国香港劏房住户生存与命运的深度报道,正以文字、摄影、视频的形式呈现在大家面前。这是他们用来交付四年新闻专业学习的毕业作品,从作品体量和深度上看,他们度过了颇有收获的四年。
张笛坐在台下,听着他们的讲述,感觉身体里有什么在被撑开,鸡皮疙瘩在皮肤上一阵阵蔓延。她的感官突然变得很敏锐,似乎可以越过屏幕,感觉到劏房里的呼吸。
学长学姐话毕,台下掌声雷动。
新闻系的老师点评犀利精准,台上新闻系的学生务实认真,这一切,都是她在自己的专业广播电视学里没有体会过的——那些偏向影视的课程内容大多重实操轻理论,很难帮助张笛提升自己渴望拥有的逻辑思维和文字表达能力。
三年后,当张笛终于进入新闻系读研,却没能实现当年看到的那种全力以赴投入采写的状态。在疫情的影响下,她焦虑地刷新着互联网大厂的实习岗位信息,卷到毕业,她发现自己走上了另一条路,实际点说,是相对新闻理想,她更务实、更需要赚钱带来的掌控感。
大学校园里,新闻系是闪耀着理想的屋檐,庇护着骄傲的学子,给他们鲁莽的勇气。但当面对就业,新闻系似乎又显得脆弱而天真,成为张雪峰口中“报了就把孩子打晕”的存在。
近来热议的背后,折射出整个社会对大学教育、就业及未来的焦虑。尽管一考不再定终生,专业也不再和就业强相关,但在经济形势不明朗的当下,新闻专业是否还值得选择?什么样的人适合读新闻?新闻教育又能带来什么?
一切开始的地方
凌晨一点,季洁缩在被窝里点开微博,那些来自远方人们的讲述和求助轮番涌现,一些图片刺痛她的眼睛,冲走了她的困意,她无能为力,只有失眠。
在2020年初,她度过了许多这样相似的夜晚。疫情搁置了她的实习——这本是许多大三学生备战就业的最后一次机会;也搁置了她的毕业展演——这本是她最期待的校园告别仪式。她不甘心就这样离开大学,也对未来的就业感到焦虑。
就在无力感徒增的那段时间,她通过参与公共事件的讨论,关注到许多优秀的媒体人和学者。他们对社会系统、政治、科学的思考像一面镜子,为季洁解答疑惑,也映出季洁不堪一击的知识储备和逻辑思维。
于是,21岁的季洁决定:“我要读研,再多读点书。”
父母无法提供更多建议,她寻求职业兴趣测试、星座、八字、人生教练、塔罗牌,其中高频出现的几个词吸引了季洁:媒体工作者、记者、传播......
“寻找真相,去参与、见证、记录、传递。你看,这种新闻的概念,在当时就像我的兴奋剂。”
她想到自己曾在学院旁听新闻系老师的采访写作课,那种严肃求索的精神让她至今想起都精神一振;又想到过去的自己也爱打抱不平、维权索赔、大声制止地铁上的流氓......当即决定:“就读这个!新闻系!”她写了一封长长的陈情令,获得了爸妈的支持。
后来的深夜,她不再陷进爆炸信息里无法自拔,转看非虚构的文章,一遍遍重读十几年前的行业故事,全力以赴备考新闻专业。那是2020年的初春,季洁向内求,为自己构建出了理想的未来。
00后立丹和新闻的结缘更早。
初中入学,她因脚伤无法参加军训,百无聊赖中给校报投稿,屡投屡中,她享受到写作带来的“小小快乐”。而后,广播站站长沿着报纸署名找到班里,她又受邀加入广播站,得以在初中就有了校园媒体实践。
后来,她觉得这像“命定”。
2019年高考后的暑假,她听到网易云音乐上的一档播客,播客名叫“凡间角落”,主播“走来走去的F小姐”常分享人文历史的内容。“听了她的播客,我感觉新闻专业培养出来的人,在思想和行为方式上都值得人欣赏。”
那些无意的巧合或有意启蒙,总让不少孩子早早确立了新闻志向。用张笛的话来说,是“文青、玛丽苏”化。
初中,她被书上“编辑XX”的名头吸引,“做出作品,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太有意思了。”随后,语文老师推荐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和行业的非虚构作品,愈加催生出她做记者的想法。
满腔热血、人文气息、社会担当…...这是许多学生选择新闻专业最初的理由,但父母们往往更关注这之后的就业问题。
即使一考不再定终生,专业也不再和就业强相关,但新闻专业从在中国高校设立起,便是服务于社会的“有用”专业,而非像社会学、文学的“无学”专业。不过它们的命运似乎很相似,每逢高考后、毕业季便被唱衰一次。
父母希望张笛选师范类或小语种——他们认为,这是文科里相对好就业的专业。向志愿填报老师咨询新闻专业时,张笛还记得那人的表情,看起来像在说:“嗯?怎么选这个?”
父母很焦虑。立丹也接受父母的安排,做了基因检测:“他们花了五位数,刮了我的口腔细胞,去测我基因里适合什么工作。”基因报告里有销售、人力资源,没有传媒。
立丹相信自己善表达、交际,适合新闻。她以“都是与人打交道”为由说服了爸妈,以排在广东省文科2000位的高分成绩,选择了4000位就能上的新闻专业。
张笛则和父母做了场交易:“我听他们的要求选了省内的学校,他们就得听我的,让我选自己喜欢的专业。”她填上了传播学院所有与新闻有关的专业。
在新闻专业的门前,有人渴望得到精神救赎,有人渴望执笔改变社会,有人被它犀利尖锐的气质吸引,有人想做狗仔娱记,有人渴望提升沟通与表达能力,有人想实现更好的就业……
他们带着不同的美好愿望来到新闻专业,可大学教育毕竟不万能,也有诸多弊病。期望越高,失望越大。
2019年,立丹进入南方一所大学的新闻系就读,这是她反抗“基因检测报告”后,靠雄辩争取来的结果。但一年之后,她就从新闻采写实践转向研究传播学理论。
立丹是ESTJ型人格,她说这代表自己重理性、善规划。
果不其然,入学后,她先研究了学校的课程培养方案:“每个课都是蜻蜓点水,下学期就学别的去了,什么都只能了解个大概。”于是她希望从课外实践入手,加入了校报、系报,担任学生记者,希望能在实践里收获更多专业技能。
这期间,学校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她跟进调查写出的报道却在发表前被迫做出了改动:“这件事让我觉得平台和渠道很重要,那些开办新传时间更长的学校,专业度相对会更高,受到的限制也会少一些。”
在课堂教育、课外实践中都没有得到满足的立丹,开始考虑升学问题,但又很快发现,新传专业的升学渠道偏窄:“新闻相关的竞赛很少,不可能通过一篇新闻作品就获得升学的机会。如果你一直在做新闻实践,那后面可能把路越走越窄,只有进媒体。它不像你会做网页,后面可以转码、进公司、做数据抓取和学科竞赛,还能帮你争取到升学的机会。”
立丹并不是功利导向的人,从一开始进入新闻专业,她就渴望变成更加理性、像“F小姐”那样优秀的人,但在大学里,她总有“书没读够”的感觉:“再来一次,我可能会选一个更好的学校学新闻。”
抵达事件的本质和真相,将其还原呈现给外界——这是众多新闻记者都渴望抵达的境界,也成了立丹却步的原因——从外界环境和个人能力上,她都觉得沮丧。
“如果我当初喜欢更感性的表达,可能会选汉语言文学。之所以选新闻,就是觉得写新闻报道很像在解数学题:先把题目读懂,整理资料和采访的过程就像在看条件,写作就是在解题,但你往往没办法解到最后一步,就像往湖面扔小石子,扔了100次都沉下去,这种感觉就让我觉得很难受、很困惑。本科期间,我所有的新闻实践好像都没达到这个状态,只要靠近一点点就可以了,但一次都没有。”
立丹反观身边的同学,依然有人在追逐真相,他们体现出的锐利、冲劲和韧劲,让她从外到内地审视自己:“也许,我没有那么渴求真相,做不到那么较真。”
和早早入门,早早“看透”的立丹不同,张笛从当年在演播厅里被震撼之后,就一直对新闻抱有类似“高攀”的想象,当她终于圆梦新闻系,也借此完成了学历提升。
本科时,她曾向南方一家媒体投递实习,却没得到回音。“我安慰自己:你只有一段大厂的实习,也不是新闻科班出身,可以理解。”
2021年,她终于读上新闻专业的硕士,却深受疫情的影响,对未来就业感到恐慌,开始“卷实习”。
这不是简单的内卷,张笛做事一向慎重。她眼见身边不断有朋友进入广电、传统媒体实习,忍受媒体业内多年来的常态——那些“为爱发电”的传媒学子,往往会遇上“无酬劳动、倒贴进组、为项目垫钱、被画饼PUA、打杂应酬一无所获”等五花八门的情况。既然如此辛苦,何必继续徒劳?
另一边,张笛的学校有着浓厚的互联网实习氛围,那些公司大多福利待遇优厚,价值观和职场氛围更为开放。
权衡之下,她决定放弃去传统媒体实习的想法,扎进互联网和新媒体的沃土,一连积累了四段实习经历,成为同学中的“卷王”。
毕业前,她又想起之前的“遗憾”:“我又投了那家媒体,我想,自己是研究生,又有这么多实习,应该可以胜任吧......但我一份简历都没有通过。”那次之后,她难过地找到在南方系媒体的朋友,聊了很久。
她意识到,能够进入这些优秀老牌媒体实习、工作的同学,大多已经在学校里有过丰富的媒体实践经验和作品。在她眼里,那些同学有热情、有韧劲、能忍受漫长而低回报的工作现状。
一边是高投入、低薪的媒体,另一边是氛围活跃、高薪的互联网大厂,头上顶着疫情的阴霾,身旁是卷出新高度的同辈压力,张笛尽管圆梦新闻系,却在实习中一步步离新闻业越来越远。
张笛的选择并不少见——在不合理的系统下,能吃苦不是美德。
但还是有许多以媒体为职业方向的新闻系学生,能通过系里的人脉关系争取到实习机会,通过系统的帮助完成那些入行所需的实践。
连珊便是其中一个。
新闻系硕士在读期间,她经介绍进入一家老牌报业实习,那是不少非新闻专业或没有渠道的学生遥不可及的地方。
“好无聊,每天都是那种很单一的活动,一篇通稿抄来抄去,蛮恶心的。毕业后,我第一个排除的就是当记者,真的很讨厌现在的媒体环境,讨厌记者干的一切事情。”
当初,因为对娱乐圈感兴趣,她决定读新闻,今后做娱记。在她看来,这个专业有趣、简单,相对本科的戏剧影视也更好就业。
可真正入门,她才意识到自己似乎跳进了另一个“坑”:“书上学到的是很正统的知识,但又学得很杂。如果选理科,学一门技术还比较好就业,但文科学到的都是很大很泛很空的东西——现在所有的文科都是这样吧?我不知道。”
说起最近的社会热谈,她直言:“我觉得张雪峰说的很有道理,新闻学的教授好多都是高高在上不食肉糜,自己可能已经功成名就,觉得新闻系很有前途,但其实看一看新闻系惨淡的招生和就业率就知道了,说什么能文能武,其实就是替代性很强”。
连珊以就业为导向、更看重学历提升。但很明显,她所在学校的新闻专业没有能助她一臂之力。临近毕业,连珊投了50多家公司,近100份简历,参加了2次线下招聘会,一无所获。
立丹对新闻系的学科教育实践感到失望,张笛却步于媒体氛围和待遇,连珊没有通过新闻系实现在职场上的竞争优势。
新闻班30多人,毕业后,只有季洁选择进入媒体行业。
过去的两年里,每逢聚会,大家总免不了讨论今后的打算。考公、考编、教师、互联网公司,一圈轮流发言下来,选择总是这几个。两年来如此,十多年来也如此。当初说要做记者的几个同学,临近毕业也悄无声息选了别的。
在这期间,季洁创建自己的自媒体,以每周一期的频率产出文字、音频和视频内容,终于争取到一个进入非虚构写作媒体实习的机会。在那里,她卯足劲争取独立写稿的机会,最终积累出自己较成规模的作品集。
“有次我去采访,本来说半小时就结束,我们聊了三个多小时。最后他说,我对他在做的事情非常了解,看得出是认真做了功课,他很佩服我的认真和沟通能力。他通过聊天整理了自己,觉得能被采访很开心。”那次,受访者坚持要和她合影:“他确信我会成为很棒的记者,还说以后要给孩子看这张照片,给他讲我的故事。”
在交流时四目相对,感受思绪流通,从采访对象那里得到对自己的正反馈,也许还能通过写作改变些什么——这对季洁来说,是会上瘾的人生体验。
通过丰富的实践经历,她笃信自己的特质和兴趣爱好,都与记者这份工作完美匹配。在新闻系,像这样留到最后的记者苗子,总会得到其他同学的鼓励和寄托。就这样,在种种原因的推动下,季洁锁定采写记者的岗位,将新媒体运营、传统媒体、大厂统统抛在脑后。
错失媒体实习的张笛,曾对像季洁这样的同学做出了总结。
“做记者工作需要几个东西:第一个是很大的热情、毅力;第二个是洞察力,能够冷静分辨事物;第三个是创作天赋;最后还要有经济基础。这份工作要求你在前期有很多金钱和精力的投入,要你去牺牲,很苦,没办法很快给到自己或者家庭一些回馈。”
季洁总是侃侃而谈,但在谈到薪资时,立刻变成了哑炮。
近两年,季洁的父母接连到了退休年龄,他们仍继续工作,为季洁支付学费、生活费、实习租房等一切开销。看着同等学历、实习经验不相上下的朋友们一个个确定了工作,薪资待遇诱人,季洁有时候心里也直打鼓。
她在拥挤的早高峰地铁上刷到张雪峰,看了看标题,没敢点开。
“我有点怕,如果他说的是真的,我会受不了。过去几年我都在坚持,要做记者、要写作、经历一切新鲜有趣的事情。但如果我选错了......这算不算啃老,自私?要父母为我买单?同学们去挣钱独立了,我一直任性,像在做白日梦,是不是很蠢?”
她想起上次过年回家,亲戚们问她的志向,她激情洋溢地描述了记者的职业规划,迎来支支吾吾的反馈:“你看XX,之前在北京做了那么多年记者,最后还是得回来卖酒。要不......你再考虑考虑?”家里的亲戚们热切地向她介绍“安逸岗位”,希望她能够回家乡共享人际纽带中蕴含着的既得利益。有些时候,她会心跳加速,说不清是心动,还是恐惧。
在记者这行里,就算大家的目标一致,自身面对的情况也各不相同,这是一条注定孤独的路。更多时候,她会在播客、讲座和书里寻找媒体行业前辈留下的“火种”。
后来,她点开那些关于张雪峰的新闻,认真算了算父母的年龄,站在离家2000公里的城市里,给父母打电话,要他们注意身体,说最近很有收获,未来应该会很有前途。然后,她不敢继续想下去了。
“一些很有理想的人,不会因为工资很少或者没有工资就不去实习、工作。我向往新闻理想,也很佩服有新闻理想的人,但我本人更注重实际,比较在意自己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不想让家里为我所谓的理想买单,支持我去更远的地方比如北京上海,在那租房几个月实习。我不想吃那种苦,更想享受挣钱的快乐。”
尽管张笛想好了要先经济独立,在做出最后的职业选择前,她也曾在一份内容创作的工作前犹豫过。最后,她还是决定,先去一线城市的大厂做公关,等有了更高的能力、收入,再转回做媒体也说不定。
艺源从新闻系毕业,刚刚签下一份国企的文秘工作。谈起从前,她还记得自己对新闻传播的热爱是从何而生。她爱和家人一起看《人物静距离》;纪录片节目里,人文视角下的世界让她动容;电视上,她看到驻边战士和家人团聚的那刻,暗想:“能做一个记录者,也挺好。”
此后,她进入大学,拍过很多条视频,从不觉得辛苦,熬夜也乐在其中:“我很坚定喜欢自己的专业,那时候每天都有动力,从不拖延。”到了2023年初的春招,她的热爱却没有换来等价的薪资回报。
她找到一份位于上海市中心,以人物专访、记录社会为主要内容的视频编导工作,对方要求她2次跨1500公里去参加线下面试,经过重重筛选,却也只能给到6千出头的薪资。
艺源开始失眠:硕士出身,一直以来为爱发电,拿到的工资却似乎只能在上海勉强糊口。“如果我在上海有房子,也许我就会选择这份工作了。”她说自己不够“勇敢”,只能暂缓对工作内容的期望,选择更稳定的工作以求自保。
2023年6月29日晚,刺猬公社主理人叶铁桥在知乎平台发起了一场名为《聊聊新闻专业:新闻专业还值得学吗?》的圆桌对谈,复旦大学陆晔教授、原《中国青年报》深度调查部主任刘万永、正面连接的作者吴呈杰都加入了这场直播展开讨论。
毕业临近,连珊在求职市场上屡屡受挫,最后,教师招聘广告一篇篇发布,她称这是“大势所趋,走投无路”的选择。
新闻系让她失望,可还是留了印记在她身上。参加教师面试时,连珊过关斩将,名次领先。她分享了在面试现场的趣闻:“你可以很明显感觉到哪些学生是学新闻传播的,哪些不是。前者头脑比较灵活,有思辨能力,口头功夫了得——可能从学新闻开始,就已经准备好了要走出去和人打交道吧。”
她从没想过从事教育,却顺利成为了老师;她一直讨厌自己来到的这所城市,却成了宿舍唯一留在南方的人。
命运在毕业的转折点冒出了许多未知的分叉,稍不留神,就会走到完全陌生的地方去。
季洁则在担忧和摇摆中,决定给自己三年时间来深耕媒体行业,借此来考验自己的毅力和能力。头脑枯竭面对着电脑屏幕时,她常翻出一首诗:“林中分两路,可惜难兼行......我独选此路,境遇乃相异。”读过之后,继续上路。
这首《未选择的路》的作者罗伯特·弗罗斯特,是20世纪最受欢迎的美国诗人之一,也曾四次获得普利策奖。早年,弗罗斯特的诗歌一直没有得到美国诗界的认可,为了创作,他在38岁放弃了安逸的教书职业和农场,去到英国伦敦开始潜心创作。在那里,他的诗作相继问世,大受欢迎。
向着“F小姐”一路前行的立丹,今年毕业,已被保送至一所985院校就读传播学专业。接下来,她希望潜心传播学学术研究,将新闻采访中的沟通、观察能力,运用在质化研究中,总结出一些规律和结论。
她并不后悔学习新闻专业。
“也许当时我的分数可以读金融、科技这样更加热门的专业,但我对它的热情会在大一就被消磨殆尽,后面一直被DDL或绩点推着走。现在我一点都不后悔,因为我找不到另一个可以让我读四年都没有任何厌烦的学科,新闻专业也许不是最完美的,但它是我心中相对最优的选项。”
她没有被自己的专业束缚,而是利用自己新闻传播专业的优势,在全方位拓展自己的能力:“在新闻专业里,我学到最实用的技能就是和一个陌生环境、一个陌生人群去打交道的能力。”从传媒出发,就像是1+X,后者可能是另外行业里的其他能力,这需要每个人自己去探索和培养。
“也许以后,我还是会进入媒体行业,但现在,我希望先把路走宽,先宽再收紧,这样我会在中间阶段有更多的选择。”这个暑假,她同时打了4份工:“我先做了初中生的家教工作,验证了我不喜欢做老师;其次我利用保研的经历,联系到一些成功保研的学长学姐,成立了一家教育咨询工作室,希望能够帮助其他的学弟学妹,顺便给自己攒些积蓄;我还加入了一个Web3互联网金融的创业团队,希望能够进一步了解到前沿的互联网氛围;同时我也在运营自己的自媒体账号,已经有一些合作找上门了。”
对于立丹来说,选择尚多,时间尚宽容。
而艺源在一片哀声的就业环境中,最后选了能给自己安定感和体面薪水的国企宣传岗,她能睡个好觉了。
“也许之后我做的工作和专业不太相关了,但我很珍惜那些过去的回忆,它让我认识了很多有相同喜好的人,今后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支撑。”
那些天,杭州一直下雨。艺源在离公司10分钟的地方找到心仪的房子,请一位师傅上门换锁。闲聊中,师傅聊到今年高考的女儿,又问起她的工作和专业。
“我是读传媒专业的,学的新闻。”
“这个专业工资不太高吧?”
“是的,不要报传媒专业。”艺源开玩笑。
“是的,我听了那个张老师,他说这个新闻传播专业很踩雷,不好找工作,我不会让我女儿报的。”
师傅头也不抬,毫不留情地在艺源心里补刀,她有点难过。
窗外正下着暴雨,她思来想去,小声补了句:“其实,还是很好找工作的,只是,很难找到高薪的工作......”
(文中受访者为化名)
来个“分享、点赞、在看”👇
新闻学子在挣扎
微信扫码关注该文公众号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