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敏有着一个一听就知道是广东人的名字,已经忘记她是我认识的第几个“家敏/嘉敏”。那天我们约在一个贵州菜餐馆见面,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唉,我错过了今年香港小姐的报名时间。”我原以为她在开玩笑,但她似乎很认真地想去竞选港姐,说就当作是次人生体验不好吗。 家敏很“广”(很广东的意思,我也是最近第一次听到这个形容词):眼睛大大的——长得很广;粤语说得字正腔圆——口音很广;表情多多,有时古灵精怪,有时一身正气——性格很广。她总是会让我想起,小时候广东卫视播放的粤剧里的女性文武生。若让她反串《梁祝》里的梁山伯,或者《唐伯虎点秋香》里的唐伯虎,一定有板有眼,像模像样。 事实上,家敏是个跳舞的女孩。第一次看见她,是她在自媒体上,用“100 个让自己简单动起来的方法”,教别人在蹦迪时,如何通过想象自己是抱着 baby 的惠慈,自然地让身体找到感觉,跟着律动跳起来。视频里的这个可爱女孩,总是不自觉地挑眉,把这些最简单、最日常的细节变成一个跳舞的引子。她知道人们在生活里害怕跳舞的理由,她想告诉所有人:你能够随时随地舞起来。 话说最近咱们这个“别的运动”专栏,已经介绍过两次舞蹈,每次发稿我都担心,要是把舞蹈说成是运动,会不会被一些很认真的人说在偷换概念。好在,家敏说她其实也不知道她现在跳的到底还算不是舞蹈。她在做一个新的东西,用一种新的方法,让更多人自发地、有机地“舞动”起来。都有个“动”字,那姑且算是种运动吧。  家敏与舞蹈
家敏与舞蹈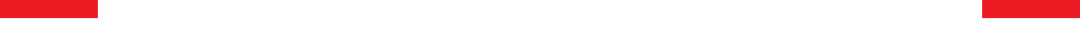 跟很多体质相同的中国宝宝一样,家敏 4 岁的时候,通过兴趣班第一次接触芭蕾舞,11 岁开始职业芭蕾舞训练,曾就读于香港演艺学院,跟无数香港明星做校友。后来又去了荷兰的 ArtEZ 艺术学院学现代舞。从舞蹈到武术,她会的东西一对手都数不过来。而她现在专注于让人从最细微的动作开始动起来,也不难理解她为什么会有“我不知道自己现在跳的还算不算舞蹈”这种身份认同的困惑。 家敏在欧洲创作并表演的作品《Funny Soft Happy & the Opposite》 “以前在广东现代舞团培训中心教课,一些资深舞蹈爱好者过来问我:‘老师,你教的这个是现代舞吗?’我一时之间不知该怎么反应,是我没把理论知识说清楚吗?那我就再给他们解释一遍。” 家敏每到一个新的城市生活,都喜欢让自己充分浸淫在不同的环境里,有时一天去三个不同舞种的场子。“三种环境,圈子的社交氛围都不一样,比如说街舞圈,不管你跳得好不好,大家都会一顿给你猛鼓掌;而芭蕾舞圈,可能每个人都已经跳得很好了,但大家都往里收着,面无表情;有段时间我的同事基本都是 LGBTQ 群体,那又是另外一种氛围。身边的场景不断变化,每个舞种里,怎么穿,怎么讲话,怎么相互支持,又怎么相互贬低,各有千秋。”家敏说。 家敏在欧洲创作并表演的作品《Funny Soft Happy & the Opposite》 “在这么小的舞蹈世界里面,这么小众的文化,就有这么多的变化,所以根本不用去纠结舞种本身,或者我到底要符合哪一种标准,因为根本没有所谓的标准,其实都不重要。” 因为自己在舞种和圈子中被身份认同困扰,家敏在生活中看见其他人也有相似的困境:“后来被学生提问,包括看网络上的评论,我发现在国内环境里成长的大家,虽然从事的行业不同,但内心的声音是一样的,总是觉得‘我腿不够长’、‘我太过用力’、‘我是不是太懒了’、‘我是不是太努力了’,觉得自己这里不好那里不好。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说,我已经很努力了,今天来庆祝一下。我为‘庆祝’而跳舞,而不是为了当伟大的人民艺术家去跳舞。哪有这么多伟大,我不想要伟大。” 以舞蹈作为入口,在互动中让大家把心里对自己的固有期待拿掉,对于家敏来说是一件很治愈的事。 有空的时候,家敏会去公园里看阿姨大叔跳广场舞,有时会跟他们一起跳。阿姨们每天都是一番精心梳妆打扮,把自己弄得整整齐齐,她们知道自己不是跳得最好的,但在公园里她们有了这样一个身份,能够跟不同的人在同一时空,不用讲话,不需要考虑工作,只是听着音乐跳舞。很多退休了的老年人,他们一天的高光就在那里,在公园的角落,一个人也能跳到六亲不认。 家敏说:“广场舞就是一种庆祝。我觉得‘庆祝’是特别诗意的事情,舞蹈在原始社会就是从庆典仪式来的,就像农民播种劳作后,要庆祝丰收。在播种与庆祝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我觉得很诗意。梁文道做过一期电台节目,说‘奢侈’就是人类不甘于只是活着,不甘于只是当动物的、多出来的那一点东西。他说的‘奢侈’和我的这种‘诗意’有点像,生命的意义不只是吃了上顿找下顿,吃了下顿再找下一顿,中间还有一些不是为吃饭而做的事情。”
跟很多体质相同的中国宝宝一样,家敏 4 岁的时候,通过兴趣班第一次接触芭蕾舞,11 岁开始职业芭蕾舞训练,曾就读于香港演艺学院,跟无数香港明星做校友。后来又去了荷兰的 ArtEZ 艺术学院学现代舞。从舞蹈到武术,她会的东西一对手都数不过来。而她现在专注于让人从最细微的动作开始动起来,也不难理解她为什么会有“我不知道自己现在跳的还算不算舞蹈”这种身份认同的困惑。 家敏在欧洲创作并表演的作品《Funny Soft Happy & the Opposite》 “以前在广东现代舞团培训中心教课,一些资深舞蹈爱好者过来问我:‘老师,你教的这个是现代舞吗?’我一时之间不知该怎么反应,是我没把理论知识说清楚吗?那我就再给他们解释一遍。” 家敏每到一个新的城市生活,都喜欢让自己充分浸淫在不同的环境里,有时一天去三个不同舞种的场子。“三种环境,圈子的社交氛围都不一样,比如说街舞圈,不管你跳得好不好,大家都会一顿给你猛鼓掌;而芭蕾舞圈,可能每个人都已经跳得很好了,但大家都往里收着,面无表情;有段时间我的同事基本都是 LGBTQ 群体,那又是另外一种氛围。身边的场景不断变化,每个舞种里,怎么穿,怎么讲话,怎么相互支持,又怎么相互贬低,各有千秋。”家敏说。 家敏在欧洲创作并表演的作品《Funny Soft Happy & the Opposite》 “在这么小的舞蹈世界里面,这么小众的文化,就有这么多的变化,所以根本不用去纠结舞种本身,或者我到底要符合哪一种标准,因为根本没有所谓的标准,其实都不重要。” 因为自己在舞种和圈子中被身份认同困扰,家敏在生活中看见其他人也有相似的困境:“后来被学生提问,包括看网络上的评论,我发现在国内环境里成长的大家,虽然从事的行业不同,但内心的声音是一样的,总是觉得‘我腿不够长’、‘我太过用力’、‘我是不是太懒了’、‘我是不是太努力了’,觉得自己这里不好那里不好。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说,我已经很努力了,今天来庆祝一下。我为‘庆祝’而跳舞,而不是为了当伟大的人民艺术家去跳舞。哪有这么多伟大,我不想要伟大。” 以舞蹈作为入口,在互动中让大家把心里对自己的固有期待拿掉,对于家敏来说是一件很治愈的事。 有空的时候,家敏会去公园里看阿姨大叔跳广场舞,有时会跟他们一起跳。阿姨们每天都是一番精心梳妆打扮,把自己弄得整整齐齐,她们知道自己不是跳得最好的,但在公园里她们有了这样一个身份,能够跟不同的人在同一时空,不用讲话,不需要考虑工作,只是听着音乐跳舞。很多退休了的老年人,他们一天的高光就在那里,在公园的角落,一个人也能跳到六亲不认。 家敏说:“广场舞就是一种庆祝。我觉得‘庆祝’是特别诗意的事情,舞蹈在原始社会就是从庆典仪式来的,就像农民播种劳作后,要庆祝丰收。在播种与庆祝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我觉得很诗意。梁文道做过一期电台节目,说‘奢侈’就是人类不甘于只是活着,不甘于只是当动物的、多出来的那一点东西。他说的‘奢侈’和我的这种‘诗意’有点像,生命的意义不只是吃了上顿找下顿,吃了下顿再找下一顿,中间还有一些不是为吃饭而做的事情。”
 家敏与自己
家敏与自己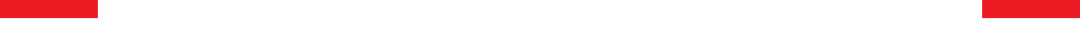 我们在餐馆里点了份丝娃娃,这是家敏第一次吃这种贵州菜,她笑说这就是“Chinese Taco”。她包丝娃娃的手法其实不对,但我想了一下,这个吃丝娃娃的标准这时也没什么所谓。 家敏边包着丝娃娃,边说:“我开始觉得身份认同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可以帮到别人。如果我今天可以帮大家去享受音乐和舞蹈,享受身体,享受生活,就已经很棒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有这种助人情节,可能我觉得在帮人的同时,更多地也在帮自己吧。”
我们在餐馆里点了份丝娃娃,这是家敏第一次吃这种贵州菜,她笑说这就是“Chinese Taco”。她包丝娃娃的手法其实不对,但我想了一下,这个吃丝娃娃的标准这时也没什么所谓。 家敏边包着丝娃娃,边说:“我开始觉得身份认同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可以帮到别人。如果我今天可以帮大家去享受音乐和舞蹈,享受身体,享受生活,就已经很棒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有这种助人情节,可能我觉得在帮人的同时,更多地也在帮自己吧。” 
家敏没有像很多创作者一样,花大量时间在艺术的道路上自洽和内耗,也没有像其他舞蹈博主一样,把自己擅长的舞种通过精心设计的编舞短视频展示出来,而是让自己走到人群和生活里,以一个带领人的身份,在另一个起点从零开始,让一部分人先动起来。我对她这个选择有点好奇,也没有在过去她发的任何一条视频里找到线索。我知道,当一个人决定“帮别人”,其中一定有原因和故事。
我终于忍不住问出了那个问题:“家敏,你的故事到底是什么?”接着我把一个包好的丝娃娃塞到嘴里。 “我是一个敏感的人,小时候有很多情绪上的问题,当时没有人可以帮我,最终通过漫长的摸索自己走了出来。每当想起当时那个无助的自己,然后看到身边有些人还被困在‘我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想法里,就想给予ta那一点点帮助,让ta从沉重的压力里解脱出来。” 15 岁那年,在舞蹈学校里的家敏,算是那种“有天赋但身材不好”的舞蹈学生。“我的老师会以胖为原因,不让我上台跳舞。我把很多时间花在减肥这件事情上,每天祈求老师能多看我一眼,给我上台的机会。终于有一次老师把我叫上台,但却是‘公开处刑’:她让我在全班同学,还有我当时喜欢的男生面前转圈,指着我的身体,说‘你看你这身材,哪里像个少女,看你这屁股就像一个生过小孩的家庭主妇’。当时我觉得如果我不瘦下来,我的事业和生活都会垮掉,不会有人爱我。” 生活中被控制,高强度的训练,再加上过高的自我期望,所导致的精神压力使家敏患上严重抑郁症。严重到无法入眠,一想到要跳舞,身体就会不自觉地因为恐慌而抽搐,从心理到生理都在逃避跳舞。后来她花了几个月,瘦了快 20 斤,别人睡觉她跑步,别人休息她拉筋。就当她觉得老师快要对自己改观,人生将要沸腾时,那根弦断了,她崩溃了,开始暴食。“巨大的孤独感把我吞噬了,无论我多努力,都没有人来帮我,愿意推我一把,我没有办法,身材也在短时间内经历暴瘦和暴肥。” 后来,家敏开始意识到,得把自己从这个深不见底的循环里拉出来,打算放弃跳舞,但除了跳舞自己还可以做什么,她却没有一丝头绪。她希望能找到“那个真正的梦想”。 包丝娃娃的手停了下来,我完全没准备好听到一个关于女德班的真人故事,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离传说中的女德班这么近。 “进女德班对当时的我来说,并非是件多不好的事。那个场域给了我一个出口,一上课,我就像鬼上身一样,无法自控地暴哭。没有人敢管我,当时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厨房里帮工。” 女德班里那帮所谓的传统文化导师,跟家敏说:“你所有的烦恼都是因为不知天命!不知道你的使命是什么!那就让我来告诉你,作为一个女人,你就得从父从夫从子,做好你当女人的本分!舞蹈是个什么鬼东西,跳舞能干什么,有什么用吗?跳得好,你对这个社会有什么帮助,还不如当个好妈妈。或者投身到我们这个传统文化的教育行业里,当一名老师,让更多人知天命。” 家敏接着讲:“然后就是那个moment!我就醒了,心想我自己说不跳舞可以,但被你这样说跳舞没用,我就很不爽了。”说起那种不爽来,她有些激动。 从女德班出来之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家敏小时候的舞蹈启蒙老师邀请她去福利院,给小孩做一场公益演出。当时她还因为长时间训练中断和身材发胖而犹豫和紧张,然而启蒙老师这么跟她说:“没关系的,你的身体会知道很多。”那次公益演出,台下都是 3-7 岁的孩子,从小被父母遗弃。家敏穿着简朴的演出服,编舞也不是高难度的,但那群小孩用眼神告诉她,她的舞姿是优美的、高雅的,像是编织出了一场梦。 “演出最后,我们跟小孩手拉手,让他们也加入到舞蹈中。我身边的小男孩一直不肯把手给我,当时我就 emo 了,觉得难道连小孩也不喜欢我?我边鼓励他试试看,边把他的手放到我的手上,才发现他的手有个凸起来的、像第六个手指般的一块肉。我突然明白他为什么不想跟我牵手,因为他觉得自己不好看,或者有人说过他不好看。” “我小心翼翼地握着他的手,感受到那只手慢慢地越握越紧,对我越来越信任。当时我就像被重拳打中了一样:为什么一直以来我满脑子只有自己。那天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小男孩,但那一刻我决定我要继续跳舞,哪怕没有人看,我也要跳舞!” 
家敏家里关于“手”的元素
人们总是出于惯性地,把过去的创伤投射在一些能引起自己共情的人和事上,或许,当时的家敏希望跟那个小男孩说,他手上的那个东西不是个大问题。然后小男孩也能跟她说,她一点都不胖。生命总是在某些瞬间,被彼此需要。那种微弱的被需要感,会变成强大的生命力。 家敏的动作小屋
家敏的动作小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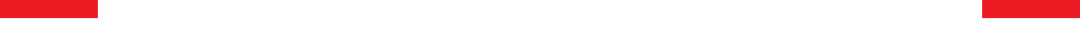
家敏在国外时“还混得不错”,之所以选择回国发展,是因为“害怕”,怕那个严苛的、激进的、压迫式的、特别直男审美的舞蹈世界,怕在国外好不容易获得的自由自在跳舞的感觉会再次失去。但她转念一想,如果有一件事,能让自己如此害怕,说明要去解决它才对。 最近,家敏在上海有了自己的工作室,她把这个空间,起名为“动作小屋”。里面没有安装镜子,是为了鼓励大家多感受身体的体验,少依赖镜子做为外界参考。来的人站着可以跳舞,坐着、躺着、趴着也可以跳舞。无论胳膊有多长,练习舞蹈的时间有多长,舞蹈的体验在这里是可以属于每个人的。 
在动作小屋里的家敏
“有时,不会跳舞的不是身体,而是头脑。现代舞里,经常会用到我们的日常动作,比如刷牙或者洗碗时,有很多打圈的动作,这些重复的动作你说你的身体不会吗?只是你不知道怎么把它放到音乐和舞蹈里面。为什么这里叫‘动作小屋’,而不是‘舞蹈小屋’,是因为我希望大家回到从动作开始的状态,到这种运动体验里面来。我们每天都在走路,只有当我们对走路这个行为有了察觉,后面才会有舞蹈。这个就是我做动作小屋的初心。” “回到一开始说的‘庆祝’,现代人越来越少庆祝别人的成就,那我就在想,我们之间还有什么是相通的。后来我想到,每个人起来是不是都要刷牙?吃完饭后是不是都要洗碗?身边的植物,和头顶的天空是不是都一样的?是不是都有妈妈?是不是有同一道爱吃的菜?这些都是能把所有人联系起来的经历和体感。从生活里边找这种细小的东西去回味,然后去庆祝,去跳舞。” 
生活中的家敏
对于家敏来说,直到此刻,还是很难去说清这种使命感是怎么一回事。 “在国内,女孩子出门穿不穿内衣、刮不刮腋毛、头发的长短,都会被别人讨论。我的视频号下面,老有人猜我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很多从来没有跳过舞,或者害怕跳舞的人,来这里上课,甚至不用在课后告诉我,我就能从她的状态里,看到完全投入舞蹈的快乐。我就会很感动,她把跳舞的障碍消除了。再讲远一点,如果大家能把身体的羞耻去掉,打破禁止自己快乐的限制,人生其他方面或许也能改变很多。”家敏说着,那双大大的眼睛似乎能发出光。 丝娃娃这个时候也快吃完了。我在想,被禁止快乐,真的是个很东方社会的产物。 
生活中的家敏
前段时间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我看了纪录片《起舞的皮娜》。著名现代舞编舞家 Pina Bausch “做自己”的舞蹈精神至今影响着每一个人,她认为舞者的肢体语言必须抛弃规范化的技术身体,将肢体语言回归日常。在影片中,当舞者们知道演出因为疫情被取消,老师对他们说了一段话—— “当你流汗的时候,
汗水渗入土壤,
它不会消失,
我们现在做的一切都不会消失。
有时困难的事情会发生,
但可能会有更好的结果,
我向你们保证,这将继续下去,
每一个身体都能起舞,哪怕是一个有过去的、沉重的身体。家敏说她的身体里有一座游乐场,这座游乐场我有,你也一定有。 在 7 月 22 和 23 日,家敏将会在于阿那亚·金山岭举行的“别的聚会”,用她的有机舞蹈,带大家找到那座内心的“游乐场”。 “别的运动”还会在现场带来接触即兴、巴西战舞等多重身体体验,如果没听过,那就点击往期文章读读看。 //作者:肥牛
//编辑:肥牛
//排版:板砖兮
//摄影:热心市民-大猫,刘景瑜,Greg,郑灵敏,黛比,aili
版权所有,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家敏的动作小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