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朝永振一郎(Sin-Itiro Tomonaga,1906-1979),量子电动力学的奠基人之一。196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图源:维基百科
朝永振一郎是继汤川秀树之后,第二位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日本科学家。1976年,他在日本发表的演讲中,反思了科学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尤其是20世纪二战期间与冷战时期军备竞赛中,恐惧对于政治家和科学家的深刻影响。他指出,恐惧感能造出武器,却无法增进福祉。他还提出了两个问题:科学的进步会持续到什么时候;没有战争的时代什么时候才能到来。他认为,只要第二个问题没有解决,第一个问题就变得无足轻重。朝永振一郎 | 演讲
周自恒 | 翻译
到19世纪,或者说到20世纪初期,人们也能够在实验室中,甚至是实验室外产生出日常生活中所不存在的现象,并通过这些现象制造出了各种东西,但那时候的物理学普遍规律所支配的世界,与我们日常世界之间的距离还没有那么远,它们之间的区别也没有现在这么显著。因此,对于科学蕴藏着如此异常的可能性,普通人,甚至是科学家都未曾想到过,所以大家都觉得科学是一种为日常生活带来各种便利的好东西。
的确,科学所衍生出的各种机器和产品可以产生出一般情况下所无法产生的现象,这些现象并不是特别偏离日常生活,因此大家还可以放心地使用它们,特别是欧洲充斥着各种科学技术的产物,也因此获得了空前的繁荣,大家也都对科学赞美有加。歌德对于科学所展现出的异常世界感到十分不快,并认为开发自然是一种恶魔般的行为,但即便如此,歌德依然无法忽视科学的恩惠,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表达了对科学的赞美。在歌德的《浮士德》中,浮士德与梅菲斯托费勒斯定下了契约,做了很多恶魔般的事情,也从事了开发自然的行为,但最后他并没有下地狱,而是得到了上天的救赎。进入 20 世纪之后,由于原子弹的出现,19 世纪时那种乐观的态度随之烟消云散,之前我们也说过,在原子弹实验成功时,奥本海默曾感慨物理学家尝到了罪孽的滋味。此外,大家可能也听说过在苏联研制氢弹的萨哈罗夫,他也曾向苏联政府建议停止核试验,并因此陷入了悲惨的命运。尽管如此,从现在的科学及其衍生物来看,科学家和工程师依然在不断开发着核武器或者与之相关的恐怖的东西,而且这些人是竭尽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在制造着这些恐怖的,或者令人厌恶的东西。这是事实。我很想知道他们做这些事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在这一点上,他们与 19 世纪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所作所为是截然不同的。19 世纪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也会利用科学来制造新的机器或者新的产品,但他们的目的是为人类谋福祉。相对地,现在的那些非常卓越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以及那些卓越的美国和苏联的政治家们,却在不断制造着核武器,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有必要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深入地思考一下,这些科学家和工程师到底是怀着怎样一种心态去做这些令人厌恶的事情的。对于这个问题有很多看法,比如说科学家和工程师通过这种研究和开发可以获得巨额的报酬,或者通过制造这些新东西可以让自己出名,这些因素我觉得是存在的,但我还有另外一种看法。在 20 世纪下半叶的现在,科学已经算是非常先进了,正是科学的巨大进步才造成了这样的现象。我们说这是一种与日常生活所不同的异常现象,这个异常越大,威胁越大,或者说越恐怖,科学家和工程师反而更愿意去制造这样的东西,这是一种非常矛盾的悖论,而我认为这样的状况就存在于我们现在的社会结构中。如果科学能够制造出恐怖的东西,那么我们应该不去制造这样的东西,拒绝这样的东西。如果说拒绝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那为什么越是恐怖的东西越是要去造呢?到底是怎样的状况才会造成这种荒唐的结果呢?这样的悖论又是如何出现的呢?为什么科学家、工程师和政治家会做出如此矛盾的行为呢?如果我们简单了解一下原子弹问世的过程,也许就能够明白其中的缘由了。最早制造出原子弹的是美国科学家,大家可能也知道,当时是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美国、德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物理学家都知道,利用铀核裂变制造具有巨大威力的原子弹,至少在原理上是可行的。铀核裂变现象是在二战爆发之前的 1939 年,由德国科学家哈恩和斯特拉斯曼发现的,不过这两个人不是物理学家,而是化学家。他们发现在铀核裂变的过程中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因此,无论是美国的科学家,还是德国,甚至是日本的科学家,都知道利用这一于是,美国科学家们觉得,既然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是可行的,那么作为敌人的纳粹德国科学家当然有可能制造出这样的武器,这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是一种噩梦般的恐惧感。如果人们都不知道这种可能性还好,但不幸的是,现在人们知道了,而且不光是自己知道,作为敌人的德国物理学家也知道。如果德国科学家先造出来了怎么办?我们会被德国干掉吗?美国科学家们觉得这太可怕了,于是他们说服了罗斯福总统,启动了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后来大家才知道,当时德国科学家虽然知道制造原子弹的方法,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实验,但最终并没有真的要造原子弹。但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战争已经结束了,德国已经投降了,在此之前,美国科学家一直被这种强烈的恐惧感所笼罩,这一点我们应该可以感同身受。原子弹是因为自身的恐惧感而制造出更恐怖的东西的第一个例子,但后来这样的事情却接连发生。首先,在二战期间,苏联科学家也知道原子弹的可能性,但没想到美国真的会把这东西造出来。美国已经制造出并且拥有了原子弹,这次轮到苏联科学家笼罩在美国核威慑的恐惧之下了。于是,苏联科学家也开始不惜一切代价制造原子弹。后来,人们又发现了制造出相当于原子弹上千倍威力的氢弹的方法,美国和苏联都觉得,如果自己不去制造的话,就会被对方抢先,这样是万万不行的,于是双方都造出了氢弹。这样的状况,到现在依然在继续。当知道一方要造某种东西,或者说知道了一方能够造出某种东西,那么另一方就被迫也要造出这种东西,因为如果被对方抢先的话,局面就会变得糟糕,现在这种状况依然没有改变。从这段历史来看,如果科学和技术不再发展的话那么还好,但只要有发展的空间,只要新发现和新理论产生出制造新东西的可能性,那么人类内心深处近乎本能的那种恐惧感,也就是害怕被对方抢先的恐惧感,就会驱使人类不断制造出威力更大的武器,或者不断提高武器的性能。即使自己知道这种想法是不对的,也无法抗拒这样的冲动。如果科学家被恐惧感所驱使,现在问题还仅仅局限在美苏两国之间,只要其中任何一国的科学家闪现出一个科学发现,或者是一个技术发明,或者哪怕仅仅是一个新的想法,这种 “闪现” 本身就足以让另一方产生恐惧感。科学规律是具有普遍性的,因此基于这种普遍规律所发展出的技术,和科学一样也是具有普遍性的。没有什么规律是对一个国家成立而对另一个国家不成立的,因此自己发现了一个东西,不能保证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发现不了这样的东西。于是,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怀疑对方是不是也早就已经发现这个东西了。说不定对方比我们走得更快,再磨磨蹭蹭的话必输无疑,而且这一输可能就是致命的,于是就必然会产生将想法付诸实践并制造出实物的冲动。这时,科学家没有时间去深入思考制造这样的东西对人类的未来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而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必须得造出来。当科学家在这种恐惧感的驱使下去制造某种东西时,政治家也会感到恐惧,他们会不惜投入大量的财力为了国家安全去推动这样的研究和开发,造出大量的武器并拿在手里以备不时之需,而且不只是想想而已,而是真的会付诸行动。此外,现在很多人认为,为了国家利益或者为了保卫国家安全,是可以行使武力的。只要这种想法存在,之前所说的这种令人作呕的状况是不会消除的。正所谓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正是这种备战心态驱使着科学家、工程师和政治家。但在现在的状况下,即便手里的粮再多,还是做不到心中不慌,因为将来还会出现更多新的发现和发明,这才导致了现在这种矛盾的状况。大家可能会问,既然有那么多钱,那么多人力,那么多智力,为什么非要利用科学来制造那些恐怖的武器呢,为什么不能利用科学来增进人类的福祉,或者帮助那些发展中国家的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呢?这是因为增进福祉这件事,无法和我们刚才所说的恐惧感发生联系。不增进福祉并不会马上亡国,这不是一个特别急迫的问题,也就是说,即便对方先增进了福祉,也不用担心这一点会对自己造成什么致命的打击,因此这些事是可以从长计议的。于是,大家都忙着去制造那些不好的、恐怖的东西,但在制造好的东西上,恐惧感却完全发挥不了作用,这真是一个充满讽刺意味的状况。
刚才我们讲的都是核武器,但这种局面在更小的规模中也会出现。比如企业之间的竞争,我们只不过是把国家换成了企业,把战争换成了竞争,上述局面依然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只要存在竞争,当出现新想法、新发现的时候,企业家和企业中的科学家、工程师也会担心竞争对手是不是也已经知道了,也会存在害怕对方比自己先做出来的恐惧感,尽管这种恐惧感与被核武器干掉的恐惧感没法比,但是大家自然而然地会害怕自己的公司被对手击垮。于是,每个企业都被这样一种冲动驱使,希望把所有想到的东西都变成现实。而一旦真正制造出产品,又要想着怎么把它卖掉,于是就会用十分夸张的广告吸引消费者来购买这些产品。现在闹得沸沸扬扬的洛克希德丑闻,可以说就是由美国航空器业界的激烈竞争所引发的。在日本国内,各大航空公司之间的竞争,以及贸易商社之间的竞争同样十分激烈,害怕被对手击垮的恐惧感,驱使着这些企业盲目地制造产品,然后千方百计地将产品卖出去,甚至不惜动用贿赂的手段。我们可以说,在现代文明中,尽管不都是核武器这种血淋淋的东西,但弱肉强食的竞争的确造就了上述这些诡异的状况。这种从 20 世纪下半叶开始愈发显著的充满矛盾的异常状况,到底是一种暂时的病态呢,还是一种会一直延续到下个世纪甚至更远的必然趋势呢?我也很想知道这个答案。就像我刚才说的,至少,如果科学技术不会继续进步,到了不会再产生什么新的东西的时候,这种异常状态也就能够得以平息了吧。对于科学是不是有一天真的会停止进步,作为一个科学家,我觉得自己有必要思考一下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先要看一看什么叫科学的进步。人们之所以会制造出像核武器这种自然界中不存在的极其夸张的东西,是因为科学家和物理学家在探索普遍自然规律的过程中需要进行实验,而在这些实验中会引发我们日常生活中所不会发生的自然现象,从而发现一个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大相径庭的世界。我们刚才所说的进步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于是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进步会持续到什么时候。还有第二个问题,拿核武器来说,如果到了一个国家之间不允许进行军备竞赛或者战争的时代,那么这种诡异而矛盾的状况也就不复存在了。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是,国家不再需要通过武力来保卫利益和安全,世界上也不再有战争,这样的时代什么时候才能到来。对于第一个问题,即对于科学家探求普遍规律的可能性,有人认为总有一天会结束,会到达尽头。现代科学中,从力学到声学、热学、电磁学,以及其他各种物理学的领域,还有化学甚至生物学的一部分,我们一直在探索支配所有上述这些领域的普遍规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做实验需要越来越大的机器,同时也需要越来越多的钱。照这样下去,发现新的规律会越来越难,当然,这不是说绝对做不到,但和所得到的结果相比,我们需要花费的能量、金钱、劳动力、智力等代价会变得越来越大。我们在学校里学习法制和经济的时候都学过收益递减原理,拿农业来说,通过增加施肥量等方式可以增加收成,但到达一定程度时收成的增加就会小于为此所花费的成本,这样就不划算了。有人认为对于探索普遍规律的可能性也是一样,终有一天会完结。关于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不认为对普遍规律的探索会有尽头,其实科学的目的也并不仅局限于此。我之前讲过,物理学的目的是以尽量少的定律去解释尽量多的现象,这可能让大家觉得探求这样的普遍规律就是科学的唯一目的,但其实科学还具有与之不同的另外一面。
除了为探求普遍规律而进行各种改变自然的实验,并在人们面前展现一个异常世界之外,物理学中还有另外一种科学,即在我们日常的自然本身之中,也就是在正常的,我们日常的世界中去寻找规律。科学也有这样的一面。因此,尽管追求普遍规律的科学目前是占据了中心地位,但我感觉会有某个时期,现在这种科学可能会让位于另一面的科学。先是牛顿统一了天体和地表的规律,接下来物理学又逐步统一了力学、声学、光学、电磁学等领域,然后又通过量子力学统一了化学的所有领域,现在连生物学的一部分,也就是和遗传相关的部分也被归并到了物理学中。我和桑原武夫先生十分熟识,桑原先生说过一个非常符合他风格又十分恰当的词——“物理学帝国主义” 。我觉得这个词说得非常好,因为罗马帝国、大英帝国也不是永存的,最终都逃不过分裂成若干小国的命运。同样,相比进一步探求普遍规律,对于原本的自然中会产生怎样的现象,又是受怎样的规律所支配,探索这些未知的领域可能更有意义,这样的时代或许有一天会到来,或许这一天离我们并不远,这是我的一点感受。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最近愈发感到,就算不涉及基本粒子的世界,就说在我们身边,还有很多很多未知的东西。即便阿波罗计划已经将人类送上月球,即便我们可以非常精确地描述原子内部所发生的事情,在我们身边依然有太多的东西是搞不清楚的。拿地球物理学这个领域来说,对于天气是如何变化的,地震是如何发生的,我们无法对这些问题进行实验,因此要搞清楚这些问题是没有捷径的。即便如此,地球物理学家们还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现在这一领域中出现了很多新的成果。除此之外,对于我们身边的各种生物是如何生活的,生物和生物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以及我们身体内部的一些事情,尽管分子生物学可以解释遗传现象,但对于这些我们身边的现象依然还有很多搞不清楚的东西。因此,除了去探索那些只有改变自然才能发现的普遍规律之外,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做。我觉得可能是时候把中心的位置让给这些研究了。对于第二个问题,也就是关于社会局势、社会结构的问题,比如改变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创造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这些事情到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这些都是像我这种自然科学家最不擅长回答的问题,我给不了大家一个靠谱的答案,也没有这样的自信,所以只能简单说说自己的看法。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不知道物理学的进步到什么时候为止,或者说物理学帝国到什么时候会迎来终结,但即便假设这一时期现在已经到来,现阶段科学家们已经积累了很多的知识,因此即便科学停止进步,只要对竞争对手的恐惧感依然存在,仅靠现在已经掌握的知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依然存在制造出很多新东西的余地。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在核爆炸实验成功的时候,奥本海默说物理学家尝到了罪孽的滋味,接下来他又说,这是他们无法忘记的知识。这句话是说,对于已经获得的知识,物理学家是无法完全忘记的。因此只要世界上还有这种恐惧感,第一个问题就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也就是说即便现在科学停止进步,当然没有停止进步的话情况会更糟糕,如果我们不想办法尽快解决第二个问题,那么这种矛盾的状况就会依然长期持续下去。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做呢?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我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应该留给各个领域的学者、社会科学家、政治学家、人文学家,或者宗教学家去思考,也许艺术家也应该思考这个问题。大家应该群策群力,共同推动第二个问题的解决。如果科学还会继续进步,就更要先解决这个问题,即便科学不会继续进步了,这个问题也不能放任不管。所以说,科学有两面,它们互相补充才发展到今天。在科学进步的同时,文明也需要思考应如何改变社会的结构,和科学进步一道,摆脱现在这种矛盾的异常状况,否则将会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我的两场演讲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这么长时间的耐心聆听。1976 年 10 月 19 日、26 日于岩波市民讲座上的演讲 本文内容摘自人民邮电出版社图灵文化出版图书《物理是什么》,原文本标题为“科学与文明”,经出版社授权发布,发布时有删减。
本文内容摘自人民邮电出版社图灵文化出版图书《物理是什么》,原文本标题为“科学与文明”,经出版社授权发布,发布时有删减。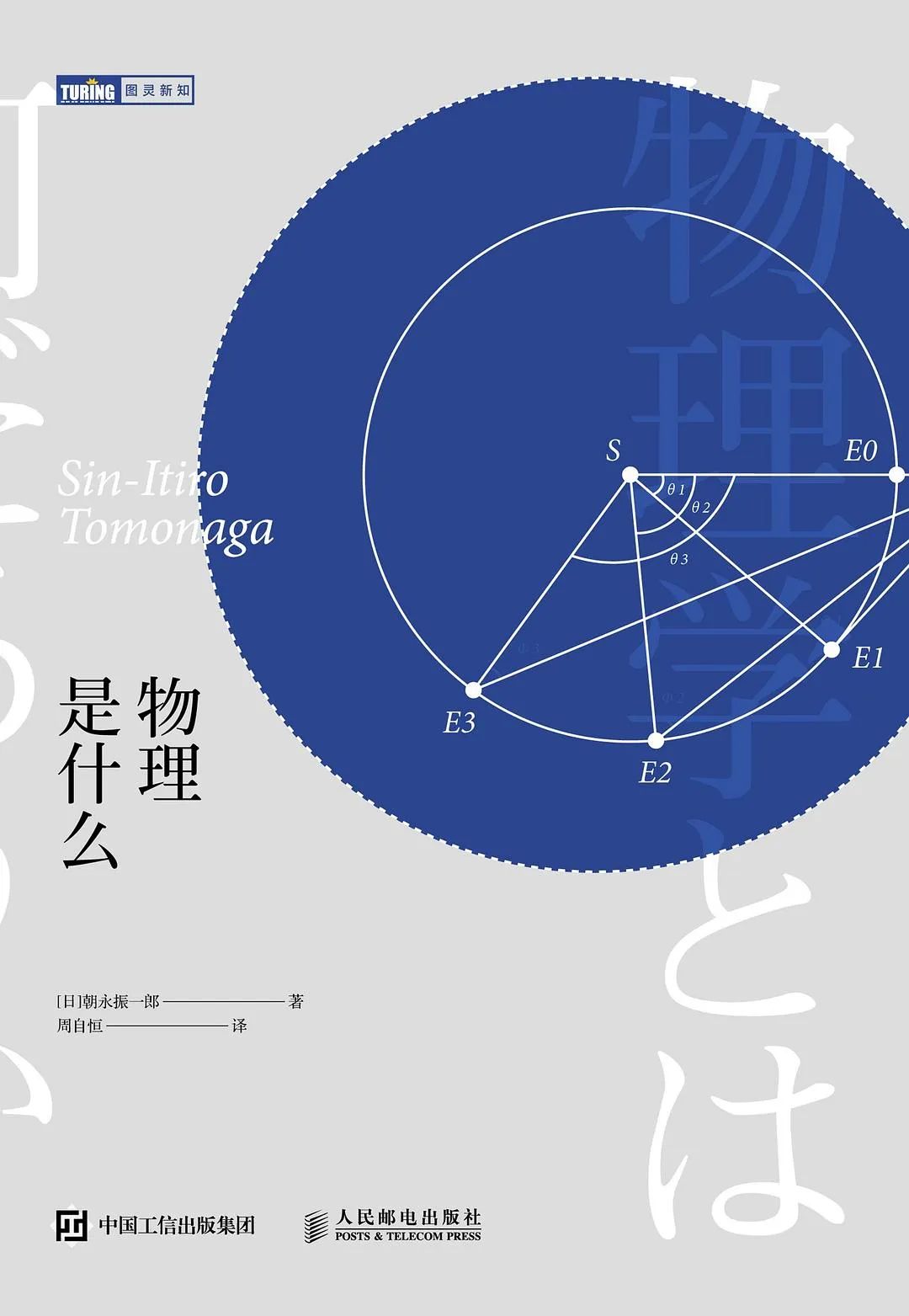
本书已在赛先生书店上架,欢迎点击图片购买。
朝永振一郎是著名物理学家。1906年生于日本东京,京都帝国大学(现京都大学)物理专业毕业。中学、大学期间与日本另一位著名物理学家汤川秀树(日本首位诺贝尔物理学家获得者)就读同一学校。1931年担任日本理化学研究所(Riken)研究员,后留学德国,在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指导下从事理论研究工作。1943年开始研究和发展自己的超多时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重整化理论。1965年,与施温格、费曼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朝永先生同时是一名优秀的教育者,指导过诸多学生。晚年积极开展自然科学的启蒙普及活动,1979年因喉癌去世,本书为朝永先生晚年思考物理的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