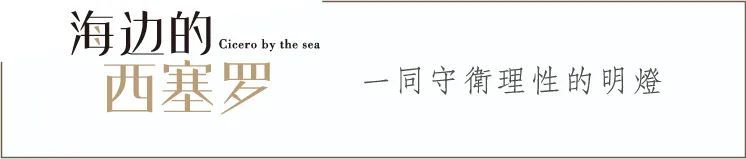
各位好,今天在路上走了一天,没时间写新文章了,昨天聊到了苏轼,就发一篇关于苏轼的旧文吧,晚安。
对中国文学史稍微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黄庭坚和苏轼是一对好基友。黄不仅是“苏门四学士”之首,而且留下了很多与苏轼写诗互怼开玩笑的文坛公案。与苏轼是可谓是标准的亦师亦友的关系,同时代文人当中若说有谁最了解、最认同苏轼,除了苏轼他弟苏辙,那就属这位黄庭坚了。但黄庭坚对苏轼有没有意见呢?有的。他有个外甥叫洪刍,应该是苏轼的狂热粉丝,写什么东西都模仿偶像的笔法。黄知道后写信勉励外甥,夸了一通之后却特地嘱咐了一句:苏轼的文章好是好,但他的吃亏就吃亏在“好骂”之上,你看乌台诗案把他整的那个惨样,外甥啊,咱可千万别学他哈。你可能会觉得奇怪,苏轼?写“大江东去浪淘尽”“明月几时有,白酒问青天”那个?没看出来他的诗怎么喜欢骂人啊?其实,如果先了解一下宋史背景,然后再拿起《苏东坡文集》来读,你会感叹这苏轼老小子头真铁,什么不要命的话都敢说,还都说的那么文雅却又那么损。当时的背景是,王安石改革搞国家信贷,要求各地把“青苗钱”借给青黄不接的农民,等到丰收时再连本带利收上来。在王相公的设想中,这本来是官民两便的事情。但苏轼看到的却是,地方上的官员为了完成上面摊派下来的“青苗钱”任务,把放贷的地点设在了赌场、妓院旁边。农民子弟借了青苗钱之后,受不住诱惑,闷头进去赌和嫖,弄了个“过眼青钱转手空”。成了宋朝版的“套路贷”受害者。然后诗的后半部分,苏轼一通猛“夸”:还是王相公的政策好啊!“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让农民子弟都逗留在城里的勾栏瓦肆里败家,为我大宋的普通话普及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这诗也很过分,苏轼吃货一个,跑到农庄去吃竹笋,你吃竹笋就吃竹笋呗,觉得口淡,非来那么一句“迩来三月食无盐”:原来农民们不是因为像孔子一样因为听了韶乐而忘了味道,而是几个月都吃不起盐了啊!盐铁在中国古代是官办的。王安石改革要为国家聚财,盐政上自然加码。于是盐价就高企了。所以苏轼说来说去,还是在骂王安石——吃个竹笋忘不了这茬,损不损?就问你损不损?这诗写的就更是不要脑袋了。当时,在杭州任上的苏轼八月十五到钱塘江边儿去看大潮,看到当地渔民,赶在大潮的时候还在捕鱼。然后他说:东海若是知道我们圣上的意思,一定会让盐碱地也变成桑田吧。写这诗的时候,王安石已经下野了,宋神宗自己走到前台来推动新政。于是苏轼来了个“宜将剩勇追穷寇”,干脆连着皇上一起讽……“乌台诗案”的时候,苏轼的这些作品都成了他“诽谤朝政”的“罪证”。评良心说,后世明清的文字狱可能多是捕风捉影。但苏轼这个罪名真的没冤枉他,他话里话外就是那个意思。而苏轼自己的说法则是“如蝇在食,不吐不快”——看见他看不惯的事情,他跟吃了个苍蝇一样难受,非要骂出来才行。而且不仅要骂,还是借写诗曲里拐弯的骂——进个城、看个潮、吃个笋,他绕来绕去最后都能绕到怼朝廷上、怼新党、甚至怼皇上那里去……由此看来,黄庭坚说他:“其短处在好骂”,也没算冤枉他。但问题是,黄庭坚只是做了横向对比,觉得苏轼在同时代诗人中“好骂”,如果纵向对比,跟之前的诗人比比,苏轼又如何呢?
读苏轼的诗,你会感觉他诗中的“唐风”很足,而这种“唐风”的最大要义之一,就诗人要借诗表达自己锋芒毕露的意见和风骨。其实翻翻《唐诗选》,你会发现唐朝人写诗很多都是苏轼那个“好骂”的调调。个个都是不怼人不会说话的“祖安老哥”。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同样是写诗骂人,高适没事儿,杜甫没事儿,李白没事儿,到了苏轼这里就出事了呢?难道真的是华夏精神至宋已经中衰,皇帝与唐代相比都更小心眼了吗?在让苏轼倒霉的“乌台诗案”爆发之前,其实出了一件当时还挺受关注的事情:苏轼在京中的好友,驸马王诜(就是高俅的前老板)自掏腰包,帮他结集出版了一本诗集。这套诗集运用上了当时刚刚在北宋开始广泛应用的雕版印刷技术。雕版印刷的刻字精美,苏轼又是当世文豪,诗写的朗朗上口。于是这套诗集一下子成了当时“爆款”,很多读书人争相传阅。而这么一搞,苏轼那些讽喻诗的味道可就变了——唐朝的诗人们在自己的书斋里写写诗,对时局发发牢骚,那真的就只是自己发牢骚而已。顶多诗集做成几个手抄本,传给几个友人在小圈子里自娱自乐一下。而苏轼所生活的宋代则不同,在雕版印刷的助推下,苏轼这种文化顶流的影响力成几何倍数的被放大。你苏子瞻今年到任杭州,写个什么诗骂骂王相公,明年这诗也许就在京城刊印出版了,后年可能就形成舆论压力影响朝局。这可还了得?那对不起了,朝廷为了管控风险,必须把你这个不可控因素摁死。于是,苏学士,委屈一下吧,请带枷来汴京受审。就像复旦的朱刚教授在《苏轼十讲》一书里说的那样,苏轼遭遇“乌台诗案”,原因无他,就是被技术变革的时代撞了一下腰。其实苏轼这还算命好,神宗对他还算法外开恩。因为他那些诗的影响力,后来看其实被低估了。苏轼的弟弟苏辙,后来出使辽国。发短信,啊不,写短诗说:哥,你在辽国火了啊!“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我在辽国这边一说自己姓苏,胡人们就问我:“你可是大苏学士的弟弟?”还拿了你的诗集给我看,究竟是谁把这些诗集传到北京(幽都)来的呢?当然是印刷术,苏轼以前,辽国最火的“网红诗人”还是唐代的白居易,但苏轼那本要命的诗集一出,他马上在那边也成了顶流。但这种大火,对苏轼本人其实是有风险的。苏轼诗歌里那么多诽谤宋朝朝政之语,传到辽国去再传回来,你让宋朝君臣百姓们怎么想?所以,苏辙在后两句中不无忧虑的说“莫把文章动蛮貊,恐妨谈笑卧江湖。”——哥啊,咱低调哈,低调。用今天的话说,用唐朝的习惯写宋朝诗的苏轼,高度疑似史上第一个“给境外势力递刀”或“为辽帝国主义输送攻击我大宋炮弹”的汉奸。幸亏宋神宗没想起这茬事儿来,要不然就算宋朝有“不杀士大夫”的祖训,怕是也救不了苏轼的命。其实双方都没啥错,苏轼只是在按过去的诗人那样写,朝廷也只是按过去的规矩那么判。只不过他们共同遭遇了印刷术这场时代变革。权威与诗人,顿时就不能在一起愉快的玩耍了。从这个意义上讲,16世纪马丁·路德的遭遇与11世纪苏轼的遭遇是异曲同工的,就像苏轼没想过自己仿唐人随手写几首牢骚诗能助推下“过幽都”一样。在路德看来,他当年贴出的“95条论纲”,也不过就是一个青年神学教授对“赎罪券的效能”发表一点自己的见解——这样的论纲中世纪其实还算蛮常见的,马丁·路德起初压根没有什么要跟罗马教廷公开对线的革命觉悟。
但苏轼遭遇了雕版印刷术,马丁·路德遭遇了古登堡印刷术,两个人的文字因此都获得了大大超乎前人和自己意料的声量。这个声量最终让他们不得不与其时代对言论的宽容上限进行一场“对对碰”。在这种碰撞中,幸运的路德撞碎了其时代的上限,三十年战争一打,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一签,欧洲原有的对言论的宽容上限被突破了。社会容忍度对言论做出让步。而在几百年前的东方,这个逻辑反了过来。人们似乎认为,该让步不是社会容忍度而是言论本身。苏轼本人在经历了乌台诗案一通好整之后,写诗收敛了很多。而黄庭坚在总结苏轼的悲剧之后更是提出:“诗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谏争于廷,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坐之为也。”——写个诗,你就不要老想着给朝廷提意见,对世道发牢骚了。既然技术的扩音器被调大了,那你低调点说话不就可以了吗?写点风花雪月它不香吗?但这么一来,诗的意义其实就没了。苏轼以后的文人再也难写出那种“唐风”十足的诗歌。于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中国的文学主流,越来越远离直指时事的严肃文体,向着通俗、闲情和风花雪月去避难。但也犹嫌不足,“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夺朱非正色,异种亦称王”。在步步近逼的不宽容之下,咏叹风花最终也成了杀头的重罪。孔尚任编个戏剧《桃花扇》也能丢官挨整。于是中国的文化最终在“不敢高声语”中陷入了“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沉默当中。龚自珍空叹什么“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写《宽容》一书的亨德里克·房龙曾说,不宽容是人类的天性,而宽容则是一种需要后天习得的技能,且文明越发展,这项技能就越重要。
这个定义很精准,信息技术革命与迭代,总是不断的在给言论赋能、拓张其影响力。而这种成几何倍数增长的言论影响力,与成线性增长、甚至可能难以增长的人类对不同意见的宽容度是难以匹配的。
所以每到了技术迭代之时,社会对言论的宽容度,就会遭受一次考验。前不久,又一位公众号作者师玥宣布封笔、从此不再写了。临封笔前写了一篇文章,自述自己“不是因为不愿意再坚持理想”,而是因为部分读者过于不宽容。这些读者“自己不敢写,甚至不敢转”,又对写手“苛求无数”:不能接广告,不能写不好理解的文字,稍有不合其意,就留言辱骂。师玥还贴出了一部分读者的辱骂内容,骂的确实非常之难听,不堪入耳。我作为一个公号作者,看了这些之后,确实感觉于我心有戚戚焉。我们这些还在秉笔直书、我写我心的作者们,究竟在跟谁作战呢?我毕业后曾在一家传统媒体做过评论员,我记得那时候报社隔三差五,总能接到一些读者电话,骂我的文章写的不合其意——虽然当时在前辈老师们教导、修改下,那些文字其实已经很温吞水了。我记得当时我的一位老师就提醒过我这个问题:你写有观点的文章、揭露性的报道,总会有读者看了不舒服。而这种人出现的概率,是随着你文章的阅读量而攀升的。所以搞文字创作就像用手去扯钢琴线,你用力越猛,就越会被那琴线割伤。而投入自媒体这个行当以来,我越发感到这个道理的真实。随着号的做大,我所遇到的辱骂、苛求,也成百上千倍的增加。抛开404不算,即便那些来自受众的不宽容,也已经让我经常感到逼近我的心理承受极限了。所以,我们正在遭遇的,是另一场“苏东坡悖论”、“马丁路德危机”。在信息技术的极度发达的当下,人类到底是选择固守自己旧有的不宽容,对一切自己不喜欢的言论施以暴力?还是再次释放宽容的底线,让那些声音得以存留?这个选择,现在又摆在了我们面前。如果受众们选择了后者,那么写作者们也会做出与黄庭坚当年相似的选择:所有带刺儿的声音迟早会都大音希声,最后只剩下“今天的天气哈哈哈哈哈”“你好我好大家好”之类的无效信息。只要信息技术继续演进,而受众们固守着自己旧有的不宽容,那些古典气的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少,只因为他们过于“棱角分明”。这是苏轼晚年写的,此时他已经被贬到了惠州。已到广东了,不能在远了吧。所以他做了这首《纵笔》:我满头的白发好像在风中被秋霜染过一般,躺在小楼的藤床上一脸的病容。大家都知道我睡得正香甜,不忍心打扰,连附近的道人,在五更敲钟的时候,手上特意轻慢了许多。可以看出,此时的他,早已没了当年“如蝇在食,不吐不快”的脾气,他已经不想讽刺了,也无意骂谁,只想美美的睡上一觉。可是远远听到“道人轻打五更钟”的苏轼,还是高估了印刷时代千山万水的隔音效果。这首诗传到京城之后,他的昔日旧友、今日政敌、宰相章惇听了不开心:苏子瞻尚尔快活耶?再贬!去琼州(海南)做别驾吧!当技术已经打破了空间的隔音板,人们却仍要固守心中不宽容的时候,可有文案真能让我们纵笔的写作?可有地方真能供我们安心的春睡?所以,为了那纵笔,为了那春睡,请让我们为自己、也为时代选择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