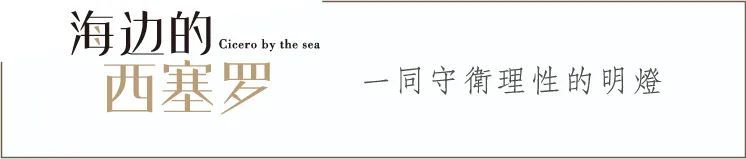
各位好,有篇好稿子被删了,我挺无语。
今天这篇文章我想玩个花活,学学巴赫,来个“对位法”写作——用一新一旧两封信拼一篇文章。
一篇写给懂我这个人的朋友,另一篇写给删我文的朋友。
两篇文章同题、同律,甚至素材也有重合,但一半海水,一半焰火,愿大家能各得其所:

早上接到通知,前天写乌合麒麟的那篇稿子又404了。
每到这种时候,好多朋友私信问我:小西,为啥没了啊,感觉你那篇没写什么不合适的东西啊。
我遇到这种问题就特苦恼——这我咋能知道呢?你得去问删我稿子的人,反正我自己是已经很小心了。
只能瞎猜了,会不会乌合麒麟老师这话题也比较敏感呢?上一次记得我写马保国老师还是谁,也莫名其妙的被404了一次——这种能给人民群众带来欢乐的老师,总是不能多谈的。
但我得说,这种删稿,挺打击我的。大家应该能看出我每篇稿子都写的很费心血,一般一写就写一天,晚上还得看书充电。我写十个钟头,你看十分钟,他删稿一秒钟都不用。严重不平衡。
所以,本来今天还想写个长稿子的,这一来又兴致全无了,只觉得心累。
其实,昨天是著名历史学者何兆武老师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日。本来前天开始我就犹豫过,要不要拿出一天的时间和大号的一个头条,谈谈何先生。
但想了想,最终还是作罢了。只在小号上很简单的写了《今天是何兆武先生逝世一周年,推荐他的几本书》一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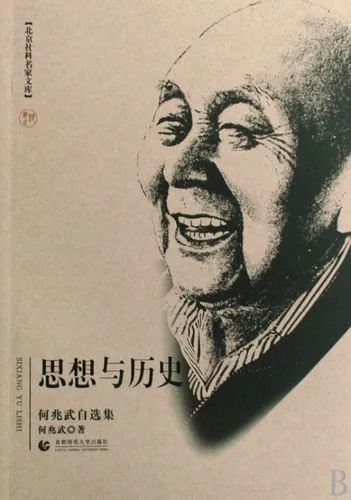
不写大稿子在大号上发的原因,我在这篇文章里也说了。
第一,是我觉得我自己学养还不够,而何兆武老师的思想十分精深,把文章写出来,传出去,万一哪个地方解读偏颇了,不仅贻笑大方,我也负不起这个责任。
第二,是我知道这种文章实在太冷门了,真正的历史学本来就冷门,思想史、史学理论,就更是冷门中的冷门。我现在笔力也没信心把这种东西讲好——虽然我觉得其实这种事情,比时事更有价值。
是的,一个人写东西,到底是先写的足够硬,不避冷门,把有价值的东西讲述出来。还是先写软一点,写有一定热点、有一定关注度的东西,等到你水平练出来了,写的东西也有人看了,再去尝试把真正有价值的思想讲给大家听呢?
我大学时,有位至交好友,记得有一次,我们曾经为了这个问题彻夜长谈,争了一晚上。
后来他选了前者,现在在某大学里做了一位年轻学者,研究一些很精深的、我已经听不懂的史学学问。
而我则选了后者,现在在微信号上给大家天天写文章。
这么多年了,我们两个人的路,到底谁走的对呢?若参照“薪釜论”,又谁是薪?谁是釜?到底是“君为其难,我为其易”还是“君为其易,我为其难”呢?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自己的这条路走的真的很辛苦,很疲劳,很艰难。愿他那边好些吧。
刚刚,我又跟这位挚友久违的聊了聊,他转了我最近写的一篇文章给我,然后评价说:“你在这里面说的,我都很赞同。”
我突然莫名的觉得特别感动——虽然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虽然我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但我们却依然都未忘初心,我们依然还是朋友,是同路人。当年的晤谈、当年的理想。他还记得,我也还记得。
“置酒高殿上,亲交从我游。”这是曹子建的《箜篌引》。我以前一直不理解,在他哥给他那么大的压力下,曹植怎么还能苦中作乐,写出那么多好诗呢?
现在我有点明白了,因为他有亲交,因为他有能理解他、与他意气相投的朋友们。一个且行且歌的诗人,一个且行且思的思想者,只要他还能听到自己的声音有同伴的回应,他就能跨越荆棘,坚定的将这条路走下去。
所以,虽然我走的很累,但我依然是很幸运的。我少年时就有三五好友,如今又能得到如此多读者的认同。在写作中受一点挫折,几篇自鸣得意的稿子心血付诸东流而已,又算得了什么呢?
“外面街上人多,你们别出去。”听说,这是何先生晚年有些糊涂了以后,会对他的学生常嘱咐的话。老人家可能对某些年代留下的心理阴影太深刻了,对人多竟有了一种本能的惧怕。
但我觉得,学者,尤其是人文学者,应当有一份勇力、应当担当一份责任。不惧构陷、不惧刀斧。到人多的地方去,把自己的思考,讲给更多的人听。讲给能听懂的人听。

因为一个人文学者,难道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谨以此半篇文章,给我自己、给懂我的朋友,也纪念何兆武先生吧。
下面这半篇文章,是给删我文的那位朋友的,是篇旧稿重发,但我依然愿意称他为朋友——因为我知道人人都有他的局限与无奈。
前几年看过一个电影,叫《你好,疯子》,说有七个人有一天突然被抓到同一间精神病院里,主治大夫也不告诉他们为啥关他们,就让他们在一间厂房里自己讨论,同时开了个监视器进行监视。
接下来乐子来了,面对医生硬说你是精神病这种神奇的境遇。这帮人怎么证明自己其实没病呢?于是他们做体操、搞合唱、办行为艺术,做出种种滑稽举动,以证明自己精神正常。这帮原本没病的人,此时反而更像是精神病了。当然《你好,疯子》后面还讲了很多其他事,但我觉得这一段提的一个问题特别深刻:最容易把一个正常人逼疯的环境是什么?是他的生死荣辱完全被拿捏在另一个主宰的手上,那个主宰随意的给出安排,却又不告知理由,对被掌握者的反馈也不给出回应,时间一长,被掌握的那人不精神崩溃才有鬼。你对揉捏你的那个主宰说,够了吧,我想跟你好好谈谈。你在他面前只是虫子,面对你交谈的请求,他只是冷哼一句:“毁灭你,与你何干”。卡夫卡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审判》,说有个银行高级职员约瑟夫·K,某天早晨醒来突然无缘无故地被某个神秘法庭逮捕,并被宣判有罪,然后释放了,虽然K的行动自由之后并不受限制,仍然可以像往常一样生活,但他知道有一个必然执行的死刑等待着他。K当然想不通,四处上告、求助,但压根没人理他。最后,在他31岁生日那天,他在根本不知犯了什么罪的情况下“像狗一样被处死”了。
卡夫卡的小说写得都很荒唐,但最荒唐的也许莫过于这篇——你活的那么努力,人家审判你却那么随意,随便到连个罪名都懒得给你。你想谈谈,但没人理你。你越发发现自己的卑微渺小与可笑。每次被删稿,我这种感觉就特别强烈。就像昨天那篇文字,我觉得我的大多数表达已经很柔和了,甚至稿子删了以后,很多转载我文章的号还能看到此文,并点击量客观,足见其实没有什么犯禁的地方。可是文章为什么就404了呢?我这么努力的写,读者那么认真的讨论,就换来这个吗?可是我又无法愤怒,甚至我也无权愤怒,更确切的说我连惧怕都来不及。因为微信公号稿子发不发、删不删其实的都是腾讯官方的权力,就像推特想禁特朗普几年,在美国现行法律下他们有随意处置权一样。而现在写稿已经成了我唯一的收入来源,这条路不能断,所以我不能想、不能写不能发的稿子(这话说的有点绕,但就这个意思)。因为我要生存下去。我想做什么?我无非想做一个写点自己喜欢的文字的人,让读者能欣赏,自己也能挣钱糊口,仅此而已。我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如果真的“生逢其时”,它应该允一个大龄青年满足他这点最卑微的愿望。
所以我必须像《你好,疯子》里的那些被关者一样做出表演,哪怕这些表演其实无用。第一,最近一段时间,至少近几个月内,进一步缩减本号谈时事的比例,多写写艺术、文学。比如昨天那个稿子,如果只分析一下宋江人格,我觉得应该是篇还算比较安全而且有味道的文学评论。多说最后那一段干嘛,实在是我多嘴了,跟一定要加一句“敢笑黄巢不丈夫”的宋江一样。第二,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之前我已经开了知识星球,给我的VIP读者群提供一些更深度的知识服务。下一步可能视频和其他媒体平台我也会开起来。想看我更多文字的的读者可以移步。
我初步的想法,是想先出一个现有文章的精修编缀版,因为之前由于我写稿比较快,很多文字没有精心编辑过,读者看了会感觉比较硌牙,重编一下会更好些。另外我个人能力有限,文章的配图、编版始终没有达到自己预期的效果。如果再加工一下的话可能会好些。早前已经有好几家出版商朋友跟我联系,现在还都在谈。也请有意向的出版商朋友联系我,我择优挑选,大家争取一起把这件事为读者们做好。暂时就先想到这么多吧,今天真的很累,心累。昨天稿子被删之后,有好多读者留言让我私信发给他们,抱歉,相关要求太多,我实在来不及都回复。另外,我觉得既然微信大大把稿子删了,肯定是不想让此文传播的太广。
那就这样吧,让此文随风散去。文章我再仔细检查一番,最不敏感的那些部分,我会挑个另外的机会发一下。但不是现在,现在重发,给人感觉我在跟微信顶牛,而我不想给人造成这种印象。当然,有些朋友从别的转载甚至抄袭的号上看到了该文,也好,原稿被删、转载甚至抄袭却挺火,这种事我也不是第一次遇到了,也没办法,您能喜欢我的那篇文字就好。但有读者说,有的号在这篇文字底下贴了他们自己的二维码骗打赏。在此特地声明一下,我所写的所有文字,只有在本号上打赏,您才能够真正帮助到我这个码字为生的“文字码农”。今天心情很不好,本想不到什么好音乐能配,但从昨天起我总莫名的想着曹植的《白马篇》。可能自古以来,所有想做一点事的人,人生都是在刀尖上跳舞的。但即便七步诗能做出来,曹丕弄他,也不需要理由,谁让人家是哥呢?本文4000字,感谢读完,写作确实不易,喜欢请三连,今天其实也算篇谈心的请假条,就这么休更好了。祝大家周末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