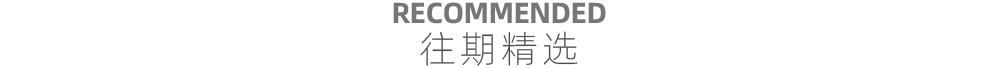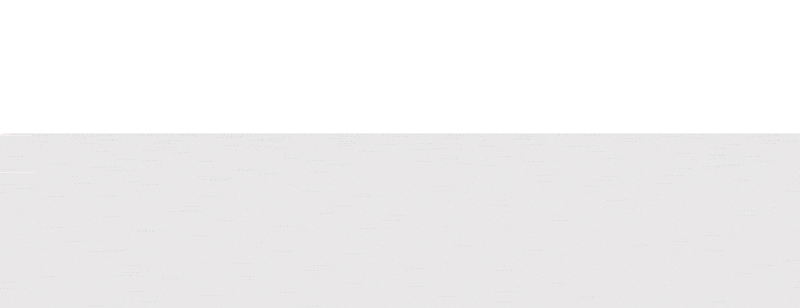“我最后的乐章至此落幕”,与癌症抗争了9年后,日本著名作曲家、“教授”坂本龙一3月28日与世长辞,享年71岁。
他最后一次进入大众视线是2022年12月18日,一场提前录制好的、被粉丝称为“告别”的音乐会。坐在钢琴前的坂本龙一身材消瘦,精神不佳,但仍可以感受到他在努力奉献一次高水准的演奏。
作为久负盛名的音乐家,坂本龙一在中文世界广为人知似乎也是近十余年以来的事。或许你没听过“坂本龙一”这个名字,但是你一定听过《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Merry Christmas Mr.Lawrence)《Energy Flow》或是电影《末代皇帝》中的主题配乐——这些脍炙人口的旋律在今天的互联网传播效应下拥有了极高的知名度和辨识度。
出道于1970年代末,80年代以来坂本龙一凭借其在前卫电子音乐和电影配乐的斐然成绩在海内外一举成名,进入21世纪后又以社会活动家的身份对反战、反核等社会问题频频发声……坂本龙一的不断“出圈”,无疑使他成为了兼具“偶像”和“严肃”的东亚文化符号。而这次患癌的消息在中文互联网的“刷屏”则又一次将他推到了台前,引发了人们对他的作品及生平的关注和讨论。1952年1月17日,坂本龙一出生于东京都中野区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担当过三岛由纪夫《假面自白》的文学编辑坂本一龟,外祖父下村弥一则是创立了日本佳速航空(JAS)的著名实业家。在家庭氛围的影响下,他很早就表现出了对音乐的兴趣和天赋。中学期间,坂本龙一在钢琴老师的介绍下拜入东京艺术大学教授松本民之助门下学习作曲,打下了深厚的古典音乐基础。1960年代正是摇滚乐浪潮席卷全球的黄金时代,除了巴赫、贝多芬等古典音乐家,披头士(The Beatles)和滚石乐队(The Rolling Stones)也给青少年时期的坂本龙一造成了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德彪西、拉威尔等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印象派”作曲家也对当时的坂本龙一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德彪西的《g小调弦乐四重奏》打破了传统古典音乐的调性与和声功能的束缚,使用了更为丰富的和弦音来表现音乐的“色彩”。而“德彪西转世”的梗也直接出自他的自传:“或许由于太过着迷,我逐渐将自我与德彪西混在一起,对他经历的一切感同身受,渐渐认为自己就是早已逝世多年的德彪西,觉得自己就是他投胎转世而来。”——坂本龙一《音乐即自由》高中时期,坂本龙一接触到了约翰·凯奇(John Cage)、白南准(Nam June Paik)等60年代“激浪派”现代艺术家的作品。彼时正是凯奇刚刚访日后不久,日本的前卫音乐界还沉浸在“Cage Shock”的余波中。凯奇从东方的禅宗、易经等传统文化中受到启发,将“沉默”和“随机性”运用到作曲里,深刻地影响了当代的艺术实践。除此之外,达达主义、现象学、未来主义……这些前卫艺术与哲学理念也深刻地影响了坂本龙一的“三观”。由于作曲老师的关系,坂本龙一顺理成章地考入了东京艺术大学作曲科,毕业后又读了两年研究生——“教授”的绰号也源于此。除了入学考试时“五小时写一首赋格,七小时写一首钢琴奏鸣曲”这些乐迷们津津乐道的故事之外,大学期间坂本龙一系统学习了小泉文夫的民族音乐学课程,并接触到了当时还十分新颖前卫的电子音乐。仿佛冥冥之中命中注定一般,这些经历也成为了他今后重要的创作来源。大学毕业前后,坂本龙一没有选择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而是为了维持生计以伴奏乐手的身份活跃在东京的各个录音棚、地下剧场,甚至是酒吧和咖啡厅。尽管“接散活”没有固定的收入,却让他有机会认识活跃在当时东京音乐圈的重要人物:大泷咏一、山下达郎、铃木茂、林立夫、阿部薰……以及改变了他一生的重要伙伴:细野晴臣和高桥幸宏。至于YMO(Yellow Magic Orchestra)的成立,则充满了历史的偶然:细野晴臣在计划翻奏马丁·丹尼(Martin Denny)的《Firecracker》时通过经纪人介绍认识了坂本龙一,而高桥幸宏在这之前就已和二人分别熟识,经常一起录制音乐。作为命名者,细野希望YMO能够在“白魔法”(白人音乐)和“黑魔法”(黑人音乐)中杀出一条属于“黄魔法”(亚洲人)的道路来。原本只是抱着玩玩看心态的坂本龙一与其他二人一拍即合,在1978年底发行了他们的第一张乐队同名专辑《Yellow Magic Orchestra》。这张专辑的大部分曲名都取自法国导演戈达尔的电影,例如《东风》《中国女人》和《狂人皮埃罗》。三人在这张专辑中各自加入了自己喜欢的音乐元素,例如德国Kraftwerk(发电厂)乐队和英国的New Waves(“新浪潮”)中使用模块合成器生成的电子音色。坂本龙一有深厚的古典音乐基础,高桥与细野二人虽然不是科班出身,却对50年代以来的欧美流行音乐,特别是摇滚乐和爵士乐了如指掌。YMO将“Techno Pop”这一电子音乐风格与极具东方异国情调的旋律融会贯通。加上吉他手渡边香津美、歌手矢野显子等共演乐手出色的即兴演奏,作为“资本主义音乐潮流”下诞生的YMO在欧美演出时意外地获得了当地乐迷的青睐。这样“互补”的一支乐队所爆发出的能量无疑是巨大的。1979年,随着第二张专辑《Solid State Survivor》的发行和第一轮全球巡演的结束,YMO在欧美和日本收获了超高的人气。截止到1981年,YMO的唱片在全球唱片市场销量总共超过了500万张,坂本龙一也因此一夜爆红。“也许是因为在海外大受好评的缘故,有些人过去根本没听过YMO,现在也都知道我们了,甚至可说是一种社会现象。我先前的人生中,一直都希望自己不要出名,不要成为公众人物,然而当我注意到的时候,自己早就成为了人人讨论的对象,甚至连走在路上都会被指来指去。这样的情形超出我原先的想象,实在是让我相当困扰”——坂本龙一《音乐即自由》YMO的成功给坂本龙一带来了财富和名气,也带来了其他的烦恼。三人合作固然能实现一个人无法做到的事情,但对坂本龙一而言,这样的合作势必会在个人表达上造成妥协,继而无法“尽情创作”——这也是YMO后来解散的一个重要原因。怀着这样纠结的心情,坂本龙一在1980年抛开其他二人创作了个人专辑《B-2 Unit》,在这张专辑里他“将YMO当成了假想敌”。这一行为也被高桥和细野二人看在眼里,1981年二人在YMO的新专辑《BGM》中同样瞒着坂本龙一创作了歌曲《Cue》(线索)。这首意味深长的曲子由于没有坂本龙一的创作参与,他“只是负责敲打节奏,同时心里想着,这根本就是他们二人对我的报复”。1983年底,YMO举办了最后的国内巡演“1983 YMO Japan Tour”后宣告“散开”。YMO期间的坂本龙一创作出了令世人惊艳的音乐,也和其他成员有过针锋相对的争吵,甚至产生过憎恶情绪。为了给这段旅程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他们三人默契地决定用这场巡演作为各自音乐旅程的新的起点。1983年12月22日的日本武道馆演出之后,YMO正式宣告解散。早在YMO解散之前的1982年,三人就独立开始了各自的音乐活动。例如为广告配乐,或是帮助其他音乐人制作专辑等等。坂本龙一在这一时期走上了人生的另一个转折点:电影配乐。1982年,日本著名导演大岛渚邀请坂本龙一出演他的新片《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中“世野井”一角。在导演邀请其演出的时候,年轻气盛的坂本龙一随口表示“配乐也请让我来做”。出乎意料的是这一“无理”要求竟然得到了导演的同意——而坂本龙一之前并没有任何电影配乐的经验。凭着一腔热情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他在导演和制片人的支持下创作了电影配乐,其中就包括他最有名的作品《Merry Christmas Mr.Lawrence》。这部讲述二战时期日军战俘营内部同性恋题材的电影,在1983年的戛纳电影节上大放异彩,虽然最终在金棕榈奖的角逐中输给了今村昌平的《楢山节考》,但是摇滚巨星大卫·鲍伊(David Bowie)同日本电影新浪潮的代表导演大岛渚的合作无疑引发了巨大的话题。而坂本龙一的电影配乐则在当年获得了第37届英国电影和电视艺术学院奖,以及第7届日本电影学院奖的最佳配乐。这让作为“电影配乐家”身份的坂本龙一在电影界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在戛纳评奖期间,坂本龙一得以接触到世界各国的著名电影人,其中就包括意大利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在当时,他就同坂本龙一提到过筹拍《末代皇帝》的事宜,而请自己出演并制作电影配乐则是当时的坂本所没有想到的。1986年,《末代皇帝》剧组在北京故宫开始拍摄,这也是新中国第一次允许剧组(尤其是外国导演的剧组)在故宫“包场”拍摄。空旷的古代宫殿与紫禁城外川流不息的、骑着自行车的人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至今还能通过声音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大街上有很多自行车的声音……但是紫禁城很安静,很空荡,仿佛仍然有皇帝住在里面,尽管我们知道它是空的。我还记得那里的风的声音,这让我感觉有种孤独和悲凉的感觉。”——《十三邀》 许知远采访坂本龙一在这部影片中,坂本龙一受邀出演“满洲映画协会”会长甘粕正彦一角。性格桀骜的坂本在得知剧中的甘粕正彦是以切腹自尽(历史上是服毒自杀)作为结局的时候,和导演产生了不小的冲突:切腹在西方人眼中或许是一种独特的、很“东洋”的仪式,在坂本龙一眼中,这种“刻板印象”却让他十分反感。双方僵持不下,最终坂本龙一表示,“如果要拍切腹我就不演了”,这才让贝托鲁奇同意将结局改为举枪自尽。长春是坂本龙一的父亲在服兵役时曾经驻扎的地方,当年关东军占领东北时期留下的宿舍、厂房等建筑也被保存至今。儿时听父亲讲述的回忆逐渐浮现在眼前,坂本龙一不禁百感交集。在这里,他被委托写作溥仪“登基”伪满洲国皇帝时现场的背景音乐。之前从来没有写作过中国音乐的坂本龙一,用一架老旧的有些走调的钢琴,凭借自己扎实的作曲功底和对“伪满洲国”的想象,写了一段“有法国风格的,不伦不类的音乐”。拍摄完成约半年后,人在纽约工作的坂本龙一接到了《末代皇帝》制片杰里米·托马斯的电话,要求在一星期之内为《末代皇帝》制作其他配乐。尽管听起来是个无理要求,但坂本龙一还是以两星期为限接受了这项工作。这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回到东京的坂本龙一一边进行作曲,一边和伦敦正在剪辑的工作人员沟通。远程传输一首乐曲,无论是曲谱还是录音文件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都是一眨眼的事情,但在当时则需要耗费一个小时左右。坂本龙一在助手的帮忙下一星期创作出44首乐曲,并带去伦敦录音。如此不眠不休地工作半个月下来,坂本龙一因过劳而住院,所幸努力工作的成果并没有白费。《末代皇帝》横扫1988年第60届奥斯卡9项大奖,除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奖项外,坂本龙一、大卫·拜恩、苏聪三人也抱走了最佳原创音乐的金人。坂本龙一自此跨入世界级电影作曲巨匠的行列,这是他自YMO以来的第二次事业的巅峰。在这之后,他继续同贝托鲁奇导演合作,完成了“东方三部曲”中另外两部作品《遮蔽的天空》《小活佛》的配乐。近年的作品包括《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荒野猎人》《黑镜第五季》等,坂本龙一以日本人独特的感性,活跃在世界电影音乐舞台上。坂本龙一在1990年因为工作原因移居纽约,并长居至今。离开日本,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生活,坂本龙一仿佛一棵无根的浮萍。好友村上龙来纽约工作时顺路拜访,说“你有一股移民的气息”。而这种距离感似乎又给了他一种新的视角,去重新审视他一直以来的生活和创作。1992年,坂本龙一推出了新专辑《Heartbeat》,即心跳的节奏。Heartbeat也是胎儿在母体内听见的声音。除了表达对移居纽约之后“探寻某种新的起点”的态度,也充满了他对美国领导发起的海湾战争的一系列态度和思考。
〓 2019年,坂本龙一感受他限量版唱片中所附乐谱纸张的触感。上世纪90年代至今,作为作曲家的坂本龙一也频频在一些社会议题上发言,或通过作品表明自己的态度。这并不是一个突兀的行为,早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坂本龙一就已经积极地投身到当时轰轰烈烈的“反战”“反美”的学生运动中。成长在战后的一代年轻人经历了当时民众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续订的“安保斗争” ,在60年代深受法国的“五月风暴”、中国的“文革”,以及美国的“嬉皮士”运动的影响,天生带有一种“反叛”的标签。经历过战争创伤和战后重建的日本人深知战争给人民造成的苦难,因而在看到诸如卢旺达内战、伊拉克战争等消息的时候,坂本龙一选择将这些问题用音乐的形式表达出来。90年代后期,坂本龙一接连创作了《Discord》(不协和音)、《BTTB》(Back to the Basic,回到起点)以及歌剧《LIFE》,表达了自己对创作的初心,以及对20世纪以来的人类社会因为革命、战争、冲突而逝去的数千万生命的纪念。2001年纽约的“9·11”恐怖袭击事件,身处纽约的坂本龙一目睹了世贸大厦起火、坍塌的过程。他下意识地按动了手里的相机,照片里燃烧着、冒出滚滚浓烟的双子塔和面前飞过的小鸟对坂本龙一造成了巨大的震撼。“曼哈顿的音乐似乎在一瞬之间都消失了。事情发生一周之后,我走出家门,听到广场上有人在弹《Yesterday》,这才回过神来,原来自己也已经7天没有听音乐了……可见音乐文化只能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下才能存在吧。”——坂本龙一纪录片《Coda》恐怖袭击以及随之而来的战争让坂本龙一意识到人类生命的脆弱,更对战争造成的“仇恨循环”感到深深的忧虑。当年的11月20日,坂本龙一出版了评论集《非战》。年轻时期经历过反战运动游行的他,对新时代的“反战”有着自己的看法:“非战”不是“反战”,如果一味地“反”,最终只会被你所反对的东西吸收或者同化。因此“战争”的对立面应该是“非战”,即不要战争,远离战争,我们应当思考的是如何弥合不同文化之间的对立与裂痕……这也是坂本龙一2004年2月的专辑《Chasm》(裂痕)所表达的理念。
2017年上映的纪录片《坂本龙一:终曲》记录了坂本龙一自2014年被确诊癌症以来一边艰难地对抗病痛,一边以“将每一部作品都当成最后一部来创作”的精神来工作和生活的日子。2011年的日本“3·11”特大地震以及随之而来的福岛核泄漏事件,给日本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这也是继切尔诺贝利之后人类社会最大的核污染危机。福岛核泄漏勾起了日本人作为唯一一个遭受过核弹袭击的国家人民的恐怖记忆,在此之后,日本社会反对核电的呼声日益高涨。《终曲》的片头,坂本龙一手持辐射检测仪行走在福岛灾区的街道,在一个废弃的舞台上检查一架被海水浸泡过的跑调的钢琴并尝试弹奏它——在他看来这是“钢琴在努力恢复成原有的样子”。2012年以来,坂本龙一时常前往福岛地区进行义演。对他而言,无论是参与反核集会,还是为灾区义演,个人的力量也许微不足道,但是至少能给正在遭受苦难的人带来些许安慰。很难说前往福岛灾区现场考察的经历与他后来患癌症之间是否有必然的联系——众所周知,长期暴露在有核辐射的地区会极大地增加患癌的几率。坂本龙一在停掉一切工作专心治疗的同时,也重新思考了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我们看到在纪录片中,坂本龙一从一位擅长旋律的作曲家,忽然变成了手持录音机采集各种生活的音响素材作为“音乐”的声音艺术家。他站在家门口和树林中拾取鸟叫、树叶、雨滴等大自然的环境声;也将话筒伸到北极圈冰川下的水流中录制“地球上最纯净的声音”;甚至拿着金属质地的小细棍在大街小巷的建筑、雕塑、装饰物中间敲来敲去……这一切都凝结成了他2017年的专辑《Async》(异步)。纪录片《坂本龙一:终曲》中,用水桶盖住头试图收集雨滴与容器碰撞的声音近两年,坂本龙一在中文媒体“出镜”的频率逐渐增加,2019年底,“教授”开通了个人官方微博,打开了与国内网友和乐迷沟通的新的窗口。2020年春天,在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最为严重的时候,坂本龙一与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和快手合作了名为“Sonic Cure”的线上音乐会,当天累计观看的人数超过了300万。在内地谈话类节目《十三邀》中,提到癌症带来的恐惧时,他回答道:“我们必须像老子一样微笑地接受这个过程。这是很难的事情,也许我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还无法接受,但我希望我能做到。”在《Async》中的《fullmoon》一曲里,坂本龙一引用了自己曾经为其配乐的电影《遮蔽的天空》原作小说里的一段对白,或许可以视作他对癌症、对人生的态度:因为我们不知道何时死去,所以会把生命当做永不枯竭的井。然而很多事情在我们生命中只会发生几次,很少的几次。那些失去了,你就不再是你的午后。四次?五次?也许还没有这么多。你还能看到多少次满月?也许20次,然而像还能看到无数次一样。“要保持每天创作啊,现在(身体状况)有点糟糕了呢。”在《终曲》的最后,坂本龙一有些羞涩地对着镜头笑着说道。(作者为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声音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日本声音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