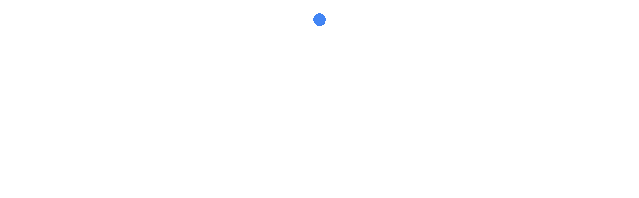
“明明什么也没干,还是觉得很累”
“活是不想活了,死又不敢死”
“做什么都觉得没意思,感觉自己已经失去快乐的能力了”…
如果说几年前流行的“葛优瘫”多少还有点调侃戏谑的成份,最近的躺平则带有一种包含了真实情感的沉重。
人生无意义、无价值感不再是个例,而更像是一种在群体中蔓延的传染病。在维持了基础的生存之外,我们的生活被各种各样的信息和娱乐填满,但我们不仅无法因此获得满足,反而感到更高密度的空虚和麻木。
从好友间的日常吐槽到影视剧的人物设定,可以感受到“丧文化”似乎越来越成为一种主流。
如果说痛苦至少是一种深刻的感知,“丧”所代表的精神空虚、感官麻木则更为严重,意味着一种存在感、意义感、价值感和幸福感的缺失。
社长老梁就跟大家聊聊当下流行的“丧”。


“丧”——一场全球性的精神危机
去年年底,心理咨询师崔庆龙发了一条微博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心理效能”相关内容的输出。面对“你有多久没有体验过那种一觉醒来,充满着活力和期待完成一天事务的感觉?”这一问题,很多人感到“被击中”了。当心理效能低,人在重压之下,会产生倦怠、匮乏的情绪感受,就像一块没电的电池,不再有快乐、希望和行动力。
日本知名学者大前研一在几年前就针对日本的社会经济现状提出了“低欲望社会”这一概念,指出日本年轻人已进入了低欲望状态——不婚不育不买房,失去梦想和干劲。
无独有偶,盖洛普公司最新的调查显示,仅38%的美国成年人为自己是美国人感到“极为自豪”,这一比例创下自2001年开始此类调查以来的最低值。
“所有这些数字都表明,人们并不觉得自己是可以相信并为之奉献一生的更大叙事的一部分。”

美国作家戴维·布鲁克斯提到目前美国存在的危机之一是“特洛斯危机” ,即“许多人不知道这个国家为何而来,我们为何而来”。
依据他的经验,特洛斯危机有两种常见形式,即走肉模式和躺尸模式。前者意味着背负着痛苦迷茫继续在原有道路上艰难地前行,后者则是就地躺下,自认无能为力而选择默许或接受这种停滞不前的状态,而不论是哪一种,也是当下我们很多人的真实写照。

“丧”就像溺水,该如何自救?
如叔本华所说,“为了和其他人一样,我们失掉了四分之三的自己”。长大是人的社会化不断加深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面对既定的框架和标准,我们用天然性和独特性做交换,以获得接受和认同,为了生存,我们麻痹和欺骗自己,隐藏和压抑真实感受和诉求,久而久之,变得迟钝和麻木。

除此之外,社会结构、世界局势、整体性的文化氛围等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像海草一样缠住我们。该如何才能摆脱如溺水一般的“丧”?
这听上去像是一句正确的废话,但它的确是个体自救的最佳方式之一。群体化的空虚、迷茫和无意义感不只是这个时代特有的病症,战争、瘟疫、时局动荡…历史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重复上演。正如“得到”作者刘怡提到的那样,“我们无法完全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但我们的确可以拥有时代以外的自己的世界。寻找存在的意义和自己的热爱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个体的终身课题。“一方面我们觉得要去有一个好学位、好工作,一方面晚上回到家我们又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没有意义。然后总是在想,当我做完这一遭以后,我要好好干有兴趣的事情。”人类学家项飙的这段话反应了当下很多人的状态——“想要”和认为的“必要”看似并不统一,甚至背道而驰,但为了眼前的稳定,我们选择搁置“想要”,被迫接受和执行“必要”,寄希望于这份违背意志的经历有一天会成为改变的底气。但是正如项飙所言,“人的生命很短,眨眼你就变老了。如果希望过了这个瓶颈期之后会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很可能这个世界永远不会到来。”
诗人谢默斯·希尼说,“你不在此处,也不在彼处;匆匆忙忙中,已知和未知都会被错过”。时代和环境固然有其局限性,但不应该成为我们放弃和逃避的借口。被迫停下同样也是一个契机,让我们得以回望过往的得失并重新思考和厘清“我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对于我而言,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哪些是可以放弃的,哪些是必须抓住的”这些问题。比起知道自己的兴趣却无法实践,更多人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兴趣和热爱是什么。我们多数人都是按照家庭或是社会规划好的路线扮演着固定的角色,只有在某些特定时刻会忽然意识到“啊,好像从没有为自己活过”。但长久的按部就班让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热爱该从何谈起。梁永安教授在综艺《屋檐之夏》中提到过伊朗电影《樱桃的滋味》中的故事,他试图借此启发我们当我们觉得生命没有意义时如何寻找出路——“一个男人结婚之后面对生活的不如意想要到果园里上吊寻死,但因绳子不结实所以摔了下来。当他重新爬到树上系绳子时,无意中摸到一个软软的东西,原来是一颗桑葚,是他以前从未吃过的东西。后来天快亮了,有一群小孩子路过那棵树上学的时候朝他喊,让他丢一点桑葚下去。小孩子的蹦跳和欢笑让他的心忽然明亮了起来。”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也都会有这样一颗桑葚、一群小孩子或这样一个充满人生隐喻的瞬间,可能在旁人看来微不足道,但他们的存在折射出了生活本身的无限性和多样性。不管生活在我们的对外陈述中多么黯淡和贫瘠,其中一定还存在着能让我们的感官、情绪、思维活跃起来的部分,这些部分可能尚未被我们发现和充分利用。事实上,早有研究发现,相信兴趣是待被发现而不是发展的人,对生活的热情更少,对新鲜事物的接受度也更低。如果我们想要看山,就不能等着山自己走来,唯有主动向山走去。随着网络生态的日渐丰富和完善,以社交平台为代表的虚拟世界越来越成为我们逃避现实生活的出口和精神寄托。但这种“沉迷”无法帮我们真正建立对现实的耐受性和宽容度,改善我们和现实的关系。相反,回音壁效应会不断放大和强化我们既有的印象和感知。基于互联网的“虚拟的组织化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它有极强的选择性和被选择性”,我们通过选择相同的圈子、聆听相似的声音来获得熟悉感和安全感,但这实际上只不过是另一种方式的自我重复。美国心理学家路易斯·柯佐林诺提出了“社会突触”这一概念,意在提醒我们一种超越个人主义的幸福愿景必须以真实的、肉身性的、与他者的“相遇”为前提,“所谓社会突触,就是社群成员的空间。也正是它使我们从属于更大的有机组织,例如家庭、部落或社会。我们的微笑、问候、寒暄等等行为,都凭借符号、声音、气味和话语进入这个空间”。基于同样的对社会原子化的观察和对城市生态的思考,人类学家项飙提出找回和重建附近这一实践,即从以自己为起点的“最初500米”出发,与这一范围内的活生生的人们进行互动。他呼吁人们把目光重新投向自己身边的事物,在破碎的年代,重建小共同体。根据项飙的描述,“附近”具有“体感性”和“异质性”这两个重要的特性。“体感性”代表我们与世界的互动是直接而真实的,这种面对面、实体对实体的互动可以帮我们更好地感知自身的存在。而“异质性”恰好与“选择性”相对,对于“附近”来说,它没有事先确定的共同的话题,各种差异会毫无预演地进行亲密的接触、多方位的交叉。因为遇到的人不确定,对方可能是对门孩子正在上小学的夫妻,也可能是每天帮我们送餐的外卖小哥,亦或是楼下正谈着黄昏恋的大爷,他们的话语、行为、主张、动态等等一系列因素于我们而言都意味着陌生和未知。正是这种“异质性”让我们的互动变得复杂而全面。虽然这种互动不会直接为我们带来愉悦感,甚至在最初会让我们感到有些“不适”,但却可以有效锻炼我们的社会大脑,对我们的身心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从项飙提出的 “最初500米”出发,我们可以将“附近”的概念延伸得更远——与虚拟相对的、能够亲身参与和感受的都可被称为对“附近”的实践——不论是与好友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和宠物来一次草地上的赛跑,还是走上街在饮品店新换的菜单里感受季节的变化,这些细微和平凡的日常都是由我们亲身构筑或参与的一部分,即使不够完美,这种物理的接触和互动都可以帮我们更好地建立与真实世界的联结。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曾说,“人不是活一辈子,不是活几年几月几天,而是活几个瞬间”。如果未来捉摸不定,那就暂时把它放在一边吧,起码我们还有当下可以珍惜。- 《GQ报道|不确定的环境,心理咨询有用吗?》,作者:杜梦薇,公众号:GQ报道
- 《我们正在对很多事情失去热情》,作者:[美]布鲁克斯,公众号:楚尘文化
- 《“没精力工作、游戏玩腻了,找不到对生活的兴趣。”|KY研究:如何能“活得有意思”?》,公众号:KnowYourself
- 《项飙:海子说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为什么不是从现在开始?|十三信箱》,公众号:单向街书店
- 《“允许自己不快乐”:快乐是一种能力吗?》,作者:孙慈姗,公众号:新京报书评周刊
社没【AI+个人发展深度思考群】继续邀请中,分享社长对于「个人发展、内在成长、职场或亲密关系、新个体IP、AI式趋势」等方面的深度思考和判断~如果你对感兴趣,不妨加下方社长老梁微信,邀请你入群,请发暗号:个人发展深度思考 。还有见面礼盲盒哦,包括:小课、好书解读或者闭门会精华PPT。
作者:吴佳木
编辑:留木
你可能还喜欢:

实在撑不住就哭一场吧。在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