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日,我们在上海举办了第118场一席演讲,以下是本次活动的幕后花絮和精彩片段。2009年我又回到村里待了九个月。那些我在1980年代曾观察过的孩子们都能听懂泰雅博语,其中有几个还说得相当好,我让他们用泰雅博语给我讲故事时,他们能讲出语法正确的、复杂精彩的故事。但是,他们在村子里从来不说这门语言。我问他们为什么不说?他们说,我感到羞耻。一说泰雅博语,一些老人总是会马上跳出来:你说错了,你没学会,不会说。年轻人则反击:我们不会说是因为你们没教过。水獭不单是被科学家或保护团体遗忘了,它是系统性地被所有人都忘掉了。这个其实挺触目惊心的。我们如果在上海的城区里去做貉的保护,你问一个人说,你知道貉吗?他可能说他不知道。但你说一丘之貉,他一下就能联系上了。或者我们去保护豺,虽然大家都不知道豺是什么东西,但你一说豺狼虎豹,对方就能知道。但当你说出水獭的时候,那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没有什么俗语是与它相关的,甚至连一个糟糕的刻板印象都没有。虽然家长们都希望有一个“黄金标准”的教养方式,但我想说,没有放诸四海皆准的方法,只有跟孩子的气质、个性特点相匹配的教养,才是真正合适的。对于趋近型的孩子,一定的约束和管教是需要的;而对于抑制型的孩子,我们需要更多地激发他们的自我意识和内在动力。天性没有好坏之分。如果能在孩子早期成长阶段去了解他们的特点,日后就更有利于我们因材施教。
我在北大荒的作品再美也只是歌颂集体主义的,我想把个人对世界的看法呈现在作品中,这才是真实的我。我从小有个毛病,就是爱说话,多嘴,至今都没有沉默寡言。所以我做了一把壶,也刻了一张木刻,叫“多嘴的家伙”。因为生活告诉我们,多嘴不宜,少说为佳。但是几十年的生活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都闭着嘴,谁为我们说话?很多职校学生面临的困境,是我们这个社会里广大一线劳动者的普遍性困境,那就是劳动待遇比较低,社会保障比较差。最近这些年我们在讨论教育能否改变命运的时候,很多人在讨论上大学是否可以促进个体的阶层流动。但在我看来,改变命运不等同于个体的阶层流动,而是劳动者作为一个群体的权益得到保障。我希望我们的职校同学能够意识到,我今天所付出的劳动,值得有保障的待遇,值得别人的尊敬,我应该是一个有尊严的劳动者。对我而言,《还童》意味着一种回归,真正地回归家庭,回归孩子的身份。这张专辑里有父亲的说书和母亲的绘画,是我们三个一起完成了这些作品,所以它们是关于时间,关于自然,关于成长的。这张唱片的制作过程中,我有很多收获,最重要的就是学会了接纳。接纳完美的父亲,接纳有缺陷的母亲,接纳当下的自己。只有真正接纳此刻的自己,你才能完整地表达当下的你,不然的话会很痛苦。也希望更多朋友可以真正接纳当下的自己,不论他是完美的或者是有缺陷的。当时浙江的一些基层干部并没有严格执行激进的左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默许或支持了民间自发性的地下经济的发展,从而与群众形成了一种互惠的关系。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一些基层干部没有很大动力去执行比较激进的政策。一项政策如果最后被证明是不合时宜的,很多时候是基层干部承担不小的责任。这是因为,政策本身不会在短时间内被否定,问题主要体现为政策的执行出现了差错,这时候执行过激政策的干部就会面临来自群众批评的巨大压力。
我们在调研时发现了很多案例,比如某县曾专门派了一个检查组到一个村子里蹲点查账,发动群众检举过去工作中有问题的干部。但因为这里的干群关系不错,过了一个月,群众并没有积极参与和配合,工作组最后没有查出什么问题,只好撤走了。
“家”字是讲到文字的文化内涵常举的例子,说房子里养一头猪,有财富才是一个家。但是这不合常识啊,不管是把猪养在人的房子里,还是人住在猪圈里,都不合情理。我们看甲骨文、金文,发现“家”字里不是一头普通的猪。商代甲骨文的“豕”字有大嘴巴、大肚子、短尾巴。如果在猪的胯下增加一划,这是公猪,在古代就叫“豭(jiā)”。如果这一划掉下来,是去势公猪(豖zhuó)。商代周代文字中的“家”里是只公猪“豭”,和家庭的“家”同音,当时大概都念/kra/ 。所以“家”是一个很简单的形声字,宝盖头是形旁,那只猪只是用“豭”来表音的声旁,和家庭没有逻辑上的联系。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正在鸡娃的父母?有没有父母觉得最应该“鸡”的就是数学?如果有的话,恭喜大家,你们已经达到了伽利略和笛卡尔的高度了。因为伽利略就说过一句话:自然是一本用数学写成的书。当家长都变成“笛卡尔主义者”的时候,他们与孩子的关系也渐渐变成了经理和职员之间的关系。当我们认为世界的本质是数学公式,那么我们也会认为,任何东西都可以被管理,比如睡眠、时间,甚至情绪也可以被管理。我们正在用“福特主义”养育下一代。那个造车的福特发明了一整套适用于流水线大规模生产的管理模式,但福特主义是不是也适用于“造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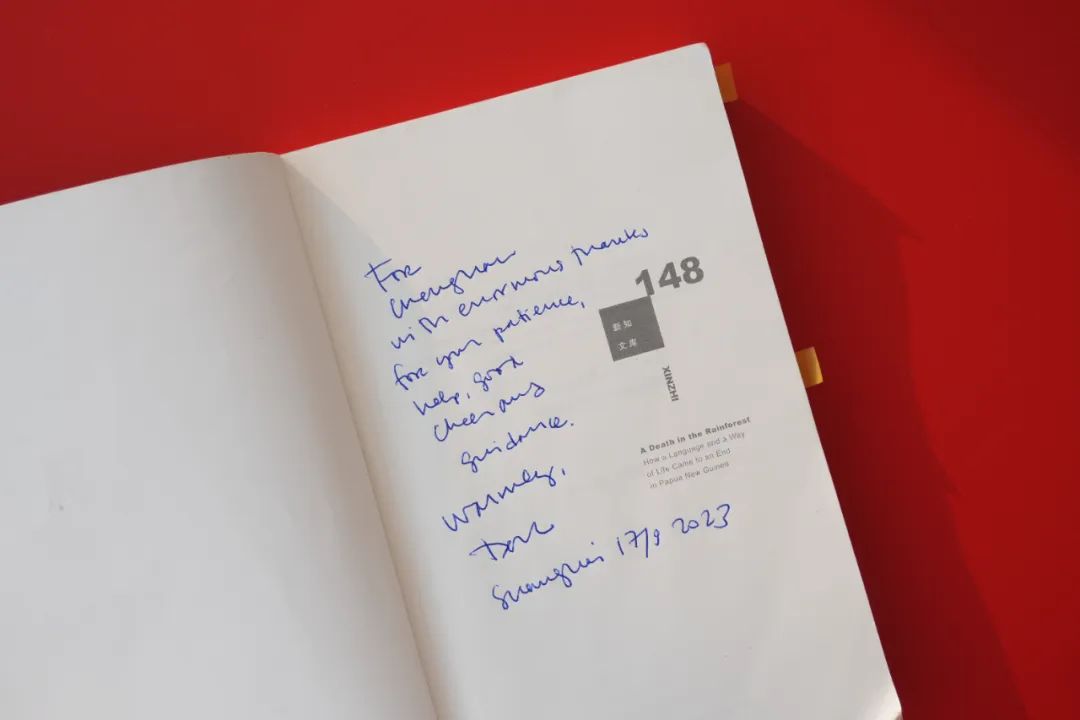








✿✿✿ 一席 x 跳海 ✿✿✿
陈月龙 x 韩雪松 · 与野生动物为邻

▲ 石藤咖啡/摄


▲ 石藤咖啡/摄
场地鸣谢:石藤咖啡、跳海酒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