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历史演绎中,东汉一度被视为西汉末年的翻版。不论是从内部的政治运作,还是从历史节律在两朝留下的足迹看,中国读者熟悉的一直是两汉历史更像是一种自我往复。但事实是否如此?
《洛阳大火》是第一部以西方语言撰写的后汉通史。澳大利亚著名汉学家张磊夫(Rafe de Crespigny)以都城洛阳的命运为切入点,透视了东汉百年的兴衰变迁。在这本书中,他将东汉置于世界史的大视野中,点出了东汉政治现象后更深层次且环环相扣的原因,展示出了有别于传统史学叙事中的东汉的独特性格。

传统中国人的眼里,东汉的形象并不那么伟岸,由于《三国演义》的巨大影响,东汉最家喻户晓的一段历史是它的最后三五十年乱世——东汉正式终结于公元220年汉献帝禅位于曹丕,因此三国故事很大一部分是发生在汉末。除此之外,整个东汉时期几乎没有太多存在感,像一道余晖,又像一抹影子,作为光芒万丈的西汉的漫长尾声,还有三国的激荡岁月之前充满了白噪音的一阕序曲。然而,汉学家张磊夫(Rafe de Crespigny)在《洛阳大火:一部后汉史》开篇第一句话所起的调子却是如此高亢:“公元1-2世纪,欧亚大陆的两端出现了两个可以匹敌的伟大帝国。”作者张磊夫今年已经八十七岁高龄,他戏称自己很可能是“英语世界里唯一一个读过《后汉书》全文两遍的人”。几十年来,西方的中国史研究虽然突飞猛进,但很可惜自鲁惟一、毕汉思、余英时等学者合写的《剑桥中国秦汉史》(1986)后,关于东汉乃至延及三国到魏晋,并没有更完整系统的史学成果(甚至《剑桥中国魏晋南北朝史》仍未撰成),因此2016年,英文版《洛阳大火:一部后汉史》由著名的学术出版机构荷兰·布雷尔学术出版社(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推出时,可说是西方历史学界这几十年来屈指可数的一部东汉断代史。

《洛阳大火》,[澳]张磊夫 著,邹秋筠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3年5月版
张磊夫这本书以政治史为中心,其标题“洛阳大火”,以火之意象与地名洛阳,绾合的是东汉从崛起到衰亡整整196个年头。作为东汉都城的洛阳,可谓与火相始终。光武帝刘秀公元25年称帝后定都于此,改洛阳为雒阳,正是为了呼应汉王朝的火德说,以避免水火不相容。在秦汉四百年主流历史观——五德终始说的支配下,刘邦立国时,原本将汉朝定为水德,尚黑;汉武帝改正朔为土德,崇尚黄。而刘秀延续的是王莽篡汉时的说法,将汉王朝改为火德,尚红(王莽改制对东汉的影响可以说是全方面的,远不止此一端,书中有详细展开),汉朝在后世也便有了“炎汉”之号。书里更戏剧化地描述了东汉衰亡的关节点:189年9月22日晚,何太后之兄、身为摄政的大将军何进当晚被宦官所杀,他的军队冲击南宫宫门,洛阳皇宫惨然的火光照亮了东汉皇权的终结。董卓从城外军营看到火光,率军入城。一年之后的公元190年,董卓胁迫汉献帝刘协、朝臣和百姓西迁长安,一把大火将洛阳彻底烧为灰烬。如今作为东汉首都的洛阳城,位于今河南省洛阳市以东数公里无人烟处,公路和铁路穿过的一座座脊状土堆,那就是城墙遗迹。书中用了整整一章来描写东汉时期的洛阳城,它的布局,它与罗马的对比,以及它的兴废,由此奠定了全书的宏大旋律的苍茫主调。东汉的存续和罗马帝国的“前半生”基本平行。张磊夫看到两个帝国的国运似乎也“纠缠”在一起:罗马帝国有五贤帝时代(“安东尼时代”),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吉本称之为“人类最幸福的时代”,而东汉前三帝(光武帝、明帝和章帝)时期也被后人司马光誉为“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后汉之盛者也”(《资治通鉴》)。

《阿什杜德的瘟疫》,尼古拉·普桑作于1630年,198 x 148 cm,油画,帆布,目前该作品由卢浮宫保管。
巧合的是,两大帝国的衰亡均开始于一场肆虐全世界的超大瘟疫——“安东尼瘟疫”。这场瘟疫暴发于公元165年,造成当时执政的哲学家皇帝马可·奥勒留(《沉思录》作者)染疫而亡,五贤帝时代戛然而止。大疫在罗马帝国持续了十多年,造成七千五百万人口的七百万到八百万人死亡;数年中,瘟疫从西方传到东方,后汉在同期亦频发严重瘟疫,张仲景《伤寒论》便是写于此时,名医华佗也是这一时期人士,可想而知瘟疫对当时中国的冲击有多大——全境估约五千五百万人口中,死于瘟疫者的比例当不小于罗马帝国。安东尼瘟疫导致罗马帝国自此走上由盛转衰的漫漫长路,在东方则引发汉灵帝光和七年(公元184年)黄巾军起义,汉帝国数年后直接土崩瓦解。
把东汉置于世界史的大视野中的做法,应该是受益于张磊夫年轻时在剑桥大学整整三年的欧洲史学术训练,而正式进入东汉三国史研究领域之后,他师从瑞典裔汉学家毕汉思(Hans Bielenstein)。毕汉思著有《汉朝的中兴》(四卷本,分别出版于1953,1959,1967,1979,历时十五年始出版完竣),他作为主撰者之一的《剑桥中国秦汉史》(1986)中对东汉有诸多别开生面的持论。而张磊夫的这部《洛阳大火》很明显看得出来是受到老师毕汉思以及《剑桥中国秦汉史》的深刻影响,是将其分析与观点的进一步推进。
和刘邦尽诛功臣不一样,光武帝优待云台三十二将,以至于东汉的皇后之位一直由阴、窦、邓、梁、马等少数几个开国时立下汗马功劳的大家族所把持,这也带来一个历史奇观:光武帝皇后阴丽华诞下明帝之后,除了末代傀儡皇帝汉献帝,再没有一个东汉皇帝与皇后产下任何子嗣。对此,张磊夫不认为这是政治婚姻导致皇帝刻意回避(毕汉思观点),他举欧洲史为例,“很多国王出于外交考虑不得不迎娶并不喜爱的王后,两人还是会有儿女,有时一次交媾便足以产下孩子”,他进而作出了一个大胆的猜想:“考虑到妊娠并发症和传染病的危险性以及当时的医疗条件,对一位皇后来说,最好的策略可能是让另一位嫔妃怀孕,然后带走孩子自己养育——作为皇帝的正妻,皇后是所有皇子名义上的母亲。”不管东汉皇后无子女的背后真相如何,无论如何这造成了传统历史演义中,东汉的历史很像西汉末年的翻版,乏善可陈,表面上不过是将西汉末年的那些母题反复变奏:中央似乎永远是皇太后、外戚加上刻意挑选的小皇帝,一遍又一遍如走马灯,至多加入了宦官这一股新势力作为皇权一方的新变量。这种阅读东汉的传统方式,中国读者再熟悉不过。两汉真的只是在如此地自我往复?难道中国古代史,真的暗合《三国演义》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一套历史循环论的说法?或者径如清代历史学家赵翼所认为的,光武帝只是西汉皇室的小宗,“譬如数百年老干之上特发一枝,虽极畅茂,而生气已薄”,从而前三帝(光武帝、明帝、章帝)之后,除了末代汉献帝,再没有一个东汉皇帝活过34岁。张磊夫则明确认为当以线性历史观来看待两汉史,东汉的无关乎朝代兴替之“气数”,他在书中专门引用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在《哈佛中国史》中的一句断言:“东汉王朝在很多方面和它的前朝——西汉极少有共同之处。”
《洛阳大火》书中所使用的方法,张磊夫自称为结构主义史学,这与作为西方史学主潮的布罗代尔“年鉴学派”一脉相承,也就是将历史放入政治、地理、经济以及当时特定的危机等因素的“结构”(Structure)中来理解,进行问题导向的全景式叙述。换句话说,点出东汉政治现象后的更深层次环环相扣的原因,正是张磊夫书中的一大特点,我们恰恰可以读出东汉的独特性格。而东汉的历史表象,实际上是由它特有的权力制衡结构所决定的。简而言之,东汉以皇后皇太后为中心的外戚家族,以三公九卿为首的外朝文官系统,以及皇帝与宦官的利益联合体,不能视为东汉政权不稳定、积贫积弱的症候,三者反倒构成了鼎立式的权力制衡体系,这样一个互相制衡的体系防止任何集团独掌大权。再加上光武帝刘秀为减削外朝政府之权力,废除了秦、西汉二朝实行的丞相独自执政制度,改行三公(太尉、司徒、司空)联合执政的办法,又让品秩低下的尚书台和三公实质上形成了两个竞争的内阁,以及东汉呈现出弱中央、强地方的态势,地方豪强大族与中央朝廷的结构关系中,国家权力从都城向地方转移,在这种种情况下,哪怕皇帝无后嗣,或如走马灯般轮流换天子,也不至于像权力过分集中的一人体制那样导致权力真空式的脆断,过于影响政治体系的正常运作。同样,宦官也远不是王朝软弱的象征,用《剑桥中国秦汉史》里的话来说:“当外戚家破坏了这个平衡的时候,皇帝在宪制的意义上就得恢复它,因此,这时宦官就被引进其中了。”对于东汉的这种看似不稳定但实则平稳的权力格局,《剑桥中国秦汉史》对此评价极高,曰:“后汉的制度不仅具有建立在牵制和平衡这一基础上的十分重要的稳定性,还具有适应性和发展的能力。后汉的制度成为当时世界上及后来世纪最引人注目的政府制度。”对比于钱穆在《国史大纲》里的看法,“东汉的立国姿态,可以说常是偏枯的、静的、退守的”“东汉是秦、汉以来统一政府之逐渐堕落”,描述的虽则是同一现象,但是看到的却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洛阳大火》延续的无疑是《剑桥中国秦汉史》的致思进路,在张磊夫看来,东汉的崩溃在根本上也是其“稳定结构”的崩溃,书中这样总结道:“公元189年9月26日对两千多名宦官的屠杀,汉代政治体系中宪制的均势因素才被破坏,它的末代皇帝被野心勃勃的将领们所控制。王朝在余下的时期的特征是一片混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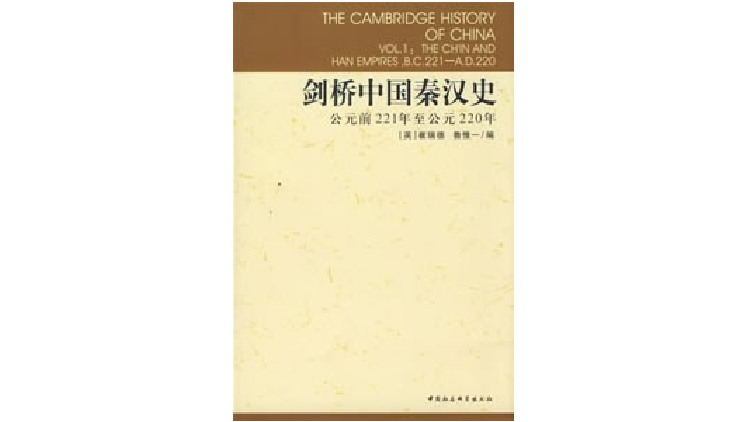
《剑桥中国秦汉史》,[英]崔瑞德 /[英]鲁惟一 著,杨品泉 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年2月版。
按张磊夫的叙述,东汉国力强盛的顶点,当在章帝之子刘肇(和帝)统治时期,和帝“勤勉负责,关爱百姓”,仅以经营西北而论,就有窦宪北伐匈奴,大败北单于,以及班超重建西域都护的武功。不过,此立论明显与传统立场相违。早在东汉末年,学者蔡邕为改变当时烦琐的宗庙体系,便提出自和帝开始的皇帝全不宜称宗,“应毁之”,理由是这些皇帝“功德无殊,而有过差”。蔡邕可以说代表了后世史学的正统立场,比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写道:“及孝和以降,贵戚擅权,嬖幸用事……是非颠倒,可谓乱矣。然犹绵绵不至于亡者,上则有公卿、大夫袁安、杨震、李固、杜乔、陈蕃、李膺之徒面引廷争,用公义以扶其危。”似乎能挽救东汉社稷于既倒者,只有朝堂上的袁安、杨震、李固、杜乔、陈蕃、李膺这些士大夫清流,但历史的吊诡在于,当袁安的四世孙——袁绍背负公卿大夫之重望,劝摄政者、大将军何进对洛阳城里的两千宦官赶尽杀绝之时,便是为董卓开启了入洛擅权的方便之门。从蔡邕、司马光到张磊夫,古今评价之所以会有这种刺眼的反差,原因恐在于和帝一朝,外戚和宦官势力开始浮上台面。在蔡邕等传统士大夫眼中,女性和被阉割的男性是天生没有权力参与国家治理的,“宦官看作一种生性残忍、攫取非法权力的走狗,被排除在社会主流之外”,女性当权者的形象也好不到哪里去,二者合称为“妇寺窃柄”。而且这种精英男权色彩极重的观点越到后世,越是膨胀到无以复加。其实在东汉当下时空中,也许外戚、女主和宦官之治并非一律被视为罪不可恕。毕竟王莽作为外戚,废汉立新朝之初,也算是众望所归;再以蜀地称帝的公孙述为例,他曾梦见“有人语之曰‘八厶子系,十二为期’”,“十二”指的是前汉十二个君主,可瞩目的是其中把并未称帝的吕后也统计了进去。再举一例,曹操之父众所周知是宦官曹嵩的养子。自顺帝时期开始,宦官可以被封爵、被准许有养子,且身死之后养子能够继承财产和爵位,这可以说得到了和外朝的公卿士大夫一样的政治待遇,从曹丕登基后并未还宗夏侯氏,可想而知无论曹操还是曹丕,对于“曹”姓是真心认可,这也反映出当时对宦官的态度远非后世史学家笔下的那种清一色的鄙夷与敌意。《洛阳大火》殊为特异之处,便是抛开传统精英士大夫的自我神话,不再用先天有色眼镜、心存偏见地“看待”东汉权力结构中的外戚、女主和宦官。在书中,和帝的皇后也即后来秉政十五年的邓太后,得到了极高赞誉。对于女性统治者的长处,张磊夫认为在于“相较于真正的统治者而言,她的地位相对弱势,所以不能过于独裁激进,必须小心谨慎地处理与大臣的关系”。在邓太后秉政的十五年里,她从未让邓氏子弟参与朝政,史书中多次出现朝堂辩论,公卿们能够公开表达自己的政策观点。书中如此总结道,“公正地来看,她应该被作为后汉最称职得力的统治者之一被铭记”,而这个结论,恐怕是视天下为“己任”的中国传统精英士大夫阶层所不愿也不能够承认的。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马小悟;编辑:申璐;校对:赵琳。封面图片来自《风起洛阳》(2021)剧照。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点击阅读原文,查看专题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