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田和弘:我是从2005年开始制作“观察映画”的,我的纪录片通常都遵循着相似的方法与风格。我相信观察的力量,观察并不意味着保持距离,或者是以第三方视角,而是要认真地去看、去听、去思考。观察有两个层面,一是作为创作者去观察,并通过你的发现来做影片。另一层面是,我想让观众通过仔细观看和聆听屏幕上的内容,有一个自己的观察。为了达到这两个层面的观察,我提出了观察电影的十个原则(“十诫”)。1. 不对被拍摄对象与题材进行调查。
2. 原则上不与被拍摄对象进行拍摄内容上的事前商议(除了会面地点和时间以外)。
3. 不写脚本。作品的主题和结局不在拍摄前或拍摄中设定。无计划、凭直觉拍摄。
4. 为了在各种情况下都能随机应变,原则上摄影和录音都只由我一人来做。
5. 尽量长时间开机。
6. 进行”精准深入”的拍摄,而不是“多面浅显”。不要为了“多边采访”的构想而进行表面化采访。
7. 剪辑影片时也不事先设定主题。先多次观察拍下来的素材,选择自己最感兴趣的画面,试着按画面构建场景。然后像拼图一样重新排序,疏通脉络,逐渐发现自己的观点和主题。同时,调整剪辑节奏,增加戏剧性。
8. 原则上不使用旁白、说明字幕和音乐,有时这些会妨碍观众的主动观察。
9. 为了能让观众充分地观察影像和声音,镜头的时间尽量剪辑的长一些,着重于观众体验身临其境的临场感。
10. 制作费通常由我们的工作室Laboratory X出,我们不接受有任何附加条件的投资。不干涉作品内容的基金是可以接受的。
杨洋:我想要先引用《这世上的偶然:我为什么要拍纪录片》中文版中的一段话:“总有荒废生命的瞬间,积攒起来瞬间成了时间,时间成了日子,日子成了长久的岁月。然后一转眼,或失去自己珍视的人,或失去自己真爱的故乡,这样的瞬间转瞬而至。也许,我就是想通过电影记忆的方式,留住时时刻刻流失的时间,所以才拍纪录片的。”想田先生,似乎您的好奇心都是源自于根源性的存在主义探寻,这可能和您在大学阶段的宗教专业的学习相关。围绕着“我们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我很好奇对于这一点您最近在思考些什么?想田和弘: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就困惑于“我们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所有的一切都如此短暂,生命转瞬即逝。我想我生下来就是这样的性格,这就是我看待世界的方式。人类是群居动物,通过观察,你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人。只是看着你,是不会让我了解你的。我需要看看你是如何和他人互动的,然后我才慢慢开始了解你。这是我对人,对人的存在的看法,也反映了我的世界观。我不是通过“下定决心”才去观察的,这是“自然而然”的。与此同时,因为世界“转瞬即逝”的本质,让我有想记录它的欲望。每一次,我都觉得那一刻在“溜走”。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欲望,就像每次旅行你都会拍照一样,因为那一刻对你来说很特别,同时你也渴望与你的朋友和家人分享。我的纪录片就是这样的,我也有同样的心态,这就是我做纪录片的原因。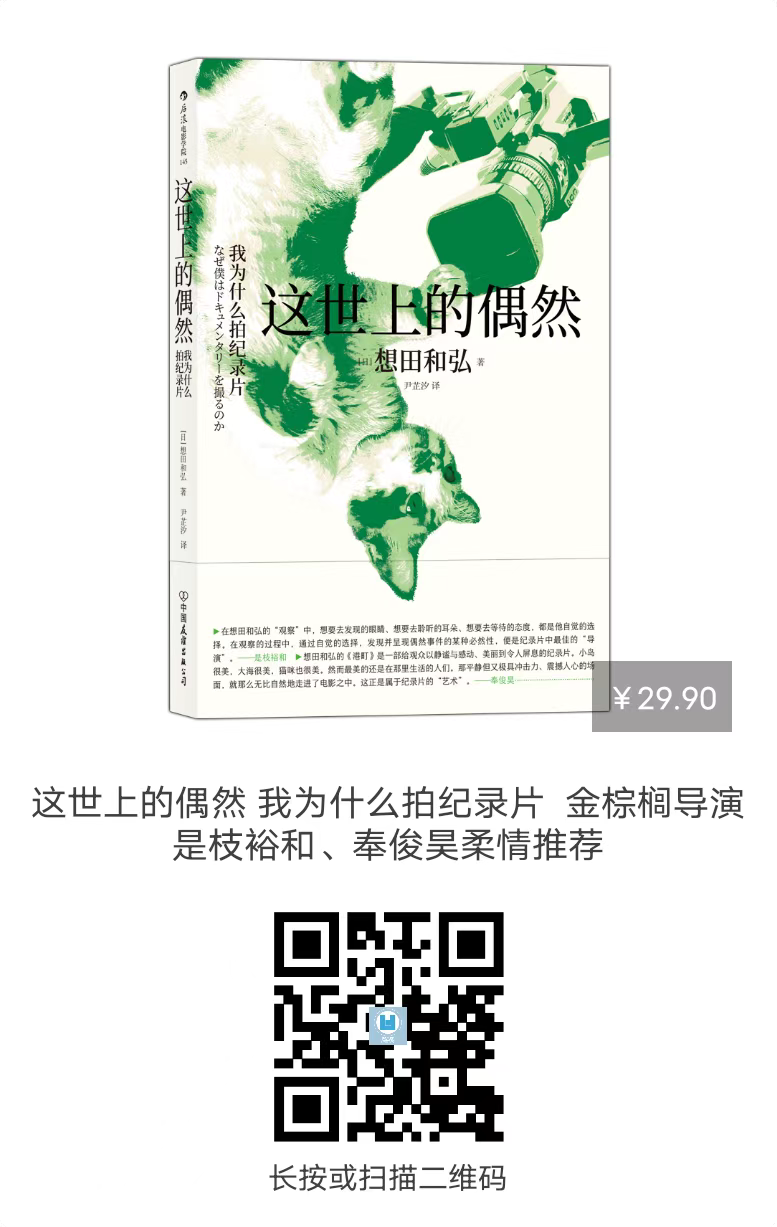
杨洋:观察意味着“面对未知”,我喜欢您在书里提到的观察的反面是“漠视”。您都是一人拍摄的,那么您在拍摄的时候如何确定您的拍摄对象/主题呢?想田和弘:首先,我不想提前预设影片的主题。这是因为我有在电视台制作纪录片的经验。在拍摄电视纪录片时,我必须要有一个主题,比如精神疾病,然后再去做研究。在大的主题下细分出来一些潜在的小点,然后对人物进行初步的采访,找到适合拍摄的内容,并根据采访写一个剧本大纲。当你这样做的时候,这些人就成为了映证你主题的工具。即使你观察到他们快乐的一面,也很可能因此忽略这些内容。所以,一个人可以是任何主题,它可以是我通过观察、倾听和拍摄发现的事情。我颠倒了拍摄电视纪录片的这个过程:让人物成为最重要的,主题是次要的。其次,我不会试图去改变正在发生的事情。我的观察是接受发生的事情,所要做的就是仔细去看去听。这取决于你是否能发现一些有趣的点,如果你认真观察,你将会发现一些趣事。如果你没有找到,很可能是你没有认真地聆听与观察。所以当我觉得有些无聊的时候,我会提醒自己去这么做。当我发现有趣的点时,我会试着把它转换成视听语言,否则我就无法与观众分享,这很重要。比如,当我拍摄某人时注意到她动了动她的手,似乎有些紧张,如果我把镜头放得很远,我就无法向观众传递我的发现,所以我会给手部一个特写。杨洋:您认为这种“参与观察”的方式是否更有创造性?比如在《选举2》中,一些参选者拒绝被拍摄,您在和他们“理论”的时候,您也变成了影片中的一个角色,让那个场景丰富了许多。
△《选举2》海报 ©想田和弘
想田和弘:我之所以说观察不是保持距离,是因为当你拍摄某人时,你的存在不可能不影响你的拍摄主体。所以,你的观察通常是一种参与性观察,这是无法避免的。这与其说是在观察某人,不如说是在观察世界,其中也包括了你自己。我开始拍摄第一部“观察映画”《选举1》的时候,我试着隐藏自己,但是到了制作第二部“观察映画”《精神》的时候,我对观察的想法改变了,我不能“隐形”,我也是那些情景中的一部分。杨洋:您的“观察映画”似乎都关注与捕捉日本社会中的“偶然”。我们知道您在纽约生活了多年,面对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是否给您一些新的创作启发呢?想田和弘:确实很容易产生一些新的观点。如果我一直生活在同一个文化中,一辈子都生活在日本,我看到的一切都会变得非常普通,因为我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你很难对自己所处的文化有一个个人的观点。但是,如果你生活在另一个国家,或者有生活在另一个国家的经历,这就会和你自己本国的文化产生关联,而一切就不再是绝对的了。当你审视自己国家的文化时,你就可以有一个人类学家的视角。这正是我开始拍摄日本所经历的。这是我的国家,我本国的文化,而我认为我的观点受到了我在纽约生活经历的影响。杨洋:有观众提问,在《这世上的偶然》中,您提到剪辑步骤时,先会最大程度保留每个场景的完整性,“完整性”指的是什么?我在自己剪辑的时候,容易陷入“情感完整性”“事件完整性”“现实完整性”等等之间导致犹豫不决,更极端的情况,会觉得无从下手,因为这样感觉是最“完整”的。想田和弘:现实世界很复杂,我渴望将它捕捉成复杂的事物。当我观察自己的时候,有时会觉得自己很善良,有时又觉得自己很刻薄,这都是同一个我。我不想把问题简化,定论一个人是好人或是坏人,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的面貌。我想捕捉的是一个整体,那个人的完整性或是那个情景的完整性。这是一个两难的事情,因为剪辑可以看作是简化事物的过程,拍摄电影不能完全避免简化。但与此同时,你也可以通过拍摄或剪辑不去过度简化,而留下更多可以解读的空间和展示更多面的空间。所以,有时候事情是矛盾的,但我想把这种矛盾的想法放在电影中,因为事物本身就是这个样子的。杨洋:所以这是您对“完整性”的主观理解,在经历现实后形成的?想田和弘:当然,这些都是主观的。没有客观的真理,即使有一个客观的真理,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一点。我们的个人观点都是主观的。同时,我也想要接受新的发现,我想放空我的大脑、我的想法。这样我就能去了解我所看到的,去探索这个世界、人类和其他动物。所以,虽然这是主观的理解,但是我会去努力地打开自己。杨洋:接下来观众想知道,在有了“完整性”之后,进入到剪辑阶段,你会开始寻找“戏剧性”和风格,您确信其中会有这些吗?如果没有,您在剪辑时是如何决策的,如何去除事物的完整性?您认为你的拍摄原则会塑造你后期工作的风格吗?想田和弘:通常拍摄结束后,我会看所有的素材,也会记录所有的内容,写下场景描述。在完成案头工作后,我会一段一段地选取并剪辑我认为最有趣或者最电影化的场景,大概会有六七十场戏,我会随机地把他们放在一起,直到我觉得差不多都剪辑好了。初剪的时候,我的妻子Kiyoko会和我一起看。第一次剪通常都很可怕,我的妻子会看睡着。但这才是剪辑的开始,我会写下这些场景,把他们贴在墙上。然后再进行第二次剪辑,之后我们会再一起看,如何行不通,我会继续这样做,直到满意为止。在这个过程的某个时刻,我会觉得它看起来像一部电影了,这个时候我就会找到影片的主题。当我找到影片的主题时,我会试着调整剪辑,以更突出电影主题,并在细节上做文章。一直都是试错,我不是一开始就知道答案的。在试错中,我总会找到一个答案。想田和弘:我很喜欢猫,所以一出现猫,我就会拍它,也想把它加进我的影片中。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不设定主题的工作。假设我有了一个主题,比如劳工问题,那么当我拍摄《牡蛎工厂》时,我就不得不专注于这个主题,并拍摄一部关于外国劳工的电影。但是我从不预设主题,我的剪辑原则就是加入所有我想加入的内容,所以我把猫加在我的影片中。没有所谓的“猫”的规则,因为它们与主题无关。杨洋:他还有一个问题,在豆瓣平台上他看到有人说《牡蛎工厂》《港町》是您在“一周拍摄的90个小时”素材里剪辑出来的,不知道情况是否属实?但是看两个片子,又会隐约觉得确实是一种非常密集的拍摄。如果属实,对于一周的90个小时素材,相当于每天是13个小时左右的素材,这是否意味着除了睡觉吃饭之外,想田和弘导演是”永不关机“,那么具体落实到拍摄当中,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对于您来说,”永不关机“是一种什么样的拍摄状态?想田和弘:有一点不对。2013年11月那时我还住在纽约,我想在我现在居住的牛窓市( Ushimado)拍摄一部电影,所以我们就在岛上待了三周。第一周我们在牡蛎工厂里拍摄,但是后来工厂里的人厌倦了被相机拍摄,所以我们被赶出来了。我们已经拍到了足够完成一部影片的素材,我原以为我们剩下的时间都是在“度假”,毕竟才过了三周中的一周。然而当我为拍摄《牡蛎工厂》布景时,我偶然遇到了海岸边86岁的渔民村田(waichan),随后就开始了《港町》两周的拍摄。但当时我不确定要拍摄两部电影还是一部电影,我以为我在拍一部影片。我在想怎么能在一部电影里把牡蛎工厂的人和这些老人联系起来。最终,我在三周的时间里拍了90小时的镜头,并制作成《牡蛎工厂》和《港町》两部影片,效率非常高。
△《牡蛎工厂》海报 ©想田和弘
想田和弘:有很多因素。比如,日程安排。当我拍摄《港町》的时候,因为我知道我明天就要走了,所以我就停止了拍摄。我们拍的最后一幕就是那场送别戏,别无选择,只能说再见。所以说要合理安排日程。另一方面,当我拍到一些强烈的场景,即我称之为影片中的核心场景时,我会拍摄一些能够支撑它的素材。例如这场送别的戏,我必须要有一个日落的镜头,或者一个人,一只猫的镜头让它更完整。所以一般你有了核心场景以及更多的支持性镜头或突出这个场景的镜头,我觉得就够了。
△《港町》海报 ©想田和弘
杨洋:听起来似乎您会给自己一些限制,比如日程安排,然后你就会全力以赴,打开所有的感官。以防会错过些什么,您有想过如果您错过了一些内容呢?想田和弘:其实当我决定要在三周内拍摄牡蛎工厂的时候,我一点信心也没有。如果拍了三周后,我觉得素材不够,我是会回去再拍摄的。这种情况有时会发生。比如2005年我拍摄《精神》的时候,我觉得我拍的还不够,所以我们在2007年又回去拍摄了更多。但《牡蛎工厂》拍摄完后,我觉得素材已经够了,所以就没必要回去了。这取决于影片本身,就《和平》而言,最重要的事情都发生在拍摄的最后一天。桥本先生坦白了他的经历,他当兵时打过人。第二天我们就要离开日本了,我们的机票已经订好了。我知道在最后一天我们拍摄了很重要的场景,如果没有这个场景,我可能拍的会是非常不同的一部影片。可能是一部短片,而不是一部长片,这要视情况而定。杨洋:关于道德伦理问题。您是如何看待您和拍摄对象之间的关系?观众想知道您的作品里涉及到许多关于人的障碍,有些是先天的身体障碍,有些是后天的或是精神上的,但导演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健康人,认为自己要把“自我”藏起来,也不打算提供作者的观点。而我以为无论怎么隐藏,怎么克制,拍摄者和被拍摄者的关系都是客观存在,并且能够对影片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请问导演在拍摄的筹备和过程乃至后期的传播过程中,怎么看待自己和被拍摄的关系?会遇到问题吗?想田和弘:这是拍摄纪录片中最难的事情,你拍摄的不是演员扮演的虚拟角色,而是一个真实的人。当你作为一个电影创作者、用镜头聚焦的时候,你对你的角色和角色的形象担负很大的责任。如果你想的话,你可以用一种很可怕的方式描绘一个人。如果你没有道德标准,利用剪辑和相机的力量把某人塑造成一个恶魔,你可能会毁了某人的生活。这真的是纪录片拍摄最难的部分,我试着公平地对待每一个被拍摄者,我努力描绘我眼中的他们,我尽最大可能让他们不会因为我拍摄纪录片而受到伤害。同时,我是否要把一些内容放进影片中也是一个问题。比如婆婆在《港町》中说别的村民的坏话,我不确定是否要把所有片段都加进去,因为这可能会伤害到其他人。事实上,她说了很多,比在影片中看到的更多。我删掉了最尖刻的部分,因为我不想伤害她说的那个人。正如我书中所说,我的目标是捕捉人”柔软“的一面。如果没有,你的纪录片就不会特别有吸引力。但是如果你利用这一点来伤害他,那你就是在摧毁这个人。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很微妙的平衡,它总是最难的。杨洋:很多人好奇您最近在做什么作品?近期您被什么”柔软“的部分吸引了?
想田和弘:我目前正在剪辑两部影片。其中一部是我从五六年前在美国密歇根州拍摄的,我本应该更早完成的,但是项目很难。我遇到了一位在监狱呆了快50年的人,他从16岁入狱,67岁才出狱。在他从监狱被释放后,我有机会跟拍他,在密歇根州底特律。拍摄已经完成了,我还需要剪辑。我正在做的另一部影片拍的是一个非常小的神社,有很多流浪猫。这个地方有很多不同的人因为不同的缘由出入。比如,有些人回来喂这些猫,有些人会给猫拍照,有些人来钓鱼,有人来做园艺。它就像一个社区的缩影,是不同人和不同形态的交汇点。所以,我想观察这个地方。我认为这部影片的主角是猫。想田和弘:我不使用抖音,所以不太了解。世界的趋势越来越像,基本上我们缺乏耐心,我们的注意力持续的时间越来越短,它就像如果你有一个欲望,你满足了,你就会产生更多的欲望。当你试图得到更多的时候,你会上瘾,永远不会满足。现在,即使是新闻,人们也只看标题和评论来做出判断。我有种感觉,我所做的事情与当下潮流相反,我希望我所做的事情,可以成为速度消费的反面,我认为速度不是让我们感到更快乐的必要条件。想田和弘:当我制作我的第一部电影《选举》的时候,我投了二十多个电影节,都被拒绝了,直到柏林电影节邀请了我的影片,随后其他的邀请蜂拥而至。在此之前,我认为只有我自己欣赏这部影片,但是我错了。当然你需要一些运气去找到你的观众,如果你喜欢自己的作品,觉得有趣的时候,别人也会觉得有趣。不是每一个人,但总有人会有同样的感觉。
想田和弘:我的目标一直是对创作保持兴奋。在拍了那么多作品之后,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在重复自己,好像拍电影已经变成了我自己生活作息中的一环,开始变得无聊。我想要尝试打破这种局面,而打破的方式就是要让自己保持清醒,并且要跳出自己的舒适圈,无时无刻地仔细观察和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