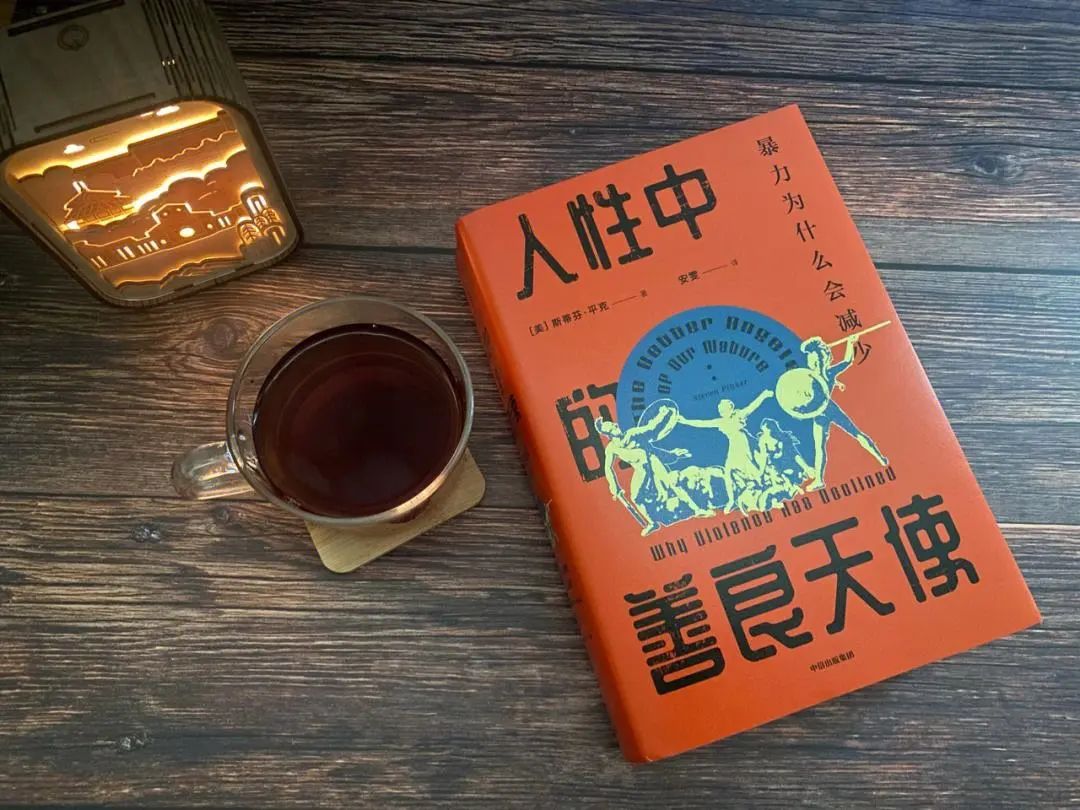
对于毒化人们心灵的意识形态,道德既可以是疾病,也可以是解药。为什么在一个国家正义的事情,在另一个国家看来是违反人权的?道德在塑造社会,社会也在改造道德。这取决于“应该有”的道德和“实际有”的道德之间的较量。
斯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当今西方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入选《时代周刊》当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百人名单,以及《外交政策》的世界百名思想家名单。斯蒂芬·平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引述菲斯克的观点,将人类的道德观分为:社群共享、权威序列、平等互惠、市场定位四个类别,人们可将社会的行为分门别类,放置进这四个类别中,一旦某个行为被错置,大家就会认为这是不道德的行为。如亲子关系,从属于社群共享,但如果有人将亲子贩卖,放置至市场定位中,则是不道德的。洛杉矶加州大学的心理学家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研究发现道德观念大概有四种,这四种道德观念与常见的社会关系是一致的。菲斯克的第一个模型,社群共享,结合了“内群体忠诚”和”贞洁/神圣“。人们在进入“共享”心态的时候,他们在群体内无偿地分享资源,不介意谁付出多少,谁又得到多少。他们将群体视为血肉相连的“一体”,这个共同的实体必须小心保护,不容任何玷污。人们用各种显示连接和亲和的仪式强化这种团体直觉,比如身体接触、聚餐、团体操练、同声唱诗或祈祷、分享感情、同样的身体修饰和纹彩,在哺育、性交类的鲜血仪式中交融体液;此外还有祖先的神话、家族传承、祖辈扎根的领土,或者共同图腾。“共享”是从母性关怀、亲缘选择和互利主义演化而来,它至少有一部分已经通过催产素系统植入人类的大脑。
比如,父母和孩子的社会关系,就是一种明显的公共享有关系。那么,资源共享关系的道德标准就应该是共享的道德标准。例如,你和我应该共同享有这种资源;如果你不遵守共享这种资源的标准,那么你就是不道德的,你就违背了这种关系所要求的行为规范。菲斯克的第二个互动模型——权威序列,是一个由权威、地位、年龄、性别、身材、体力、财产或优先权所定义的线性等级结构。权威序列让上级有权对下级予求予取,接受供奉,要求下级顺服和尽忠,同时也要求上级承担家长式、牧师式或贵族式保护下级的义务。这个模式可以说是从灵长类的等级差序进化而成,很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通过睾酮反应回路嵌入人类的大脑。
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人与人之间有等级差异,比如,老板与员工、老师和学生就是一种等级有序的社会关系,指导这种社会关系的道德标准是尊重和责任。下级应该尊重上级,上级应该对下级负有道义上的责任。违背了这种尊重和责任的道德原则,人的行为就会被认为与这种关系不相匹配。第三种社会关系是平等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社会关系就是普通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指导这种社会关系的道德标准是公平和互惠,“平等互惠”包含着投桃报李式的互惠以及其他公平分配资源的模式,比如轮候、抽签、多予多取、等额分配、儿歌式的口头规则(《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如果一个人为他人做出了服务,而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就违背了这种社会关系的道德标准。比如,我为你洗碗,而你不为我洗衣服,那么这种行为就会被判断为不公正或不合适。当然,如果双方之间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这种道德原则就不一定适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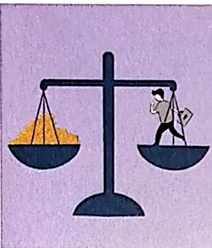
虽然黑猩猩有非常粗糙的公平感,但动物一般都没有能力完成明确的互惠活动,在出现自己要吃亏的情况时尤为如此。“平等互惠”的神经基础是我们的大脑能够记载人们的意图、欺骗、冲突、变换观察角度和计算,它涉及的大脑部位有脑岛、眶额皮层、扣带皮层、背外侧前额叶皮层、顶叶皮层和颞顶交界区。“平等互惠”是人类公平意识和直接经济意识的基础,在知己和战友之外,它让人们以邻居、同事、熟人、贸易伙伴的形式联结在一起。第四种社会关系是市场估价关系。这是在商业社会普遍存在的关系,每个人的劳动和服务都是由市场的价格决定的。比如说,我工作了8个小时,就会得到8个小时的报酬。指导这种社会关系的道德原则是公正和比例,即根据贡献的大小决定报酬的多少。违背了这种道德标准,人的行为就容易被看作是不公平的、贪婪的,或者被认为是剥削。
货币体系、价格、租金、工薪、收益、利息、信用、其他衍生品都是推动现代经济的力量。市场定价依赖数字、数字公式、会计、电子数字传递和规范的合约语言。与其他三个模型不同,“市场定价”依赖文字、数字和其他新近发明的技术,因此它不具备普适性。人们也不是天然地就接受“市场定价“的逻辑。菲斯克表示,四个模型可以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排列的标准或多或少反映出它们在进化、儿童发育和历史进程中出现的时间:社群共享 〉权威序列 〉对等互惠 〉市场定价。“社群共享”模型的思维标量是“全或无”,或者说“非此即彼”(即所谓的“名目尺度”):一个人或者属于神圣家族,或者不属于。于此相应的认知方式是生物学直觉思维,着眼于生物性的纯洁本质和潜在的污染源。“权威序列”使用顺序尺度:对统治与被统治阶层进行线性排序。它的认知手段是对空间、力和时间的物理学直觉:人的排序越高,他的形象就越大,力量越强,地位越高,越具有优先权。“对等互惠”采取等距尺度,两个量之间可以比较大小,但是不存在比例关系。具体的量度方法如排序、记数,或者以相同的单位进行比较。只有“市场定价”(以及市场定价所属的法理型思维)能够用“比例性”尺度进行量度和运算。法理型模型要求非直觉性的符号数字做推理工具,比如分数、百分比、幂。我已经说过,法理型模型在人类历史上远非常见的道德规范,它要求人们具有高级的认知能力——熟练把握文字和数字的能力。菲斯克的发现主要是证明,除了传统法律认识做出的道德判断以外,还有根据人类相互关系类型的道德判断,而且这种判断有很大的跨文化相似性。在很多文化中这四种道德判断都存在,当然不排除有些文化缺乏其中一类或者几类社会关系的情况。即使在家庭关系中,在不同情况下,也会有这四种社会关系的表现。比如,父母与孩子可能是资源共享的关系,但是也有权威等级的关系,因为父母的权利一般是大于子女的。作为普通人,父母与孩子是一种平等的社会关系。但在个别情况下,父母也可能使用市场估价关系来对待孩子,例如父母让孩子打扫卫生,然后付给孩子一定的报酬。互动模型中的社会角色和资源的配置也可以说明一个社会的政治意识形态。法西斯主义、封建主义、神权和其他原始性的意识形态的基础都是”社群共享“和”权威序列“互动模型。个人利益完全被淹没在社群中,而社群受军队,贵族或神职集团的统治。民粹社会主义追求生活的必需品,如土地、医疗、教育和托儿等资源的“对等互利”。而在相反的极端,自由意志则允许人们在“市场定价”的原则下对几乎所有资源协商议价,包括人体器官、婴儿、医疗、性和教育。
对四种关系的行为判断,可以由这四种道德判断来进行。道德观念对人的影响到底有哪些行为差异呢?最早做出跨文化实验研究的是心理学家米勒(Miller,1984)。米勒对印度人和美国人的道德判断做了一系列分析,发现美国人较多使用法律公平的标准来进行道德判断;而印度人倾向于使用关系义务的标准。她特别设计了另外一些道德两难的困境,在这些困境中,人的行为可以同时用法律公平的标准和关系义务的标准来进行衡量。其中一个道德两难困境的例子是这样的:阿本在洛杉矶出差,办完事后,他必须赶到旧金山去参加好朋友的婚礼。因为他是伴郎,必须亲手把戒指交给新郎,然后由新郎交给新娘。可是不巧的是,当他赶到火车站时,他突然发现自己的钱包丢了,在钱包里有一张去旧金山的火车票。这时,只剩下最后一趟去旧金山的火车,他必须赶上这趟火车。可由于阿本是外地人,没有人愿意借钱给他。正在他百般无奈的时候,他发现座位旁边有一件衬衣,衬衣的口袋里刚好有一张去旧金山的火车票。阿本该不该偷这张票呢?
米勒认为,对这个问题的道德判断有两种。一种是坚持法律公平标准的道德判断。也就是说,阿本不应该偷火车票,因为偷东西违反了法律和社会的道德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对朋友的承诺没有对社会的承诺重要。另外一种是建立在关系义务基础上的道德观念。这种观念认为,阿本应该偷这张票,因为如果不偷票,他就不能够履行自己对朋友的承诺。由于戒指不能交给朋友,新郎就会在没有戒指的情况下与新娘结婚,这有可能影响朋友的夫妻关系。米勒在印度和美国分别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发现了不同的文化差异。在印度,有90%的三年级学生认为阿本应该偷票,因为他对朋友的承诺非常重要;有80%的七年级学生认为阿本应该偷票;甚至将近80%的印度成年人认为阿本应该偷票。可是,在美国,不同年龄段认为阿本应该偷票的人数比例都远低于40%,而且年龄的增长与赞同偷票的人数成反比的关系,年龄越大的人,越认为阿本不应该偷票。这就是一个很鲜明的道德观念的文化差异的表现例子。美国人的道德观念强调法律的重要性,而印度人的道德观念建立在关系义务的基础上,传统的法律责任比没有关系义务的道德更为重要。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中国人甚至东亚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能更接近于印度被试的回答,因为我们都属于团体主义文化的社会,而且对人际关系的责任和重要性非常重视。中国古代就一直强调“三纲五常”,其根本含义就是强调社会关系的道德判断标准。在君臣关系上,君主的意识就是道德判断的标准;在父子关系上,父母的意志就是儿童行为的基本规范;在夫妻关系上,丈夫的意志就是妻子的义务。菲斯克说,人类之间的互动不是必须使用任何模型,他称不服从互动模型的状态为无效人际关系或反社会人际关系。不从属任何互动模型的人会被非人化:他们被视为缺乏人性的某些基本属性,被当作没有生命的物体,可以任意被忽视、被剥削或者被捕食。因此,反社会关系可以被征服、强奸、刺杀、杀婴、战略轰炸、殖民掠夺和其他犯罪铺垫基础。既然道德观念的文化差异有这么大的区别,那我们如何进行跨文化的道德判断呢?什么样的外生原因让道德直觉离开社群、权威和圣洁,而趋向公平、自治和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