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谈AI时代的工作:意义的危机与不工作的神性
撰文 | 胡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信息社会50人论坛成员
责编 | 齐卿
作为一个老师,我的学生分两类:一类是未毕业的学生,一类是已毕业的学生。两类学生都很焦虑:未毕业的学生,担心自己找不到理想的、有意义的工作;已毕业的学生,问老师最多的一个问题是:我现在做的这份工作有什么意义?如何对抗或者说消解工作中不时来袭的无意义感和对工作内容的抵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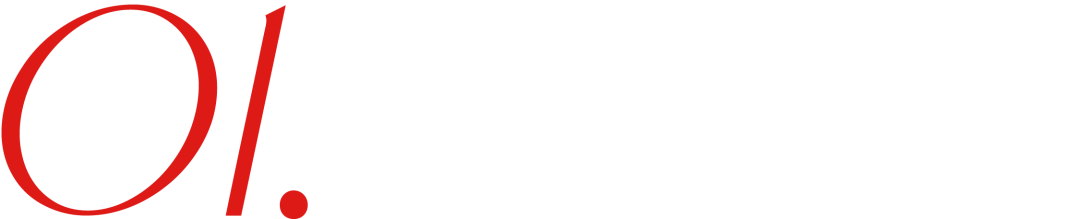 意义的危机
意义的危机
说到意义的危机与重建,我想先从我们生活意义的一种结构性的荒谬来讲起。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不同的学科当中一直有一种看法,把人类看作是一种符号化、概念化、寻求意义的动物。在过去的几年内,这种看法在社会科学和哲学当中都变得越来越流行,因为我们人类努力从经验当中来获得意义,并且通过获取意义的过程来给我们周边的世界赋予某种形式和秩序。这种努力越来越像是我们所熟悉的一种生物学的需要,这个看上去有点高端的需要,其实对每个人来讲是真实而又迫切的。
然而问题在于说,常常会出现的一种情况是,我们越是努力从经验中获得意义,反而越容易堕入一种空虚的深渊。
比如讲,为了实现在个人生活和事业上的成功,一个成年人可能会花费数十年的光阴,但是在最后实现了很多东西以后,他反而可能会感到其中的空虚,这种情况我们司空见惯。人类面临这样的一种困境,其实也不是从今天才开始。
叔本华对此有一个解释,他认为我们的生活当中存在某种结构性的荒谬。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当中叔本华写道:“一切意志的基础都是需要和匮乏,因此它就是痛苦。”所以从生命的本质和起源来看,一切生命注定都是痛苦的。反过来讲,如果欲望太容易满足,意志的目标马上就会丧失。由于缺少目标,这个时候可怕的空虚和无聊就会趁虚而入。
因此叔本华打了一个比喻,他说如此一来,生命就像是一只钟摆,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来回摆荡,事实上这两者都是生命的终极组成部分,这就是叔本华为我们描述的困境:你的意志,要么有目标,要么就没有。如果你什么也不想要,你就是漫无目的的,这个时候就可以把你的生命定义为空虚,这就是我刚才讲到的那种无聊的深渊。但如果你确有所求,你所求的东西一定是某种未经满足的欲望、尚未实现的目标或计划,但这样的东西也是致命的,因为你想要的东西自己现在尚未拥有,对于你来讲,这构成一个巨大的痛苦。然而如果你想去获得这种你尚未拥有的东西,这个过程又是极其艰辛的。
更致命的地方在于说,一旦你真得到自己想要的,也就是说你的欲望得到了满足以后,你本来应该是感到幸福,感到高兴。但恰恰相反,在你的目标实现的一刹那,你发现此刻的自己漫无目标,情绪低落,因为你的追逐结束了,现在你无事可做。所以如果我们按照叔本华的理路来认识,就会发现,其实核心的问题根本不在于你的欲望常常得不到满足,而在于说,你处于一种永恒的困境当中,就是你哪怕满足了欲望,还是逃不脱这个困境。
叔本华当年在柏林的时候,企图跟黑格尔唱对台戏,甚至有一种说法说他有意把他自己的课安排在黑格尔讲课的时段,但我们知道叔本华最后惨败,因为按照他的这套理论,他肯定不是一个激励人心的演讲者。相反地,如果你有幸坐在他的课堂上,你会发现他所描绘的人生路径极其黯淡,因为一个失去目标的人生的确是空虚的,甚至都不可以算作人生。
人工智能导致工作的终结
让我用这个出发点来思考,你的人生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你有目标,但是我们需要对目标来做一个分界,因为有些目标是具有终结性的,有些是没有终结性的。举例来讲,如果我们从日常生活当中的常见活动来看待这个目标问题,比如说你求职,或是你成功求职了以后,需要时常写工作报告;你下班开车回家,或者你散步、听音乐等等,这里面有些目标是终结性的,比如开车回家这事是终结性的,你到家以后它就完成了。结婚这样的事情,或者是写作这样的计划,都是可以做完的事情。
终结性活动的目标就是实现某种终结状态,在这个状态下某些事情被完成,然后这些事情就消亡了,但同时也存在其他的非终结性的活动,此类活动我们视之为,目的并不在于抵达事物终局的那一点上,不在于追求事物实现的最终状态。比如说散步这事儿,没啥目的,听音乐也没有什么目的。读书和思考,严格地来讲也没有什么目的,排除那些纯粹是为了某些功利的原因来读书的人。理解他人没有终局,建立亲密关系没有终局,这些活动都是非终结性的。所谓非终结性并不是说这些活动就不完结,你随时随地可以把它们停下来,而且鉴于你人生的有限性,你一定会在一定时刻停止去做这些事情。然而你停止去做的时候,并不等于完成了这些事,你永远无法完成它们,它们是没有界限的,也是没有结果的,因此它们是无法衰竭的,也永远抵达不了终点。
做了这样的一个分析以后,我们会发现说大部分人的人生基本上是被计划好的,或者为了实现某个目标精疲力竭,执着于把事情做完,凡是这种情况下你所从事的活动都叫做终结性活动。如果你的人生的意义的来源当中有太多的终结性活动,其实你时时刻刻仿佛是在为摧毁自己生命中的意义而战,除非你的计划多到无法全部实现,或者你一直坚持去找到更多的意义,不然你就是一个没有救的人,这是叔本华的洞见。如果你聚焦于终结性的活动,你的努力实际上就是在和自己作对。因为你花费光阴,其实是为了把那些为光阴赋予意义的活动一件一件地完结掉。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免计划驱动人生这样的一种活法。
假如你过的是这种人生,你会遭受一场漫长的慢性折磨,它隐藏在各种各样的事物的漩涡当中。比如我本人是个老师,以老师为例,我永远会有越来越多的需要完成的课题、等待组织的会议、希望完成的论文和计划阅读的书,还有带不完的学生,对不对?这是一个老师的职业生涯。在过这样的一种人生的时候,你当然不能够在散步或者是跟朋友共度的时光当中获得乐趣。虽说你在完成你的计划的时候,也不是一无所成,但问题在于你的人生意义诸多根源的大部分还是终结性活动,其实你是在被一种终结性的思维所左右。这个可以解释说,为何你在得到了你想要的东西以后,仍然会感到空虚,感到重复,感到徒劳无功。所以日常人的工作就这个样子,我只是以老师为例来说明这事而已,你当然可以从事各种各样不同的工作,但结局并没有什么两样。
这种慢性折磨,导致痛苦成为我们时代的最大现实,然而又很少是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索尔·贝娄说:“现代生活,如果你太过在意的话,会令你心神交瘁。”
既然各种工作都摆脱不了叔本华的钟摆铁律,我们不妨展望一下工作的未来,或者我也可以直截了当地叫做工作的终结。这首先是因为,我们的绝大部分工作,都是我上面所讲的终结性活动,它们不仅越来越少意义,反而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无意义;有的时候可能你工作得越多,你的无意义感会愈加强烈。
其次,可见的现实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工作带来巨大的威胁。在人工智能步步紧逼的情况下,我们这个时代的工作,正在见证一场社会、经济和政治层面的危机。这样的危机体现为很多的层面,比如说一个很大的层面是过劳,很多人极其疲惫地在工作,工作永远做不完;但在另外一个极端上,很多人将要找不到工作了。所以说,一个显而易见的表象是过劳,另一个表象则是工作岗位的日益稀缺。纵观整个劳动力市场,包括制造业(由机器组装的汽车和计算机)、零售业(完全由计算机操纵的商店)以及运输业(无人驾驶的汽车和火车),都在渐渐趋向或经历着最终的全面自动化。人工智能将接手许多曾被认为不可化约的工作,从市场营销到投资银行,从准备法律合同到教授数学,就连“较高层次”的认知和智力工作也不能幸免。
这就会造成劳动力市场的一个极大的萎缩,最终劳动力市场的萎缩对有工作的人和没工作的人而言,影响相差无几。就业竞争压低了工资,同时对人们的工作效率和奉献精神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一大批前途不可限量的员工时刻整装待发,一旦我们出现闪失,他们就会取代上位。这将加大我们的工作压力,切断我们的退路,让我们产生一种听天由命、万念俱灰和身陷囹圄的感觉。我们之中的许多人拼尽全力维持着体面的生活,或是仅仅想要生存,却发现自己被困在充满压力、没有成就感的工作之中,疲于奔命。这也就是“内卷”或者“躺平”成为中国社会流行语的内在原因。
呼唤后工作时代
这种迫在眉睫的危机呼唤一种针对“后工作”(post work)时代的新思想,它需要一群思想者来思考,如果我们来到一个后工作时代,如果未来世界当中的确没有工作,它会造成什么样的一种经济、政治和社会后果?
全民基本收入,即政府为每位公民提供的一笔收入,旨在保证公民维持基本生活,无须接受经济状况调查,这一概念正在激进社会政策圈子里得到热捧,并已然成为“后工作”政策和相关讨论的核心支柱。比如华裔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杨安泽提出的“自由红利”,是所有美国成年人的普遍基本收入,没有任何附加条件,是一套每月1000美元或每年12000美元的保证付款,支付给所有18岁以上的美国公民。
OpenAI的CEO山姆·阿尔特曼也持这种观点,早在ChatGPT问世之前,他在谈论“万物摩尔定律”(Moore's Law for Everything)的时候,就提出可以建立一个美国股票基金,每年对超过一定价值的公司征收其市场价值的2.5%的税,以转移到基金的股票支付,并按照所有私人持有的土地价值的2.5%征税,以美元支付。所有18岁以上的公民每年都会得到一笔美元和公司股票的分配,存入他们的账户。人们可以以自己需要或想要的方式使用这些钱——更好的教育、医疗保健、住房、创办公司等等。
然而,正如许多“后工作”思想者所言,“后工作”的未来世界向我们抛出了一个问题,它既是政治的、务实的,也关乎人类生活的意义。在下一个世界中,工作场所不再是迫使我们追问生命意义所在的中央世界。如果不工作,什么能让生活有意义?如果工作不是我们天生具备的根本属性,那么我们又是什么样的人?
我会和此前的许多思想者一样,把救赎的希望寄托在艺术上。艺术家生活在想象的世界,而不是现实的世界里,要将我们的目光从真实转向虚构和幻想。他们很少采取具体的行动,这使得他们成为那些追求美德和诚实之人不断质疑的对象。在《理想国》中,出于各种原因,柏拉图让苏格拉底将艺术家驱逐出理想城邦,其中最重要的是,艺术家不仅对正确的生活和行为方式没有任何贡献,也没有告诉我们它们是什么。苏格拉底哀叹,即使是所有诗人中最受爱戴和尊敬的荷马,也没能制定出一部宪法、发动过一场大获全胜的战争、推行一种切实可行的策略,或者致力于公共服务。艺术家也许有令人无法抗拒的娱乐精神,但作为生活向导,他们却一无是处。
大约2300年后,奥斯卡·王尔德颠覆了柏拉图的价值体系,将这种“无用”提升为艺术家的最高美德。艺术家的所有价值就在于要去抵御那种控制着其他所有人的积极冲动,因此艺术家得以摆脱现实的局限性,找到一种通往无忧无虑的梦想生活的路径,这一路径是什么?说穿了就是不以做什么为目的,只为了存在而生活。
尽管苏格拉底和王尔德持相反立场,他们有个观点却如出一辙:他们相信艺术的创造和享受,本质上表达了艺术家对于生活目标的一种婉拒。我说婉拒是比较温柔的,甚至可能就是一种直截了当的拒绝,因为艺术作品得以存在的基本事实,其实就是指向人性当中一种不必要的、甚至是无用的维度,一种对有目的行动的抵制。我们在读诗、在阅读小说或者看画和听音乐的时候,很难寻获任何切身的实用效果。它并不作用在功利主义的维度上。
但是你会问,该如何解释以下现象,就是艺术领域很多时候是有利可图的?在文学领域,也存在一个市场叫做畅销书市场。无论是文学和艺术,都可能是十分赚钱的,也常常出于各种目的为人所用,就连最新的NFT也是如此,所以,艺术从来就是我们的生活和世俗现实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与现实分离的世外桃源。这无疑可以解释为什么如今的艺术需要不断从商业价值或社会效用的层面来证明其使用公共资源(金钱、空间、时间)的合理性。艺术必须在经济或社会上有利可图。
我们当然可以拿艺术品做各种各样的事,表述林林总总的故事,但人们对此仍然心怀隐忧,因为一件艺术品之所以成为艺术品,就在于它是“不被使用”的,无关他人的行动。正如法国作家、评论家莫里斯·布朗肖所说,“艺术的行动力贫瘠且微弱……一旦艺术以行动来衡量自己,这种刻不容缓的行动只能把它置于谬误的境地”。
如果我们不以行动来衡量艺术,而是把艺术当作生活中一个不适合这种度量标准的领域,那将会如何呢?在一篇颇具煽动性的文章中,布朗肖认为,浪漫派艺术家自诩为神圣的“创造者”,让自己取代古代诸神的地位,却因此失去了所有神迹中最神圣的一种:在几乎所有关于世界起源的神话,尤其是在《创世记》的叙事中,神明不仅会创造,还会休息。浪漫派艺术家误以为自己的神性在于“劳动创作”,其实这是“最不神圣的神迹,让上帝成了每周工作六天的劳工”。
真正的神性不在于工作,而在于不工作。任何人都能工作,但不工作是上帝的特权。艺术家和上帝一样,也不是“劳动者”。建筑师用石头砌墙、架桥或建造日常生活中其他有用的东西,而雕刻家只用石头将想象世界中的东西变成现实。无论艺术家看起来多么努力,其作品都没有什么真正的用途和功能。那些自称纳税人,却将艺术家视为懒虫或废物的人也证明了同样的观点——这个世界并不像需要泥瓦匠或医生那样“需要”艺术家。
所以,哪怕我们不是艺术家,我们可否在我们的生活中迎回这种神圣的懒散并加以效仿?这种懒散从当代生活中消失,可能既与工作的神化有关,也与社会的世俗化有关。我们太着急做各种事情,进行各式选择,忘记了应该懒散,应该无聊,应该无所事事,应该待着,而不行动。是否存在一些无意义的东西,反而构成有意义的存在?
微信扫码关注该文公众号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