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白中林
来源:《历史评论》2022年第6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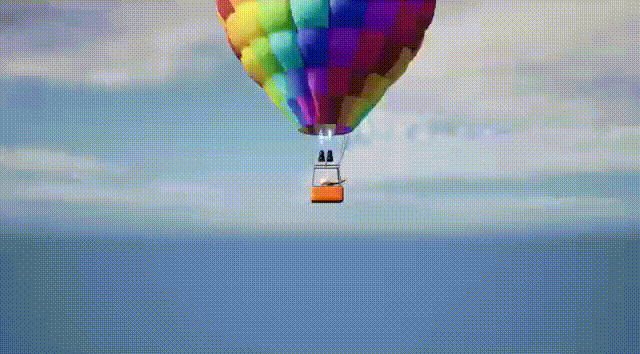

“社会史观”虽然表现出与唯物史观的亲缘性,却并非真正的唯物史观,原因在于“社会史观”未能摆脱思想深处的唯心论因素。
陶希圣虽然在理论形式上采用唯物史观的部分观点来分析历史,但在实际运用中,并没有做到将唯物史观贯彻始终,也没有做到实事求是,最终造成对唯物史观的曲解。20世纪上半叶,受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史论战刺激,社会经济史研究蔚然兴起。以陶希圣为代表的食货学派,强调立足于中国史料本身,对推进中国经济史研究作出贡献。同时,这一学派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社会史观”,表现出一定的理论自觉,在近代中国形形色色的史学思潮中颇有辨识度。不过,如何评价食货学派,以及如何分析“社会史观”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异同,至今仍是众说纷纭的难题。实际上,“社会史观”虽然表现出与唯物史观的亲缘性,却并非真正的唯物史观,原因在于“社会史观”未能摆脱思想深处的唯心论因素。
1934年,在陶希圣、顾颉刚等人的倡导下,《食货》半月刊创刊发行。直到1937年因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停刊为止,《食货》共出版61期,成为食货学派的主要阵地。《食货》主要发表社会经济史、生活史的学术论文,大多短小精悍,不乏具有相当水准的佳作,对提升食货学派的学术影响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食货学派最大的特点是,既坚持“详细的搜求材料,慎重的发言 ”,又要求“加以经济理论的陶冶,历史哲学的引导”,兼顾理论方法与史料功夫。就重视社会经济史资料、关注基层社会经济变迁而言,食货学派在很大程度上实践了梁启超等新史学先驱所呼吁的“眼光向下”的“民史”研究,在经济史资料搜集与著作撰写方面收获颇丰。陶希圣后学全汉昇、杨联陞等人的研究成果,更使食货学派影响力扩大到海外汉学界,流风余韵至今不替。
事实上,早在食货学派形成之初,它相对于西方汉学的比较优势便已凸显。西方汉学对中国历史的研究突出语言学传统,而食货学派将解释中国史的切入口转向社会经济领域,运用马克思、桑巴特等人的理论解释历史变迁的社会经济动力,不仅超越了西方汉学的语言中心导向,研究内容也大大丰富。在史料选择方面,《食货》打破西方汉学和早期中国新史学倚赖新史料的习惯,主张充分利用二十四史等基础史料与地方志、档案、账簿等常见文书,从中发现新问题,有助于纠正新史学思潮过度轻视历代正史和传世文献等“旧”史料的倾向。就对理论方法的重视而言,食货学派也与民国时代主导学界潮流、标榜“史学就是史料学”、“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实证主义考据学派拉开了距离。1929年,陶希圣在《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一书中明确指出观察中国社会应取三个观点。一是历史的观点,“中国社会不是静的,不是自然型成的;是动的,是几千年历史运动所造的”。二是社会的观点,中国社会构造与政治组织不是由个别大人物创造;相反,“大人物之所以大,是由于他所绾领所代表的社会势力之大”。三是唯物的观点,中国历史不是心或观念的发展,而是“地理,人种,及生产技术与自然材料所造成的”。三种基本观点都没有沉溺于具体的史料考辨,而是尝试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和规律,并从历史中寻找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解决之道。对此,陶希圣将其概括为“社会史观”,它构成了食货学派史学思想的核心。
从陶希圣的表述看,他用来解读中国史的三大观点,与唯物史观强调的以变化的眼光看问题、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以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等基本论断十分相近。《中国封建社会史》一书用商品、货币、交换、地租、资本等范畴建立中国历史分析模型,也基本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模版。在该书绪论结尾处,陶希圣写道:“本书的用意在提出历史的事实,供读者尤其是历史唯物论者的讨论和批评。”1932年,在《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一文中,陶希圣又表达了“把唯物史观的中国史在学术界打下一个强固的根基”的愿望。凡此种种,无异于以唯物论者自命。一些学者也正是据此将“社会史观”认作唯物史观。郭湛波说:“中国近日用新的科学方法——唯物史观,来研究中国社会史,成绩最著,影响最大,就算陶希圣先生了。”曾为食货学派成员的何兹全也说:“主编《食货》半月刊和在北京大学教书时代的陶希圣,他的历史理论和方法正是辩证唯物史观。使陶希圣高明超出他的同辈史学家的正是他的辩证唯物史观。”
但是,与唯物史观强调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不同,陶希圣虽然也将“生产技术”纳入唯物观点之中,但在分析具体问题时,更强调民族、群体身份等因素的意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重要性被淡化,陶希圣的“社会史观”自然倾向于否定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突出作用,转而强调社会的总体结构,阶级仅仅是历史的一个基本但非中心的面向。因此陶希圣从“社会史观”出发观察中国历史所得出的结论,必然与唯物史观的经典论述存在差异。譬如1928年,陶希圣在《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一文中便认为,封建制度在战国时代即已崩溃,中国从那时起便进入了商业资本主义,其统治阶级并非地主,而是兼具“地主与资本家”性质的“士大夫阶级”。这种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判断,片面将小农经济条件下零散自发的剩余产品交换夸大为“商业资本”,既不合乎历史实际,也模糊了现实社会中反封建的斗争焦点。
在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中,已经有人对陶希圣的观点提出质疑。张横《评陶希圣的历史方法论》一文便敏锐指出,陶希圣的“社会史观”存在两大问题。其一,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因为它建基于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商业资本固然破坏自然经济,打击封建制度,但在本质上并不足以完全摧毁封建制度。陶希圣未能把握这一点,一面承认地主阶级仍是中国社会的支配势力,一面又说商人资本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自相矛盾。其二,陶希圣所谓“士大夫阶级”,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各阶级的利益代表。张横强调,阶级与社会生产具有直接关系,世上没有超阶级的个人,社会的客观条件使士大夫始终依附于封建地主贵族,成为他们的代言人。陶希圣的“唯物论”不是真正的唯物论,它已经沦为诡辩主义、唯心论的傀儡。
张横的这些批评显然切中陶希圣痛处。陶希圣虽然在理论形式上采用唯物史观的部分观点来分析历史,但在实际运用中,并没有做到将唯物史观贯彻始终,也没有做到实事求是,最终造成对唯物史观的曲解。这种现象的成因是复杂的,除了陶希圣“所代表的派别底社会背景……使他不能彻底的站在唯物论的立场”(张横语)这一现实因素外,他自身思想的唯心主义倾向也是重要原因。陶希圣在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中反复提及唯物论,但他晚年对“社会史观”的自我总结,或许更能代表其思想的真实底色。他说:“我的思想方法,接近唯物史观,却并不是唯物史观。与其说我重视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毋宁说我欣赏考茨基的著作。例如考茨基的《基督教的基础》,就是我用心读过的一本书。然而我的思想方法仍不拘限于此。我用的是社会的历史的方法,简言之即社会史观。如桑巴德的《资本主义史》和奥本海马的《国家论》,才真正影响我的思路。”1979 年,陶希圣将《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一书修订后再版,其中的唯物论观点,被修正为生活的观点,或心物合一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历史是地理、人种及生产技术与自然材料所造成,也是观念的发展和思想的结晶”。“接近唯物史观,却并不是唯物史观”的自我评价,概括了“社会史观”的实际立场。
在陶希圣的自述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唯物史观对“社会史观”的影响。在社会史论战中,虽然陶希圣受到过唯物史观熏陶,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接触,并不是直接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典,而更多是靠阅读马克思主义影响下的史学著作(如考茨基《基督教的基础》)。在这类史学著作影响下,“社会史观”“接近唯物史观”,自然不令人意外。
但为什么“社会史观”终究“不是唯物史观”?这就需要注意陶希圣提到的桑巴特《资本主义史》和奥本海默《国家论》这两本书。桑巴特虽然受到马克思影响,并从经济原则、技术、组织三者的关系展开对资本主义史的分析,但居于核心地位的仍是经济主体的经济意识所落实的经济原则。从桑巴特这里,陶希圣既吸收了经济史观,也吸收了以精神为支配者的观念论倾向。奥本海默《国家论》也不排斥辩证法和经济史视角,但其根本观点是把国家理解为“武力造成的团体”,认为国家是人类依政治手段造成的一切关系之总和,其驱动力则是意志与生存欲望。陶希圣不仅取法奥本海默的意志论,而且从他的国家定义获得了构建超阶级的“士大夫阶级”概念的灵感。
至此,陶希圣“社会史观”的来源大体上已经清楚了。“历史”、“社会”、“唯物”三大观点,在桑巴特和奥本海默提供的理论框架之下都可以兼容,却并不通向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在桑巴特那里起支配作用的是精神,在奥本海默那里则是意志,陶希圣以此为关键来绾合三大观点,其历史载体则是“社会史观”突出强调的“士大夫阶级”。“社会史观”正是在这里与唯物史观分道扬镳,它带有强烈的意志论色彩,因此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并尝试运用过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却常常在具体历史判断上偏离唯物史观。陶希圣晚年将唯物论观点改成心物并重的二元论观点,实际上流入唯心主义,可以说是其意志论倾向导致的必然结果。
食货学派的“社会史观”一定程度上包含与唯物史观共通的思想因素,但本质上仍以意志论为底色,最终走向了对唯物史观的扭曲,可以说是一种“伪装的唯物史观”。不过,食货学派在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仍留下不少具有学术价值的成果。作为后来者,我们应该在对食货学派及其“社会史观”作出科学评价的基础上,吸取其经验教训,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本,从中国历史与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地认识中国古代社会性质与社会矛盾运动过程,从而推陈出新,促进新时代中国史学的繁荣发展。
中国国家历史又双叒叕上新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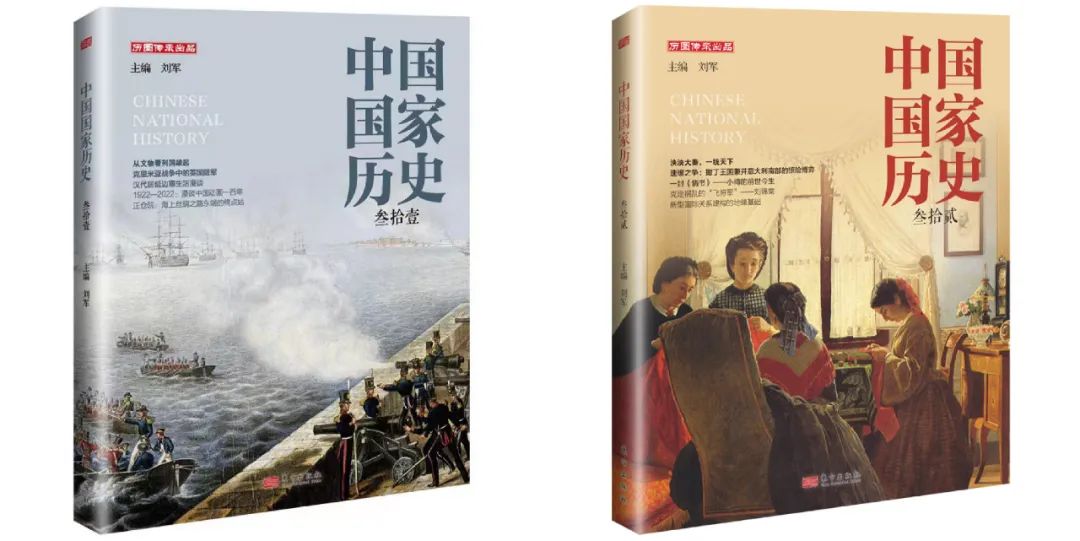
《中国国家历史》邮局征订套装(征订代码:28-474)正在火热进行,一套四本,一次性拥有全年装!
识别下方小程序或点击下方“阅读原文”直接购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