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晶 邱瑜敏
编辑|薇薇子
来源|后浪研究所(ID:youth36kr)
这场女儿起诉母亲家暴的案件,法院是在线上不公开开庭审理的。一头是23岁的北京女孩小骨。为了保证周边环境安静,已经搬离了家、住进青旅的她,特意花300块钱租了一天的单间。她把自己从小到大获得的43张奖状全都贴在了墙上,整整一墙。她边讲边流泪,努力向法官证明:妈妈打我,真的不是我有问题。画面另一端,是小骨50多岁的母亲。轮到母亲发言时,她把想说的话写成了一份稿子,照着上面的念,提及辛辛苦苦为了家庭的付出,说着说着也是声泪俱下。当着法官的面,母女两人都在哭诉自己的痛苦和委屈。但父亲是缺席的,他拒绝为母女二人任何一人出席,用小骨的话说,他必须一碗水端平。这是2022年4月下旬。1个月前,小骨正式以母亲侵犯她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为由,把母亲告到了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将母亲告上法庭后没多久,她得到了法院的人身安全保护令。此后的一审、二审,法院均认定,母亲的教育方式欠妥,但也均以证据不足判定小骨败诉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母亲的家暴行为与她主张的损害后果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她对判决结果不服,申请北京高院再审。今年7月底,北京高院最终裁定,驳回了她的再审申请。至此,她已经走完了所有的法律程序。和母亲对峙1年多,小骨有八个月都住在什刹海边上的一个青旅里,她曾经告诉父亲,如果母亲不写下再不殴打辱骂她的保证书,她就决不回家。从小,她就和父母一起,住在北京二环内的家里。四十多平的一居室老破小,小骨没有自己的房间,她从小住在客厅的上下床,直到上了大学,才有了一张宿舍用过的床帘做隐私遮挡。客厅堆满了杂物,拥挤逼仄。一楼的窗外被民房盖的顶夺去了视野,阳光无法照进来。小骨描述,她大一时,就是在这个空间被母亲殴打到医院的——那也是母亲最后一次对她动手。在8月的一个午后,我们见到了小骨,她有近一米七,身材瘦削,脸颊凹陷,穿一身黑色的连衣裙,腰间绑了cosplay会用到的黑色腰封,看起来像个女战士。她向“后浪研究所”讲述,数十年喜怒无常的母亲、在她求助时演“岁月静好”的父亲,以及她手腕上的六七处疤痕,是在她实在受不了这一切时割的。小骨有时会回避我们的问题,比如为什么还不从家里搬出,有没有想和母亲和解。她偶尔有些激动,讲述时,抓起及腰的头发向后甩去,尽力表演出母亲残暴的形象。小骨所在的社区工作人员王明深度介入过小骨与母亲的纷争。他在复盘这件事说了一段话令人深思。他说,刺猬式的父母表达爱的方式就是伤害孩子,但你不能否认,那不是爱。一个人跟原生家庭和解需要时间,可能这个时间很长,长到父母都等不到你的那一天。以下是小骨的讲述。

心理学上有个“踢猫效应”,我就是那只猫
我的母亲是四川人,又能干又漂亮,从小在家就是大家长式的长姐,管着妹妹们。我父亲从小读书很好,在那个年代能从云南考上北大,是家里宠着的天之骄子。他遇到了我母亲这样一个把他护在掌心当宝的女人。有一次我父亲跟人起冲突,是我母亲护着,说“要打跟我出去打”,典型的美女救英雄。但是两个人的认知差距很大。生活中但凡有一些基础科学的人很简单就能解决的事,在我妈那是天大的事。母亲不喜欢猫,但是父亲领养回来一只。猫跳上我家新买的冰箱,冰箱嗡嗡作响,我母亲就说猫跳上冰箱,冰箱坏了。我父亲就跟她解释:冰箱嗡嗡作响是冰箱在调节温度,不是坏了。但我母亲在乎的不只是猫跳上冰箱这一件事,她在乎的是“为什么你不经我同意就把猫带回家?”有时候他俩吵架,我母亲说不过就会推搡我父亲两下,我父亲就立马闭嘴了,要么灰溜溜地穿上鞋袜跑出门外,要么就闷在别的房间。吵架也要两人吵到消气才能消解情绪。我的父亲却永远都是一副“讲道理”的样子,他认为吵架是一种非常跌份儿的事情,“我北大毕业的,我不跟你吵”。其实有一种人很喜欢那种吹狗哨式虐待,就是“我知道我这样子会气到你,但是你反应越大,越衬托出我的高贵。”我的父亲就是如此,我母亲经常一拳打在棉花上。但是,她怎么发泄呢?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做踢猫效应,就是一个家里最弱小的东西是猫,你冲这个最弱小的东西发泄是很容易的事,而且这只猫也是你唯一比较好选择的对象。我就是那只猫。小时候,我有一次跟别的小孩玩,两家人都很开心。那个小孩提到了冥币,我也不知道冥币是什么意思,就对我母亲说,我要赚很多很多的冥币。我母亲当着别人的面就给了我一脚。我只会觉得是自己不对,惹妈妈不开心,我会哭着跑去跟妈妈道歉,那会她还会抱着我,知道她自己做得也不对。随着婚姻生活的年岁增长,之后就慢慢变成一把把我推开,大声吼着“我不要你的道歉”。在我九岁的时候,我的父亲出轨了。我母亲有一次把自己锁在厨房,开煤气点火要把家炸掉,我父亲在外面使劲拍门说,整个燃气管道都是连通的,你要是炸了厨房,整栋楼都要炸,这才把我母亲劝下来。他俩最后也没有离婚,就一直这么凑合着。因为只有这样大家才能蜗居在北京这个40多平米的房子里,才能在北京有个家。我父亲时不时不着家,加上我那会进入叛逆期,我母亲便更加疯狂了。有时候我做手工的时候,不小心把胶粘在她新换的桌垫上,脸上“啪”一巴掌就过来了,骂我“败家子”。我如果有一点过激的行为,比如质问她“你为什么打我?”紧接着又一巴掌。有时候你流泪的时候,她就倒数“321”,命令我不准哭,然后给我一脚。我那会还不知道痛苦,只是本能地害怕。我从小生活在这种环境里,也没有人告诉你,打小孩是不对的。我那段时间特别害怕失去爸爸妈妈,各种讨好他们,什么累了给你捶捶,我妈就拿着手机录,颇有点生命最后影像留念的意思。我从小到大的成绩一直很好。父母对外一直把我捧上天,我会有一种错觉,他们给我指的路一定是对的,我只要让他们满意。所以我努力做到母亲要求的东西。我只有拿了好成绩,他们才会抱着我,“来,宝贝亲一下”。后来,连这个都没有了,可能下一个小时就呵斥我,“你什么时候收拾你的东西?321……
我会怀疑自己,这一切是不是我的错?
作为家里的独生女,我从小到大都没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我家住在北京二环内40多平的房子里,一室一厅,父母睡卧室,我睡客厅。我的父亲经常来客厅工作码字,有时候他在客厅工作,我要起床换衣服,很不方便。我对我的空间也从来没有任何自主权,他们只要来客厅就能看到我,就会对我的房间指手画脚,我兼职赚钱要用的服化道东西又很多,却没有太多立体的空间可以收拾,母亲就会骂我乱。她说我不收拾房间不干家务,但是很多时候我干家务,她又说我干得不好,不满意。她不愿意容忍一点点不合她心意的事。一旦我让她不满意了,她就会发泄,即便我和父亲不理她,她也能骂半小时以上,直到她发泄完为止。
图源unsplash
暴力也是会传染的。父亲也对我使用过暴力。十四五岁的时候,有一次我没写作业,父亲出差回来就勒令我写作业,我不收拾。他就拿皮带抽我,掐着我的脖子往墙上撞,最后我的腿上全是皮带印,连我的母亲也看不下去了,她一边帮我上药,一边嫌他下手太狠。我慢慢长大,到了青春叛逆期,遇到这种时候我就会等着,我要看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高中的时候,我被父亲送进了住宿制学校。周末回家,她也会给我做一桌子菜,但是很多时候吃着吃着在饭桌上就开始挑毛病,“你上周说收拾,这周呢?”我买了条项链都会被骂,打个比方她会这样,“戴这个项链勾引谁呢?有点零花钱是让你这么花的吗?”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她会因为什么发作。她发泄的是长期对婚姻和家庭生活的不满。比如她今天工作不顺利,到账的钱少了,她会想到“我的孩子将来怎么办?”又说我将来要嫁人,找个老公对我不好又怎么办?说我那么懒,诸如此类,她会在这个社会的框架下当一个妻子,当一个母亲,她有很多社会框架带来的困扰,但是这些超过了对一个孩子的爱。有时候我也会找我父亲谈,但他永远都是一副“all right,all right ,OK?”他并不在意,反正火烧不到他身上。有一次我在学校犯了急性肠胃炎回了家。我妈又开始一边收拾家,一边骂我。我从沙发上爬起来顶了一句“你不能让我静一会吗?”得,她拿着手上的脏抹布就开始抽我,把我推到地上拳打脚踢。我父亲听到动静才冲出来拦住了我妈,我要报警,他却摁住我的手说“家丑不可外扬。”这是他的一贯主张。我向外求助的时候,父亲还会在外人面前演“岁月静好”,哪有孩子从小到大不挨打的?他把很严重的家暴行为形容成“孩子他妈脾气不太好”。上高中的时候我已经有一些抑郁症的表现了,晚上经常睡不着,厌学,甚至有一次因为成绩不达标被踢出了实验班。这对于一个15岁的女孩来说,简直就是一次羞辱,我逃了一次学。母亲知道以后,她穿着高跟鞋爬上我的高架床踹我的胳膊,我的胳膊青一块紫一块。我仍然会怀疑自己,这一切是不是我的错,是我逃学,是我不思进取,才让父母不开心。有好几次我坚持不下去了就割手腕,我现在手腕上六七处伤疤就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我爸看到我这个样子,他只会说,“我讨厌你这样”。而我母亲看到这些好像也无动于衷,她会举着我的手腕就像讲笑话一样地问别人说,“你看看,这美容能修掉吗?”她没有说跟我说过一句道歉,一点台阶都没有,对自己所有的错误永永远远都是沉默。
她总要抓住一切机会去显示自己的主权,这是一种掌控欲,而不是一种尊重。我十八岁的时候,考上了北京的一所重点大学。父母给我按月打生活费,一次2000元,但是家里的钱都在我母亲手里,我每次跟她要钱都会挨一顿骂。后来我跟父亲说了这个情况,就变成他去要,他替我挨骂,要到钱再转给我。为了摆脱这种控制,我平时会刻意省点生活费,也会做兼职,比如帮别人化妆,给自己挣点钱,有段时间我也做主播,开个情感电台,每天跟网友聊六个小时。我也很少回家。大学的每个假期对我而言都是那么的漫长。有一次寒假,我去闺蜜家躲了10天。我每次走到家门口看见那道蓝色铁门,我都会忐忑,我不知该如何面对那个数十年如一日喜怒无常的母亲,我会不会又一边吃着好吃的菜,一边被她骂得狗血淋头。2019年,我在北京安定医院诊断为抑郁状态,睡眠障碍。你能想象吗?我可能把全世界的时区都过了一遍,不知道睡几个小时,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后来,我不得不休学了一年。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很撕裂。身边很多人都说“你妈妈性格很好,不可能家暴的”。我想起小时候母亲带我出去逛街跟朋友吃饭,她也会大大咧咧地说:看上啥就买呗。我过生日的时候,她也会给我买毛绒玩具,请院里的小朋友来我家吃蛋糕。她面对外人的时候热情仗义,请吃饭送礼物,毫不吝啬,典型的大姐大,有时候被人当枪使也无所谓。我知道她有个朋友摊上了网络诈骗,我妈看出来那是骗人的,她看不下去就想劝劝她那个朋友,结果还被恨上了。我们尝试修复过母女关系。很多次我以为她要发脾气了,但是我发现她在努力地控制自己,她会离开我面前,找个地方冷静下来,而不是指着我的鼻子骂。有时候不合她心意了,她会学我父亲的方式把一件事笑着调侃出来。甚至会小心翼翼地考虑我的需要。她的职业是保险销售,有时候我看她面对外面那些人情世故确实很辛苦,经常听她电话里吐槽这个那个的,还要给客户赔这个赔那个的,也是要挣个头破血流的。她9月8日生日的时候,我也会给她发个98元的红包。有段时间我去漫展给客户化妆,我也会带她去,后来她逐渐意识到我确实成长起来了,独立到她确实该像我其他同学家长那样去尊重一个独立的孩子。我原本以为我可以有一个正常的家庭了。但是没想到我大三复学以后最重要的一次期末考试前,她又爆发了。那次我特意提前一周回家拿我要用的衣服,结果她又开始骂人,半小时起步,一边骂骂咧咧一边干自己的事,或者看一看手机然后突然想起来了,再补一句。她主要嫌我生活作息不好。因为我得了抑郁症以后作息非常紊乱,都不是什么昼伏夜出,是滚轮式的,嗜睡和失眠交替出现。母亲骂我的时候,我整个人大脑一片空白,躺在床上起不来,瘫在家里整整一周,那是期末考试前复习的最后一周。我要背10万字的材料,但是那几天我什么都背不进去,甚至有一科都挂科了。我现在完全不想承认那些温暖了,那些对我来说都是有毒的糖果,再甜也难掩毒杀你的事实。
我想我确实受够了
你觉得我能期待我的母亲发生改变吗?她已经五十多岁了,是我年龄的两倍。她这样过了一辈子了。但是我依然很绝望,为什么我要被这样的人支配我痛苦的二十年?我看过一本书,说人一定会在忍耐到再也无法忍耐的时候去改变。我想我确实受够了,我再这样下去,我的学业也毁了,我好不容易好起来的抑郁症也复发了。2021年年底,我就从家里搬了出来,住进了青旅。那个时候我的生活很拮据,一天房费100元,我很快就没钱了。我一边忙学业,一边兼职赚钱。我想让父亲给我打钱,但是他们只想逼迫我回家。在青旅住的时候,有一个印度的小姐姐听到我的遭遇都哭了,我很感谢她,她是第一个为我流泪的人。我的朋友几次要资助我,我都拒绝了。我不想任何一个人为我承担生命的重量。 我开始在网上搜索孩子遭遇家暴该怎么办?但是搜遍全网也只有夫妻家暴,没有一个受家暴的孩子该怎么自保的指导。我问过妇联能不能上门调解,得到的反馈是建议走法律程序。我父亲曾向社区寻求帮助,我也很感谢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我,我能感受到他就是单纯地渴望你要活下去。他在现实层面也为我争取了所有能争取的资源,包括帮助我解决经济危机,还帮我安排了三次免费的心理咨询。但是最后也没能解决我被母亲家暴的困境。这些都坚定了我走法律程序的心。与其说一直觉得是我的错,你不如正视自己,正视法律赋予你的权利。起诉她就是想用法律的手段保护我自己,至少让我妈知道,她这样做是不对的。我当时了解了一点法律知识后,辗转找到了我的援助律师。我那会一边忙学业,一边跑法律程序搜集证据,我自己去医院收集当时的就诊记录,重新找回了被母亲殴打之后的照片,很多照片都被我删掉了,因为太痛苦了。我把父母辱骂我的录音转成了文字。我还准备了我抑郁症的病历,之前跟母亲发生冲突的报警记录等等,都拍照打印下来。我花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准备了20多页的证据,其中还有我父亲给我写的信。我的援助律师也是一个孩子的妈妈,她后来接触了我搜集的证据,听了那些我妈骂我的录音,我们一字一句敲下我妈是怎么辱骂我的文字,那个声音在耳机里反复播放,没人会受得了。2022年3月,我正式以我母亲侵犯我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为由,把她告到了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其实在起诉我母亲以后,我还是没有彻底觉醒。我真正自我的觉醒,是我收到了法院裁定的人身安全保护令。 开始走法律程序以后,我意外得知除了起诉,我还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让我母亲停止侵害,所以我后来又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当时正是寒冬腊月,我还租住在青年旅社,一天只吃一顿饭,欠了很多钱。我不知道能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能做的只有漫长的等待。当时抑郁症的症状也比较严重,经常半夜两三点才能入睡,为了不影响我舍友休息,我尽量不打开手机,就那样熬着。让人意外的是,在2022年4月,东城区人民法院批准了我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并且明确裁定禁止我的母亲殴打、威胁我,如果违反上述禁令,会视情节轻重依法处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份人身安全保护令寄到了青旅前台,我收到这份裁定的时候,感觉自己就像范进中举一样,瞬间感觉有活下去的理由了,抑郁症状都轻了很多。
我对这场官司也比较乐观。4月下旬,法院在线上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我起诉我母亲家暴的案件。为了保证周边环境安静,我还花300块钱租了一个单间,把我从小到大获得的43张奖状全都贴在了墙上,整整一墙,我努力向法官证明,妈妈打我,真的不是我有问题。开庭的过程中,我想到了很多痛苦的事情,讲着讲着就会流泪。在画面另一端的母亲情绪毫无波动,轮到她发言的时候,她把她想说的话都写成一份稿子,照着上面的念,她说她凌晨三四点起床,辛辛苦苦为这个家,说着说着也声泪俱下。就这样,我和她当着法官的面相互哭诉自己的痛苦和委屈。那我的父亲呢?他完美地隐身了。我曾请求他为我出庭作证,他拒绝了,他不会保护我这个弱势方。他一直认为,这是你俩之间的事,他觉得如果他失去妻子,他可能会失去房子,如果失去女儿,他就是中年丧女。所以他必须一碗水端平。没想到的是,我一审败诉了。东城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定我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我母亲对我长期实施家暴,也不能证明我的抑郁症是跟我母亲发生冲突所致,所以不支持我的主张。但是法院也提到,我母亲教育子女的方式欠妥,给予批评指正。我当然不服,坚决要上诉。上诉的时候,我新增了六份证据,包括四个人的证言,提交给了北京二中院。现在想起来那段时间的我是混乱的,痛苦的。青旅的房间窗户很小,几乎没什么阳光。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看一眼塔罗牌,看到的大多数都是会让我更加愤怒的答案,事实也证明,结果的确很愤怒。经历了漫长的9个月等待,二审我又败诉了。法院再次认定,我母亲的教育方式欠妥,但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我母亲的家暴行为与我主张的损害后果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我最后不得不向北京高院申请再审,但是再审申请被驳回了。自此,我和母亲的这场纷争,几乎穷尽了所能用的法律手段。
去年8月,我最终回到了离开8个月的家,回到了我住的客厅,那个完全没有私密性可言的房间。母亲还是老样子。但是她好像也不敢再随便动手了。一审判决的时候,法官在判决书里告诫我母亲,身为人母,应注意自身言行,加强同女儿的沟通交流,对其适时地表达关爱,主动化解隔阂。偶尔我感觉她还想修复母女关系。有一次她拿了一个包杵在那儿,问我要不要,我当时不想接,有几秒钟不敢理她,不敢抬头,但我感觉她的表情也越来越凶,所以我还是接了。我现在想,即便她想修复母女关系,也还是用强迫的方式。我打算冷处理这段关系,我们已经有一年多没交流过了,眼神交流也没有,我拉黑了她的微信,平时在家里也尽量避免碰到。暂时我也不考虑搬出去住,毕竟在外面租房太贵了,我目前还打算继续考研深造。我曾经想做一名教师,但是我现在完全不想这件事了,我想考电影学院,拍片子。我之前在B站做了一个反家暴的视频,反响很好,有上百个有家暴经历的网友评论,问该怎么做。我也远程干预过几个孩子的自杀危机。
所以即便我败诉了,我还可以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那些还在经历家暴的孩子,你们可以怎么做。我觉得人要有希望,要有喜欢的事情去填满你的心,用爱和执念支撑着自己活下去。我还把我视频的弹幕分享给我父亲看,让他一遍遍认识到,他的逃避伤害了我。我也会给他最直接的情绪反馈,告诉他哪儿错了,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认为都是自己的错。我父亲是有改变的,他现在支持我做反家暴的公益视频,也支持我继续考研深造。在我和我母亲的这场纷争里,其实没有输赢,大家都是输家,都不配拥有幸福的家庭和快乐的人生。她现在虽然不再打骂我了,但是那种延后的痛苦会伴随我很久很久很久。其实,我深刻地意识到在这个家庭里,除了父母之外,还有第三个施暴者,那就是我自己。之前我一直以母亲的判断为准,我必须努力学习,方方面面都很优秀,拼了命地让父母满意,才能给自己博得一点点不惹他们生气的理由。所以我自己对自己的虐待可能比父母还要狠。我从来没有体会过完整的内心是什么感觉,我需要慢慢重新感受和接纳自己,把父母施加在我头上的精神枷锁去掉。小骨视频下的评论
我在修复好自己的内心之前是不会考虑成为一个母亲的。我为我的原生家庭痛苦了很久。你也不能指望一个家庭、一个爱人去拯救你,可能我的母亲就是这么期盼我父亲的,期盼父亲尊重她,但是她的期望落空了。记得大学期间我抑郁症休学一年后返校,她开着她那辆黑红黑红的电动车,风风火火地送我到西三环的学校赶早八点的课。一路上我们没有交流,她没有说话,我也没有说话,我也没有像正常的母女那样去触碰她的肩膀。我头上永远盘旋着一个她随时可能家暴我的阴影,挥之不去。(应受访者要求,小骨与王明均为化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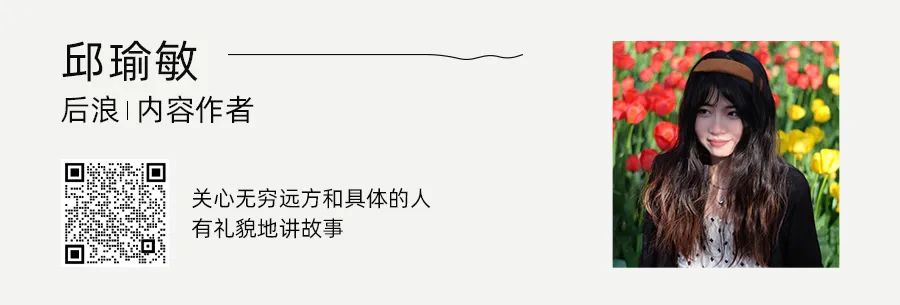
36氪旗下年轻态公众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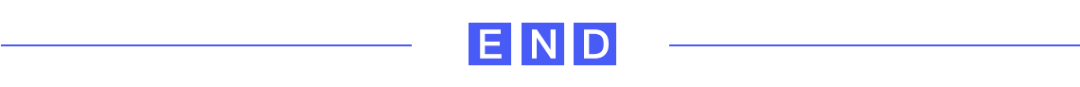


来个“分享、点赞、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