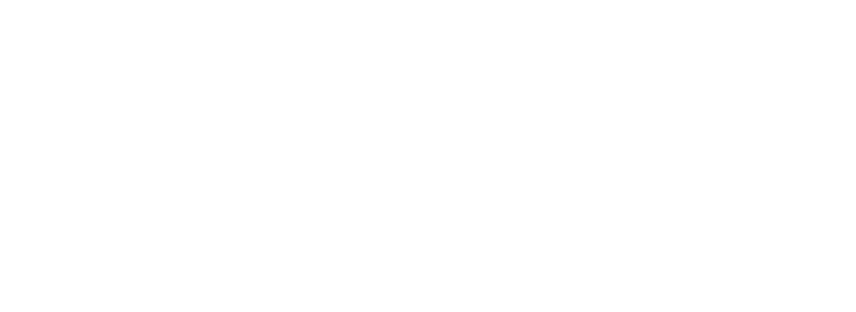
 妙莉叶·芭贝里与她的猫。(图/Boyan Topaloff)“当你是个年轻的作家或小说家时,你不理解你写的任何东西,你写下的那些都来自你潜意识深处,你只是看到了眼前的所有事情。但随着时间推移,你会更好地理解你正在做的事情和你必须做的事情。”13年前,法国作家妙莉叶·芭贝里首次到访中国。彼时,她在上海世界博览会现场。那一年,她的书作《刺猬的优雅》中文版上市不久,但在此之前,看过同名电影的人们,已经对那个探讨孤独、生死等命题的故事有所了解。无论是书还是影片,都让人们认识了哲学家一样的小女孩帕洛玛、其貌不扬却有着丰饶精神世界的公寓女门房勒妮,以及彬彬有礼、真诚和善的日本房客小津格郎。这些虚构的角色身上,或多或少都带着芭贝里自己的特质。在过往的采访中,她说:“她们(门房太太和小女孩)是同一个人的一体两面。因为这是我一个人写的。这两个角色能把我内在性格的方方面面展示出来。但是这两个人很不一样,其中一个能让我以孩子的口吻说话,另一个能让我怀着成人的情感说话。”最初,书只印刷了3000册,两年半过去,数字变为200万册。在图书市场上,这算得上出版“奇迹”。而这仅仅是芭贝里的第二部作品。就连她自己也没想到,这部书作竟能如此畅销。《刺猬的优雅》(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2月版)封面。值得一提的是,写作《刺猬的优雅》时,芭贝里尚未去过日本。书中的“小津”完全是她想象出来的,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她希望可以向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致敬。但读者发现,故事里频现的日本文化符号以及东方人的行为方式,基本与现实没有违和之处。芭贝里曾讲过,自己对东方哲学饶有兴趣。所以与日本相关的元素,也时常出现在她的书作中。她的新作《狐狸的灼心》,更是直接将叙事空间放到京都。她曾在那里有两年的生活经历,此时的她,对这个国度以及东、西方文明有了更多元的认识。今年11月中旬,芭贝里带着这部新作来到北京。接受采访的前一晚,她刚刚抵达。虽然这次停留时间不会太长,但她相信下一次“会再久一点”,因为她“对整个亚洲都非常着迷”。借此契机,《新周刊》对芭贝里进行了专访。《狐狸的灼心》(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10月版)封面。
妙莉叶·芭贝里与她的猫。(图/Boyan Topaloff)“当你是个年轻的作家或小说家时,你不理解你写的任何东西,你写下的那些都来自你潜意识深处,你只是看到了眼前的所有事情。但随着时间推移,你会更好地理解你正在做的事情和你必须做的事情。”13年前,法国作家妙莉叶·芭贝里首次到访中国。彼时,她在上海世界博览会现场。那一年,她的书作《刺猬的优雅》中文版上市不久,但在此之前,看过同名电影的人们,已经对那个探讨孤独、生死等命题的故事有所了解。无论是书还是影片,都让人们认识了哲学家一样的小女孩帕洛玛、其貌不扬却有着丰饶精神世界的公寓女门房勒妮,以及彬彬有礼、真诚和善的日本房客小津格郎。这些虚构的角色身上,或多或少都带着芭贝里自己的特质。在过往的采访中,她说:“她们(门房太太和小女孩)是同一个人的一体两面。因为这是我一个人写的。这两个角色能把我内在性格的方方面面展示出来。但是这两个人很不一样,其中一个能让我以孩子的口吻说话,另一个能让我怀着成人的情感说话。”最初,书只印刷了3000册,两年半过去,数字变为200万册。在图书市场上,这算得上出版“奇迹”。而这仅仅是芭贝里的第二部作品。就连她自己也没想到,这部书作竟能如此畅销。《刺猬的优雅》(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2月版)封面。值得一提的是,写作《刺猬的优雅》时,芭贝里尚未去过日本。书中的“小津”完全是她想象出来的,之所以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她希望可以向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致敬。但读者发现,故事里频现的日本文化符号以及东方人的行为方式,基本与现实没有违和之处。芭贝里曾讲过,自己对东方哲学饶有兴趣。所以与日本相关的元素,也时常出现在她的书作中。她的新作《狐狸的灼心》,更是直接将叙事空间放到京都。她曾在那里有两年的生活经历,此时的她,对这个国度以及东、西方文明有了更多元的认识。今年11月中旬,芭贝里带着这部新作来到北京。接受采访的前一晚,她刚刚抵达。虽然这次停留时间不会太长,但她相信下一次“会再久一点”,因为她“对整个亚洲都非常着迷”。借此契机,《新周刊》对芭贝里进行了专访。《狐狸的灼心》(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10月版)封面。
“我写小说,就是为了去
理解那些我不明晰的东西”
新周刊 :你写作这本书的契机是什么?怎样的生活经历让你决定将故事放置在东、西方的双重文化语境中? 妙莉叶·芭贝里 :实际上,在这之前,我还写了另一本小说《我将一生赠予你》。在那个故事中,我写了一个40多岁的女人萝丝的故事。她在巴黎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代,突然有一天,她的生父去世了。她的生父是一个生活在京都的日本人,留下了一笔遗产,萝丝也因此到了京都。在那里停留的一周,永远改变了她的生活。那本书里,你可以通过法国人的眼睛,去看京都与日本。之后,我觉得我该写一本完全不同的书。但我不能,因为那些角色还一直跟随着我,我知道,我和他们的联系还没有结束。我真的很想更多地了解故事里的人,尤其是她的父亲。所以我决定再写一部小说,故事就发生在她去京都之前,但这一次,是从父亲的角度来讲述这个故事。在上一本作品里,父亲是缺席的,而这本《狐狸的灼心》,则是通过他的眼睛去看世界,女儿则是缺席的。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因为我是法国人,我只在日本生活了两年。但那两年是不寻常的,无论是感受到的文化差异,还是生活里的发现,都时常让我感到惊讶。可以说,我花了十年才写下这段非凡的经历。
 与日本相关的元素,时常出现在妙莉叶·芭贝里的书作中。图为日本京都清水寺。(图/视觉中国)
与日本相关的元素,时常出现在妙莉叶·芭贝里的书作中。图为日本京都清水寺。(图/视觉中国)
新周刊 :你在过往的采访中说,自己对东方的哲学很感兴趣,有哪些东方哲学或美学吸引着你?它们与法国的文化有哪些不同? 妙莉叶·芭贝里 :我不是东方哲学专家,也不是日本文化专家。对小说家而言,用现实的碎片去组成另一个现实,其实不需要非常精确。所以坦诚地讲,我对这方面了解得不是很多。但我看到的很多事物真的让我非常着迷,有的根本无法解释。 我觉得在东方,事物存在的关系是完全不同的。我想讲一个我在日本花园里的经历。我认为那是东方文化吸引人的一大原因。一次,我去日本的一座庭院。我人生中第一次有这种感觉——我不是面对着一件艺术品,而是身处其中。在里面,时间和空间是不存在的,非常具体,非常奇特。那一刻,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接近自己。同时,我又有一种感觉——自己与永恒联系在一起。这是我在西方的背景和知识中从未经历过的,一种具体的、与现在完全不同的关系。 新周刊 :你之前书写过日本男人,这一次为什么会将小说再次聚焦在这样一个男性角色身上?在书写时,会不会存在一些视角上的问题? 妙莉叶·芭贝里 :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做这件事。写小说其实可以让你成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所以我在写作这本书的两年里,每天8点55分就开始“做那个男人”。这段经历是令人兴奋的。我觉得,我写小说,就是为了去理解那些我不明晰的东西,因此,这些角色离我越远,我对生活和自我的了解就越多。这也是我了解人类的方式。
新周刊 :你觉得故事里的父亲有哪些特质是让你喜欢的?在现实生活中,你所处的父女关系与书中所写的有相似之处吗? 妙莉叶·芭贝里 :他知道如何给予,这是非常罕见的。因为我们一般人在这种境况下都会要求回报,自发给予而没有得到任何回报的人,非常令人珍视。至于现实生活,我从来没有回答过私人问题,但谢谢你问这个问题。 新周刊:你在很多作品里都会写到人孤独的状态,这本书也是一样。为什么会有这种倾向?对你来说,孤独是常态吗?你在生活里如何处理这种状态? 妙莉叶·芭贝里 :原因肯定在作者身上。一开始我不知道为什么,当你是个年轻的作家或小说家时,你不理解你写的任何东西,你写下的那些都来自你潜意识深处,你只是看到了眼前的所有事情。但随着时间推移,你会更好地理解你正在做的事情和你必须做的事情。我也不例外。如何与他人见面,如何卸下我们的防御走向另一个人,这始终是我们要面对的艰巨任务。也许是我对人性怀抱偏见,我总觉得一个人是很难和别人合作的。但我觉得这是我们人生的一大课题,我们必须竭尽全力,这样我们才能逃离这种可怕的孤独。这就是我写小说的原因。写作时,你必须离开这个世界,把自己装进一个无限大的泡泡里。但当你走出泡泡,你会遇到很多了不起的人,正是他们教会了你生活上的一些事情。
新周刊 :书中出现了很多次“狐狸”,感觉它有比较强的哲学意味,这个意象代表着什么?让它在小说中存在,有哪些考量?
妙莉叶·芭贝里 :首先,我喜欢狐狸,这是个人偏好。我觉得它们很漂亮。我喜欢它们的神秘感。我住在乡下,有时会看到它们在花园里经过,它们是我所知道的最美丽的森林动物之一。
另外,如果你曾经住在日本,你不会忽视狐狸的存在。它们在传说、寓言和宗教中广受欢迎,去寺庙时,也时常能看到狐狸。它们在日本人的生活中普遍存在,所以使用它,也是很自然的。 在小说里,狐狸就是这种有诗意的、带有隐喻性质的动物。关于它的考量,我觉得书中每个人的解释方式都不同。我的想法是,一个好的故事通常是可以被读者自由解释的,书中留有足够的空白,这个答案,就留给读者。文学与哲学的共同点,
都是在探讨生命的意义
新周刊 :书中不断探讨死亡与新生,比如:“每个人都走向他新生的时刻,我们在孤独中死去,在光明中重生。”这是非常哲学的问题,你如何理解“死亡”与“新生”?它们之间的联系是怎样的?
妙莉叶·芭贝里 :我写下这个句子,并且相信它所讲述的,经历了漫长的虚构过程。我是写到小说结尾才得出这个结论的,在此之前,我并不确定在死亡和新生之间是否有一种联结。但在我失去了生命中的一些人和事情之后,我意识到,我们总有一天会面对死亡。在人类生活里,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话题,我真的很想尽我所能去探索,用我看到的方式,在这之中寻找光亮和内心的慰藉。《狐狸的灼心》以京都庭园的场景开始,书中写到的父亲正在冥想,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终结。(图/jhm.fr) 新周刊 :你在成为小说家之前,是哲学教授。小说如何把哲学概念融入其中?法国作家是不是都会比较倾向这样做? 妙莉叶·芭贝里 :对我来说,回答这个问题有些尴尬。因为我真的觉得自己学习哲学是个错误。我不否认哲学非常有趣,但它不是我把握世界的方式,小说才是。我的父母是法语教师,我不想和他们走上完全一样的道路,所以特意选择了哲学。我对概念不太在行,或者说,我可以很好地处理概念,但要以一种很抽象的方式。我真正想要的是理解生活,对我来说,小说是最好的工具。但我不能忽视这些年来对伟大哲学家的研究,它们都在我的文本中存在过。也许我是个运用哲学的小说家,而不是一个写小说的哲学家。实际上,文学与哲学的共同点,都是想要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选择学习哲学,是觉得自己能从中找到一个答案,但我并没有找到。我就回到了另一个家园——文学。妙莉叶·芭贝里著有《作家的猫》,从封面可以窥见她的喜好:日本元素,以及四只猫——它们会给她提供慰藉。 新周刊 :你之前的故事被改编成电影,你期待这一本书也能被改编吗?你觉得这两种文本在呈现同一个故事时,有哪些不一样? 妙莉叶·芭贝里 :如果可以,当然是好的。这样可以看到城市、寺庙、餐馆和所有坐在这里的人。如果它实现了,我会非常高兴。但我觉得拍电影非常不容易,它有很复杂的工序,你必须拿到很多执照,还要有制片人对这个感兴趣,所以我认为这还是有困难的。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本文首发于《新周刊》总648期《现实的力量》
作家妙莉叶·芭贝里:角色离我越远,我对生活了解越多
与日本相关的元素,时常出现在妙莉叶·芭贝里的书作中。图为日本京都清水寺。(图/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