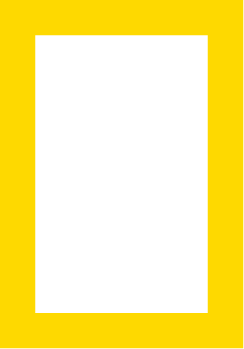
地球是一个奇迹
雨季到来,馋哭食客们的野生菌也从山上噌噌地冒出来了。“先菌子后小人”“看见小人套餐”等调侃,无一不显示出了全国网友对于见手青等云南野生菌的好奇与想象。这些段子与吃菌故事结合,共同拼凑出了一幅充满了诱惑与危险的美食景观。其中最让人捧腹的,当数那首云南山歌:“红伞伞,白杆杆,吃完一起躺板板;躺板板,睡棺棺,然后一起埋山山。”
吃菌,在云南人这里已经成为了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它甚至通过饮食,内化成了特别的地区文化。最简单的例子是,在云南,说一个人“菌中毒”不是说他疯,而是夸这人有所作为,或是活得与众不同。菌子季,更深度的体验是上山采菌子。行走在山野中,亲自采菌,不仅能直击菌子的新鲜,某种程度上,也能打破我们关于野生菌的想象与神往。
每年雨季一来,云南人都心照不宣地知道,又到了吃菌子的好时节了。
今年的雨来得晚了些。5月底,几乎整个云南都处于缺水的干旱状态,昆明玉溪甚至燃起了山火。人们都在急切地等待一场雨。等待一场场雨,一来是为了降下30多摄氏度的高温,再来也在等待雨过天晴。每当这时候,云南人最盼望的不是彩虹,而是野生菌。终于,6月,雨断断续续地来了,第一批“头水菌”出现了。在云南,采野生菌有一个亲切的叫法——“拾菌儿”。看着朋友圈的采菌人,几乎每天都在分享上山拾菌儿的收获,自己也心痒痒地想去“捞”一把,体验一下做当地人的快乐。
在大理,外地人想拾菌儿,最便捷的做法是找个本地向导报团,跟着对方一起上山。自己独自前往,一是找不到有菌子的地儿,二是无法分辨菌子的种类,以及它们的特性,如是否有毒、能否食用等。一个周六的清晨8点,我就跟着向导,从苍山脚下的一条羊肠小道上山了。没想到,仅仅3个多小时的拾菌儿之旅,让我对采野生菌的滤镜碎了个稀巴烂。
大路上是不会长菌子的。只有那些隐秘的、难走的山路,依稀分布着野生菌。这也是一定要跟着本地向导拾菌儿的原因,他们大多有着好几条成熟的采菌路线,既保证了上山的安全性,又能有所收获。上山前,我羡慕别人每天都能采到见手青、鸡枞菌等山珍,以为只要自己一上山,美味也是唾手可得。结果,现实狠狠打了我的脸。在山路上走了半个多小时后,别说见手青了,一朵野生菌都没见着。我以为野生菌漫山遍野,结果它却在和人玩捉迷藏。
苍山上的野生菌往往生长在树丛中,周围全是掉落的松枝
这时,看见有一行人从山上走下来,手提的篮子里满满都是收获,心里不免全是羡慕嫉妒恨:怎么就我们没采着菌子呢?功夫不负有心人,再往上走些,陆续能看到野生菌的身影。它们往往长在大树的脚下,或形单影只,或三五成群。采第一朵野生菌时,我小心翼翼地从根部把它挖出来,以为自己捡到宝了,结果向导冷不丁地告诉你:“这个菌子吃不得哦,吃了会拉肚子。”我只好安慰自己,体验第一,收获第二。但想要摘到见手青的心还是没死,决定继续上路,主打的就是一个“不到黄河心不死”的倔强。采菌子是一件非常考验专注力的事情,说是“眼观八方”也不为过。走山路的同时,你需要四处张望,盯着哪棵树下长着菌子。它们往往个头很小,还被杂草、掉落的松枝等掩盖着,只是探出个伞帽,如躲在树下的害羞的小精灵,生怕被人发现。
路越走越深,能见到的菌子也越来越多,但大多也都是不能吃的种类。为了满足好奇心,也是为了保险起见,每采到一种新的菌子,我都会问下向导这是什么品种、能不能吃。有时候,向导也说不出这个菌子叫什么,但她都能分辨能不能吃。当地人的标准很简单:吃了会拉肚子的菌子,就是有毒的,这是最原生态的民间智慧。终于,在爬了一个多小时的山后,我采到了第一朵见手青。

吃菌,是云南人的一件大事
见手青往往被覆盖在松枝下面。它有着圆形的伞帽、饱满的茎身,属于牛肝菌的一种。由于一被人手碰到,接触到的地方就会氧化,变成靛蓝色,所以被叫做“见手青”。见手青往往是第一批长出来的野生菌,由于味道丰富、菌肉鲜嫩,即便可能会因烹饪不当而中毒,云南人每年还是会争先恐后地采集它来贩卖、食用。
烹饪见手青也是门学问。云南人常见的做法是切薄片,厚度均匀,加大量的油和蒜片翻炒。炒见手青一般不加入任何调料,除了少许的辣椒佐味。这正应了那句话:“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菌中毒》一书的作者聂荣庆是土生土长的昆明人。在书中,他分享了自己一次“危险”的吃菌经历。通常,烹饪见手青时,炒12分钟会比较稳妥。但他的一位资深美食家朋友却偏好拿自己家乡个旧(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辖县级市)的见手青,切成半厘米,加入红、绿辣椒后,仅爆炒5分钟就起锅。这样的料理方式,仿佛在烹制一盘见手青刺身,它的口感更加脆爽,对于第一次尝试的人来说,却无疑是诱惑与危险并存的美食体验。
原来,当地的采菌人半夜就会打着手电筒上山,待我们早上8点上山,别人早已把许多新鲜的见手青采摘了。那隆起的松枝堆,就是他们留下的残破的“战场”。以大红菌为例,这种野生菌大多生长在边远山区的高山上,采摘起来十分艰难。大红菌对生长环境也十分挑剔,它不仅要求那地方温度高、湿度高,且最好是有着弱酸性的红棕壤或赤红壤土坡。同时,大红菌生长周期较慢,降雨后一般等到晴天才冒出。所以大红菌每年的产量都极少,一上市便被哄抢。不同于见手青通常以爆炒的方式来烹饪,人们通常用蒸、炖、烩的方式来料理它。大红菌煲汤更是一绝,能让汤水的鲜美与香味进化到梦幻的程度。
每一朵野生松茸都需要6年的生长周期,且对周遭环境要求十分严苛,不能有一点污染。而当松茸的子实体出土、成熟后,如果48小时内没有被采摘,它将会迅速衰老。采摘松茸,就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同时是需要运气的一件事。这些特性使得其价格比其他野生菌更高出一筹。有趣的是,过去云南人并不待见松茸。在上世纪80年代,昆明人甚至还把它归到鸡枞菌一列中,又因松茸有着奇特的腥味,人们还把它叫做“臭鸡枞”,很少人会特地去买松茸回家烹饪。松茸的地位的变化,靠的是“出口转内销”路线,日本人的追捧让它成为了身价暴涨的宝物。这时候云南人再想吃“臭鸡枞”,也没那么简单了。
野生菌,原来也有鄙视链
云南山区、半山区占全省面积94%,森林覆盖率高,加上降水量充足,天然适合野生菌生长。世界范围内,可食用的野生菌有2500种,云南出现的就有900种,占36%。而在中国,可食用的野生菌有1000种,其中90%都在云南。其中更是有70种可食用的珍贵野生菌,构成了菌子的鄙视链。
鸡枞菌鲜甜无比,拿来做汤或者爆炒都是无上的美味,且无毒,烹饪起来也可完全放心。作家阿城曾在《思乡与蛋白酶》一文中对鸡枞菌不吝赞美:“说到‘鲜’,食遍全世界,我觉得最鲜的还是中国云南的鸡枞菌。用这种菌做汤,其实极危险,因为你会贪鲜,喝到胀死。”为了一年四季能吃到鸡枞菌,云南人有妙招。菌子季要过去时,他们会将鸡枞菌用油炸好,再用这些油将炸好的鸡枞菌封存,一年四季,只要馋了,都能再尝一口鸡枞菌的味道。
还有干巴菌,虽长得其貌不扬,皱巴巴的一团,但其异常丰富的香味,折服了一大帮老饕。《昆明的雨》里,他第一次见到干巴菌是这样描述的:“有点像半干的牛粪或一个被踩破的马蜂窝。”直到吃进口中,他才觉得自己大错特错:“干巴菌是菌子,但有陈年宣威火腿香味、宁波油浸糟白鱼鲞香味、苏州风鸡香味、南京鸭胗肝香味,且杂有松毛清香气味。”
乍听下来,简直世间美味都与其环环相扣,能引得汪曾祺如此赞叹,干巴菌是有两把刷子在身上的。由于异常美味,加上产量少,在云南的野生菌市场上,干巴菌从来是最昂贵的“菌中之王”。这也使得它极有底气能站在野生菌鄙视链的顶端。同样站在鄙视链第一梯队的还有牛肝菌、松茸、松露等。再往下,便是青头菌、奶浆菌等较易采摘、生长量大的菌子了。至于人工养殖的菌子,在云南人眼里,根本算不上菌子,只能被称为蘑菇。

每到菌子季,网上总会广泛流传着各种令人捧腹的吃菌中毒的段子或故事。不同于这些传言中的诙谐与轻松,云南人对于菌中毒一事还是非常谨慎的。在一些饭店吃野生菌火锅,店家会严格把控烹饪时间,设置各种要求,例如一定要煮够一定时间。为此,有些店会在餐桌上放置一个沙漏,只有沙子全漏完后,食客才能开吃。服务员还会全程用眼角的余光瞄着你,看有没有提前“偷吃”。

本地人对于吃菌也同样留足了心眼。那个周六,我从山上采完菌下来后,向导把我的篮子拿了过去,将能吃的、不能吃的菌子一一分开。看似丰收的一篮菌子,其实只有四五朵见手青和几朵杂菌能吃。待我将见手青带回家后,房东逮着了,立马上楼提醒我,没有经验,千万不要自己处理野生菌,“村里已经吃死了好几个人”。
房东妻子看见我上山采菌的朋友圈后,也连忙评论提醒:“菌子不能乱吃,等我过两天采了见手青出来,再炒给你们吃。”最后,我只好舍弃那好不容易采来的四五朵见手青。但一想到过几天还是能在房东家饱餐一顿,又不觉得有什么遗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