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拉帕爸爸(Papa Srapa)”是爱德华·斯拉皮尔诺夫(Eduard Srapionov)的代号。
他生于 1961 年,长于苏联的黄金时代。在上世纪 80 年代,他一边给苏联军队做侦察兵,一边开始鼓捣些实验音乐。他跟一个中尉组了个乐队,在军营和监狱里搞巡演,还获得了巨大成功,,被人们称为“苏联的第一个 DJ”。
结果他太有名了,就招来了特殊部门的混蛋上校来找他麻烦,不给他的磁带过审。他一气之下就在送审的磁带里做了点手脚,让人听了就会发病的那种 —— 果然屠格日涅夫听了之后很快人就没了。

爱德华·斯拉皮尔诺夫(Eduard Srapionov),aka.“斯拉帕爸爸(Papa Srapa)”| 图源受访者
后来他凭着这一身本事成了一个萨满,以合成器替代萨满鼓,以酒精替代死藤水,把血液、唾液、精液都加到自制的合成器里,不停地制造噪音,成了俄罗斯地下圈子里最有名的电子乐手,总是出没于各大怪人音乐节。
2020 年 2 月 23 日,斯拉帕爸爸死了。2020 年 2 月 24 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战争。
我们今天要说的电影《斯拉帕爸爸》,是他在世时最后的纪录。

《斯拉帕爸爸》中文海报 | 字体设计:板砖兮
电影《斯拉帕爸爸》由俄罗斯导演康斯坦丁·伊万诺夫和尼基塔·卡班迪恩共同执导。康斯坦丁是影片的摄影师和剪辑师,而尼基塔则是一名软件工程师和前卫音乐的狂热爱好者。
这片子是他们俩自己独立出资制作的第一部电影,而且这次也是他们主动发邮件找到的 BIE 的—— 他们说这片子在俄罗斯可有名了,都上线了俄罗斯版的网飞,还去过好多电影节,总之中国观众最好也看看,中文字幕都做好了,希望 BIE 来做首发。
而我,一个喜欢 merzbow 的精苏份子,也是真的感兴趣,我们就聊上了。

《斯拉帕爸爸》的两位电影主创,康斯坦丁·伊万诺夫 Konstantin Ivanov(左)和尼基塔·卡班迪恩 Nikita Kabardin(右)| 图源受访者
诚心地说,尼基塔是我遇到过最真诚的采访对象。我们俩操着不够精妙但恰好够沟通的小孩英语,像两个分享心爱玩具的小学生一样分享着中俄地下音乐和文化中的趣闻。这才发现,我们两国的人对对方真的太不了解了,但与此同时,我们又太过相似了。
我问他为什么要来中国放他的电影,他说:“我在看完《北京朋克》这部电影之后,就爱上了中国的地下文化,他们向我展示了真正拥有「内心的自由」的人是什么样的,而这至今仍旧激励着我。”,他接着又说,“只有在为自由抗争的前线,才有「先锋」可言。( The true avant-garde happens where you have to fight for your freedom.)”
于是这段话至今也激励着我,而且在整个采访中,这样的感动还反复出现。
看下去,希望他们的电影和话语也能激励到你。
 电影《斯拉帕爸爸》的诞生
电影《斯拉帕爸爸》的诞生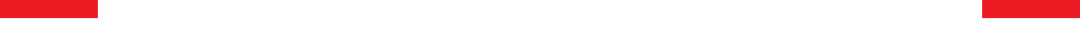
BIE:你是怎么认识斯拉帕爸爸的?你对他的第一印象是怎样的?
尼基塔:我总是和我的朋友们玩些疯狂的噪音和工业音乐,用电脑、合成器、吉他、鼓和人声。多年来,我们做了很多尝试,用一切我们能找的东西,想要做出最怪的声音来。 一天,我们的一个朋友带来了一样看起来像儿童玩具钢琴的东西,指着它对我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斯拉帕爸爸。这东西会让你惊呆的。”他把它打开了,连接上控制器然后马上就用它做出了一些巨诡异的声音。我被这个疯狂又生猛装置震惊了。 他说:“这是一个来自罗斯托夫(俄罗斯西南部城市)的疯男人,他是个声音萨满。他自己做些合成器,你可以直接跟他下单。他做的这些玩意儿都是又独特又让人摸不透,以至于你没法知道他会给你做出个什么东西来,以及要多久才能做好。不只是合成器,他整个人都神神叨叨的。” BIE:怎么想到去拍他的?你们做这部影片的初衷是什么?
尼基塔:一天,我和我的朋友们冒出了一个想法,想要为那些在当下的俄罗斯领域内最不寻常艺术家们拍摄一部影片。这个想法主要受到两部电影的启发,一个是关于一群日本噪音艺术家的纪录片《谁在乎音乐》(2009),还有一部是关于北京地下朋克的电影,《北京朋克》(2010)。 《谁在乎音乐海报》,又名《我们不管音乐是否悦耳》,记录了日本包括大友良英、坂本弘道在内的多个实验/噪音音乐人的故事 | 图源网络 我们希望让全世界的人们都能知道,我们在俄罗斯本地所经历着的实验噪音场景是什么样的。 我们起初不知道怎么拍电影,所以我们就从写剧本开始做起。一开始剧本写的特有野心,比如有在大楼的天台上用无人机拍摄的表演,还有涉及多个艺术家的多条剧情线…… 后来的一天,我跟一个朋友分享了这个想法,他叫康斯坦丁,是一个在圣彼得堡工作的摄影师。彼时,他正好有一个可以做些活动和展览的小文化艺术空间要开幕,于是他顺势就让我们在他的地盘给斯拉帕爸爸做场演出并进行拍摄! 我们没有多想就赶紧召集了所有身边所有有想法的朋友准备起来了,而我也开始试着去联系斯拉帕爸爸。有的朋友负责弄声音,有的准备舞台和布置场地,有的去借音箱,有的去联系了当地的场地方,为接下来的第二场演出做准备。很快,我们就在圣彼得堡搞了一场斯拉帕爸爸的演出,现场有 5 台摄像机从各个角度进行拍摄。此外我们还拍了一场访谈,一些街景,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接下来就是长达 5 年的搁置期。我们手头有 1TB 的素材,但没做出一部电影。原定的剧本成了空想,拍出来的东西没有重点,而我则忙于从俄罗斯搬家到瑞典,并在这儿一住就是 6 年。 直到几年后,我终于积累了一些积蓄和能量,我们才重新聚首,并去斯拉帕爸爸的家乡完成了影片最后的拍摄。 BIE:这人一看就很难搞,你们是如何让他同意拍摄的?拍摄过程中最难的是什么?
尼基塔:斯拉帕爸爸不是典型的艺术家人格,他不追求关注也不爱表现自己。甚至可以说他完全反其道而行之。他总是搞我们,让和他相关的每件事做起来都难上加难。我们用各种手段和他沟通谈判,但他这个人就是不服管,每一步的推进都很难。 比如说在第一次演出的前夕,他原本要跟我们的两个剧组成员一起坐火车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但在整整 3 小时的火车上,他一直否认说自己不是斯拉帕爸爸,不认识那两个人,让他们滚远点。我朋友吓坏了,还给我发短信说“他居然不认识我们!” 事后我们才发现,原来在我们之前还曾有过好几个剧组想拍他,但都没拍成。他反复和我们说:“你们早晚会放弃的。所有拍我的剧组后来都没影了,等着瞧吧,你们也一样。” 这话激得我们非得接着拍下去才行,虽然这让我们花了 5 年多才做完这部电影。 尼基塔:斯拉帕爸爸是没有所谓 “镜头之外” 的样子的。像我们知道的其他艺术家,在有镜头和没有镜头的时候几乎是两个人。但斯拉帕爸爸却没有这个 “开关”,他是发自内心地无视镜头,有没有在拍对他根本没差。他是绝对的、从头到脚的 Real,而他这种极端真实主义始终鼓舞着我们。在这个所有人都想给自己造个假面的世界,去做一个不是 “所有人” 的人,斯拉帕爸爸选择用一种激进的方式做他自己,完全不管周遭的现实是怎样的。 电影拍摄中的斯拉帕爸爸和两位导演 |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尼基塔:这部电影是完全独立制作的,没有任何组织和机构的赞助。所以我们俩就需要做所有事。康斯坦丁负责大部分的拍摄和剪辑,而我则负责所有的组织工作,包括组织拍摄、承担所有支出、组织各部门通力合作、营销推广和电影节合作。我们的合作是长期且稳定的,从一开始有了这个想法直到今天,我们共同解决了无数大的小的问题。而这个过程还没有结束,我们现在仍在围绕着这部电影做些内容,比如推广物料和为全球各地不同电影节和放映做的多个版本的剪辑。(特别说明:中国分享的版本也是经过“特殊剪辑”的,为了放映的正常进行,我们不得不将裸露画面哔掉了) 比如上图这个有裸露的演出场景就被剪掉了,但加起来一共也就一分钟 |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康斯坦丁在剪辑上花了大量的时间,才把那些到处搜集到的采访片段、影像素材和网络拾遗剪辑成一个简洁的故事线。我则负责顺着网线挨个跟这些影片的创作者拿授权,以确保康斯坦丁的工作能毫无阻碍地进行下去。 BIE:我注意到影片给一些受访者的独白加了回音特效,听上去很有意思,你们为什么这样设计?
尼基塔:既然这是一部关于噪音音乐的电影,那声音设计就会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这是我们从一开始就想好了的。我们的想法是,这部电影的声音应当能被作为一个独立的作品来聆听,像广播剧那样。为此,Alexander Grigoryev 加入了我们团队,他是一个电子音乐制作人和合成器设计师。接着,一个 10 人作曲家团队为电影贡献出了他们做的音乐和声音片段,其中一些是专为这部电影而作的。而 Alexander 的工作就是挑选声音和音乐,并将它们用最有创意的方式剪辑出来。经过他的创作,可以说你不仅是在 “看” 电影,也是在 “听” 他的作品。 而且,有时候人的声音在电影里作素材用的时候就会变得有点不对味。于是我们想,反正到时候这个电影的大批观众都是来自世界其他国家的,他们也听不懂俄语,那我们至少让声音听起来有意思一点吧!  斯拉帕爸爸是谁?
斯拉帕爸爸是谁?BIE:斯拉帕爸爸在2022年去世了,他的死因是什么?他这么戏剧化的人,肯定也死得很精彩,能不能说说看?
尼基塔:斯拉帕爸爸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是不会无声无息地离世的。他死后,这个电影的意味也变了,影片的第二部分开始变得像是记录了一个时代的落幕。他甚至还在电影中说了“我明确地知道我将何时走向死亡”这句话。 他刚好死在了俄乌战争爆发的前一天,我深信他对此也有所感。他感受到时代已然终结,他该走了。因为就在离他住的城市非常近的地方,那些坦克已经在蠢蠢欲动了…… 在他的濒死之际,他对一切抢救措施说“不”,就这样接受了死亡的降临。 虽然如此,但如果这是一场一切都被提前安排好的死亡,那斯拉帕爸爸就不是他了。他只和几个自己最亲近的朋友说了他想要火葬,而且不想被埋在地下……但他却没和他的亲戚们说这事,因为他基本不跟他们说话! 所以在他死后,就有戏看了 —— 他的亲戚们准备土葬他,但和斯拉帕爸爸相熟的整个社群带上了他的粉丝们一起去跟亲戚打架,抗议这个决定。所以即使斯拉帕爸爸已经死了,围绕他的好戏还在上演。 BIE:在电影中,我看到他房间的墙上画着很多神秘符号,并且有资料显示他同时也是一位俄语的考古学家。你们知道那些符号是什么吗?
尼基塔:斯拉帕爸爸对俄语的历史非常感兴趣,很严肃的那种兴趣爱好。在俄罗斯有一个备受争议的流派,他们认为俄语的每一个词汇中都蕴含着古老的智慧,而每个词的形态都指向一种特殊的寓意,包含着一些意想不到的讯息。 他为此着迷并经常谈论它,为此我们不得不努力让他转移话题,因为我们知道说太多俄语的东西会让世界其他地方的观众觉得不那么有意思。 对斯拉帕爸爸来说,语言是另一种形式的神秘学。他对它的兴趣不止于语言学这么简单,而是一种和祖先进行连结的萨满仪式。 至于他墙上的符号……实话说,我不认为有人知道它真正的意思,因为他每次解释的都不一样。我相信这其实是一种他自己创造的符号和维京时代的如尼符文(古北欧文字,常作宗教和神秘学用途)的结合,也可能是他在研究世界各地不同语言文化的过程中搜集而来的。 这确实是个好问题,但恐怕我永远没有机会知道它真正的答案了。 就是墙上那些符号,电影里也出现了很多次 |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BIE:让斯拉帕爸爸在俄罗斯地下音乐圈里出名的是什么?
尼基塔:斯拉帕爸爸的名声一直在增长,但也没有什么别的原因,除了他对自我营销完全零兴趣这件事。他没有网页,从不组织任何形式的营销活动,从没尝试去好好宣传下他的合成器,也从没发过一张专辑。他只在日本发过一盘磁带,还有一张在俄罗斯发行的黑胶,但也只录了其中一面(另一面是其他艺术家)。他的音乐都是随机传播的,没有封面,他演出的录像也通常是被人匿名发在网上的。 至于他的社交账户只用来发发他合成器的照片,以此来卖掉它们赚点生活费,也就这样了。 因此他能成为整个俄罗斯最人尽皆知的电子音乐人这事确实挺匪夷所思的,要知道他可一张专辑都没发啊…… 斯拉帕爸爸在日本发行的磁带 | 图源:discogs.com BIE:哦?这么说的话,他在俄罗斯更广大的音乐爱好者中也很有名吗?
尼基塔:斯拉帕爸爸在普罗大众中可一点都不知名,但他的一些演出片段在网上病毒式的传播并且获得了上万的浏览量。所以他的音乐没进入大众视野,反而是他的 meme 让他在网上出了名。 BIE:斯拉帕爸爸完整地看过这部电影吗?他对此作何评价?
尼基塔:斯拉帕爸爸原本对这部电影持怀疑态度,对我们也不咋友好,还一直跟他的朋友开玩笑说我们做的都是些屎一样的东西。他甚至没兴趣看一眼这个片子。 但慢慢地,有朋友说服他尝试在演出的时候放映这部关于他的影片。就这样,他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做了两场映后的演出,也和现场的观众一起观看了这部电影。出乎我们意料的是,他开始对我们敞开心扉,不再攻击我们了。他倒是没说太多关于电影的东西,但仅仅是 “他看了我们拍的电影还没把我们杀了这件事”,就已经很让我们高兴了。 事实上,我们收到了一些他的 “硬核” 粉丝对我们的批评。他们不接受我们,因为觉得我们和他们不一样,觉得我们 “假”,说我们 “装逼”,甚至认为我们展示出他“错误”的一面而毁了斯拉帕爸爸的遗产。有一些人还觉得我们是用他来赚钱,好像我们是来摧毁地下文化的资本家似的。  关于俄罗斯地下文化的谣言和真相
关于俄罗斯地下文化的谣言和真相BIE:影片中提到,斯拉帕爸爸是勃列日涅夫的最后一个 DJ,甚至可以说是整个苏联时代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 DJ……听着挺像吹牛逼的。这种说法在俄罗斯能得到普遍共识吗?
尼基塔:斯拉帕爸爸是个讲故事的人。让我偷偷告诉你,这当然只是个他说的其中一个故事而已。但当这个故事被人们口口相传的时候,就展示了我们有多么「想要」相信斯拉帕爸爸真的就是他所讲的那个故事中的人。 我们再也没法知道这事的真假了,我个人当然是不信勃列日涅夫真的听了他那盘录音的。但我特想相信这是真的!魔法和萨满教是我们很少能去亲眼见证的东西,但如果真有人能做到……那个人毫无疑问就会是斯拉帕爸爸。 BIE:俄罗斯电视节目《通灵之战》在中国挺火的。而斯拉帕爸爸也是个萨满。你怎么看如今俄罗斯对玄学的狂热?
尼基塔:《通灵之战》居然在中国火了,我大为震惊!而在俄罗斯,据我所知,只有上了年纪的人才看这节目。 我真不知道怎么解释俄罗斯人对所有神奇的、超自然事物的狂热,但确实玄学风气极盛。可能因为在俄罗斯的很多地方,居住环境都是又寒冷又艰难又阴郁的,让人有想要脱离现实的欲望,并真的去找法子这么做。这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 在 90 年代苏联刚刚解体的时候,有过一段媒体报道和书籍出版完全自由不收管制的时期,于是很多超自然题材的内容涌现并成为流行。同期,还有一群宗教和伪宗教团体还有邪教头子冒出来。 在苏维埃时代末期,所谓的“魔法师”开始出现在电视上,其中最有名的是一个 Kashpirovsky 的家伙,他通过电视疗愈观众。 Anatoly Kashpirovsky,他在 80 年代差点成为俄国新的 Rasputin | 图源:soggymush.wordpress.com 在这方面,俄罗斯真的跟印度真的很像,这种事随处可见。对了,俄罗斯有个神秘的语言学运动,就是斯拉帕爸爸参与的那个,其中很多人都相信印度瑜伽文化和印度教与古俄罗斯异教文化一脉相承,有些人甚至相信印地语起源于俄罗斯,其中蕴含的那些智慧也都是古俄罗斯智慧,只不过在俄国被遗失了,却在印度得以保全。 事实上,因为俄语和印地语同属印欧语系,我们确实有些相似的词汇和概念…… 哦对了,我知道还有两个俄罗斯音乐人在中国挺受欢迎的,就是 Mummiy Troll 和 Vitas 维塔斯。 BIE:我知道你喜欢噪音,那你觉得如今俄罗斯的主流音乐怎么样?和噪音音乐相比呢?
尼基塔:俄罗斯的主流音乐是非常多元的,有几个主要流派。 当中最大的一个流派当然还是 Hip Hop,而其中最火的那些音乐人都以低俗著称,以一种比美国那边的嘻哈文化更极端、更狂野、更性感的方式。 可以听听这些:Morgenshtern, Kizaru, Oxxxymiron, OG Buda…… 目前还出现了一股女性嘻哈音乐人的潮流,其中最有名的是 Maybe Baby 和 Instasamka。 此外还有很多指向不同年龄层的多种分支流派。其中一个很有意思的流派叫 kaljan-rap,或 shisha-rap,指的是一种可以完美适配水烟吧环境的浪漫流行说唱音乐。这种音乐受高加索文化的影响,有一种俄罗斯南部的氛围。(例如:miyagi endshpil) 我们还有一种非常特别,同时很流行的音乐风格,俄罗斯香颂(Russian Shanson)。这种风格的歌通常都以犯罪为背景,其中最典型的歌曲通常是从一个被押送监狱的囚犯说起,歌唱的则是这个亡命之徒的冒险之旅。这种歌可流行了,你在哪儿都能听到,特别是在俄罗斯小城市的公交车和出租车上…… 尼基塔:地下音乐在俄罗斯是非常多元和强劲的。但鉴于我已经搬离俄罗斯有 8 年之久了,我已经有点失去对这个场景的概念了,毕竟一切都在变。 然而,那些华丽丽的场馆终究还是不存在于地下的。这里的一切都是为爱发电的,一切都是不确定的。俄罗斯地下场景中最重要的推力是那些为怪异音乐而设的露天音乐节,其中最有名的是 Solar Systo Togathering,以 Psy-trance 风格的音乐为主,但也包含了其他各种电子音乐流派。 斯拉帕爸爸在其中一个怪人音乐节演出的情况,电影里也有录像,真的很疯 |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也时常有地下音乐演出。在这种大城市里很容易找到一个演出场所并组织起一切,所以这些城市总是充满了疯狂的声音。 可以确定的是 —— 工业音乐(Industrial Music)、暗黑氛围音乐(Dark Ambient music)和所有真正暗黑极端的音乐风格,都如群星闪耀在俄罗斯的各大城市里。几乎在俄罗斯的每个角落,你能都找到疯狂的乐队在做疯狂的事。很多欧洲的工业音乐人,比如 Coil、Throbbing Gristle 和 Deutsch Nepal,历来他们的粉丝都是俄罗斯人最多。当然这些在大众层面上都是不可见的,但即使像我生长在哈巴罗夫斯克,一个俄罗斯远东小城,也能遇到把我引向噪音音乐和工业音乐世界的人。 之后我又知道了 Merzbow,这个世界上最有名的噪音艺术家,1988 年在苏联做了他在日本之外的第一场演出……而且就在我老家。嘿,我就出生在 1988 年的哈巴罗夫斯克呀!我确信他的那场演出让我和噪音的世界有了连结,而在我出生时一定就已经有噪音在我的小脑子里了! BIE:你们给自己的工作室起名叫“Schizoproletariat”,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它对你们意味着什么?
尼基塔:“Schizoproletariat”这个名字是我从一个叫 Alexander Sekatsky 的人那儿偷的,他是个住在圣彼得堡的当代哲学家。他用这个词来描述那些在做不同寻常的、疯狂的、和超自然相关的事情的创意者们,如艺术家、演员、作家、诗人之类,所有为疯狂之事着迷而做着赚不到钱的事的人都包括在内。 他用 schizoproletariat 来形容一整个被资本主义排除在外的社会阶层。 我们非常喜欢这个词,因为它代表了我们的价值观 —— 我们做这个不是为了赚钱,事实恰恰相反。我们学习如何用特定的方式去赚钱,然后我们才能在另外做些有创意的傻事,并且尽可能地去帮助更多的 Schizoproletariat。 Schizoproletariat 不止是一个品牌,也是一场没有边界的运动。任何人都能说自己是一个 Schizoproletariat,只要 ta 相信疯狂和自由创造(Free Creation)的价值,并且准备好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创作中去!(编者os:俄罗斯艺术家算是真正参透了雷锋精神……) 当然,斯拉帕爸爸正是 Schizoproletariat 中的先锋。 Schizoproletariat 公司的 logo 尼基塔:目前,由于康斯坦丁仍旧住在圣彼得堡,而我住在巴黎,我们目前并没有一起拍电影的计划。 当然,我们也在探索新的可能性。下一步会是更国际化的行动,比如投入欧洲的先锋艺术世界,因为我就住在这里。 《斯拉帕爸爸》是是我们的处女作,为我们打开了很多机遇的大门。直到成片 2 年后的今天,我仍旧忙于规划这部电影在世界各地的放映,约见一些业界的朋友,联络各大电影节,去见不同的艺术家和音乐人,花时间和他们在一起并学习新的东西。 这部电影还是获得了一些成就的 —— 在俄罗斯,电影在我们当地的主流在线视频流媒体,Yandex(类似于俄罗斯谷歌)旗下的 Kinopoisk (类似于俄罗斯网飞)上面公映,并且通过种子文件和社交媒体进行传播,我们因此得以认识了一些艺术圈的人。 战争爆发以来,很多俄罗斯的创意工作者都搬去欧洲了。现在我们和一群住在巴黎的俄罗斯创意工作者也在努力探索着我们能做的事。 我们希望能挖掘到还不为人所知的那些事,然后为人类和艺术史做记录。我们相信这是极其重要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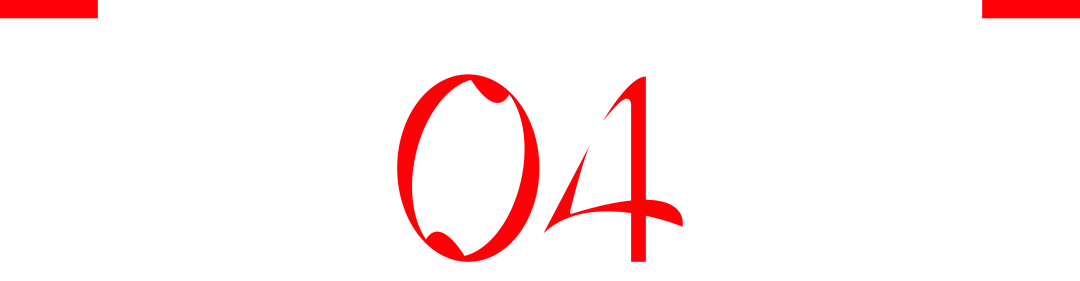 跟俄罗斯朋友聊聊中国尼基塔:首先 —— 为什么不?我们是最亲近的邻居啊。我生长在哈巴罗夫斯克,黑龙江边上,跨过江就是中国。 我对中国有特殊的情结。在地理上,我老家到北京的距离可比到莫斯科要近 4 倍…… 对我们这一辈来说,中国文化和我们关联最深的地方其实是中国的茶文化,甚至有段时间连我们这儿的说唱大咖都在吹捧传统的功夫茶。 很多我认识的艺术家、演员,还有那些创意工作者们,他们在从事高强度创意工作时,都超爱喝普洱茶。如果你非要一个俄罗斯人在普洱茶和咖啡中间做选择,大部分人都会选普洱的。 而且不仅仅是茶本身,还有茶的美学也吸引着我们,比如茶盘、茶壶、茶杯,还有喝慢茶聊大天的文化。顺便说下,我就是这么追到我老婆的:通过给她展示茶道和弄些尖儿货中国茶来喝。之前去北京的时候,我们直接去马连道茶城买了 5 公斤的茶叶带回去。 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就是中国的电子元件。目前中国工程技术的发展程度,对我们俄罗斯人来说是具有启发性的。从用于 DIY 的电子元件到各类我们能找到的零部件,我们已经无法想象一个没有中国的电子世界了。正好我们这部电影也是关于自己制作电子配件(合成器)的。所以如果有其他同样自己 DIY 电子零件的人能从斯拉帕爸爸的故事中获得一些共鸣和能量,那就太好啦! 还有就是,我在看完《北京朋克》这部电影之后,就爱上了中国地下文化的那股狠劲,他们向我展示了真正拥有「内心的自由」的人是什么样的,而这至今仍旧激励着我。只有在为自由抗争的前线,才有「先锋」可言。 我祈愿建立起中俄之间的沟通桥梁,特别是在地下场景中,因为我们对对方的地下文化都是完全不了解的……(编者:与此同时我们又是如此相似。)
跟俄罗斯朋友聊聊中国尼基塔:首先 —— 为什么不?我们是最亲近的邻居啊。我生长在哈巴罗夫斯克,黑龙江边上,跨过江就是中国。 我对中国有特殊的情结。在地理上,我老家到北京的距离可比到莫斯科要近 4 倍…… 对我们这一辈来说,中国文化和我们关联最深的地方其实是中国的茶文化,甚至有段时间连我们这儿的说唱大咖都在吹捧传统的功夫茶。 很多我认识的艺术家、演员,还有那些创意工作者们,他们在从事高强度创意工作时,都超爱喝普洱茶。如果你非要一个俄罗斯人在普洱茶和咖啡中间做选择,大部分人都会选普洱的。 而且不仅仅是茶本身,还有茶的美学也吸引着我们,比如茶盘、茶壶、茶杯,还有喝慢茶聊大天的文化。顺便说下,我就是这么追到我老婆的:通过给她展示茶道和弄些尖儿货中国茶来喝。之前去北京的时候,我们直接去马连道茶城买了 5 公斤的茶叶带回去。 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就是中国的电子元件。目前中国工程技术的发展程度,对我们俄罗斯人来说是具有启发性的。从用于 DIY 的电子元件到各类我们能找到的零部件,我们已经无法想象一个没有中国的电子世界了。正好我们这部电影也是关于自己制作电子配件(合成器)的。所以如果有其他同样自己 DIY 电子零件的人能从斯拉帕爸爸的故事中获得一些共鸣和能量,那就太好啦! 还有就是,我在看完《北京朋克》这部电影之后,就爱上了中国地下文化的那股狠劲,他们向我展示了真正拥有「内心的自由」的人是什么样的,而这至今仍旧激励着我。只有在为自由抗争的前线,才有「先锋」可言。 我祈愿建立起中俄之间的沟通桥梁,特别是在地下场景中,因为我们对对方的地下文化都是完全不了解的……(编者:与此同时我们又是如此相似。) BIE:你们对中国的噪音音乐或其他地下音乐有了解吗?
尼基塔:很不幸的是,除了《北京朋克》那个电影里讲的,我对这块完全不了解。但我很想知道!这也是我这么想在中国放映《斯拉帕爸爸》的原因之一 —— 无论如何,我们做这些都是为了去认识更多在这个场景中的人,然后通过这些人去了解文化的样貌,而我们已经准备好要向世界敞开怀抱了。 BIE:有没有哪个中国乐队或者音乐人是在俄罗斯比较有名的?你们有喜欢的中国音乐人吗?
尼基塔: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能进入俄罗斯流行文化的中国元素,要么就是我孤陋寡闻了。 说到中国的音乐,就会想到在演奏上人才辈出的古典乐(小提琴和钢琴),要么就是中国传统民乐。另外,藏族音乐在俄罗斯也为人所知。 一是因为我们都对佛教美学很感兴趣,藏族音乐就逐渐从“灵性”圈子里传播开来。假如你去练了一次瑜伽,很可能就已经听过一些藏族音乐了。当然,只有少数人会真的去钻研它,不过也不乏一些很火的曲子,比如这首:Om Mani Padme Hum - Original Extended Version(请自行 YouTube 搜索) 第二种解释可能是由于俄罗斯很多信仰佛教的地区也有跟藏族音乐很类似的音乐形式。 BIE:你们怎么知道 BIE 的?为什么找到我们作为电影的首发平台?
尼基塔:当我在斯德哥尔摩的 Spotify 工作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中国哥们,我跟他聊了我这个噪音项目。他无意中说起:“哇,你知道吗,我在北京的时候有个特喜欢噪音的同事,他也办办演出什么的,你应该认识认识他!” 我就这样认识了朱文博。他很快也表示出对这个项目的兴趣,然后帮我做了电影的中文字幕,还帮忙疏通渠道,找了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武汉的活动主办方。 于是我想,我们得把中俄文化交流这事认真提上日程了。不止为了这个电影,我也想更深入中国的场景,没准哪天我就去拍部《中国噪音》呢。 我喜欢在意外之地发现意外之事,然后让别人也意外一下。西方人不了解中国的地下文化,他们就想当然地认为好像它不存在一样,也因此对中国也有了非常片面的印象,这真令人遗憾。 后来,朱文博给我介绍了 BIE 这个平台。我用翻译器看了一些你们的文章,感觉非常了不起。网页的设计和引擎做的都太棒了(作为一个工程师我都感动了),但更主要的还是内容 —— 哇哦,你们选题都太潮了,就连西方都没你们时髦的。 我现在都跟西方的朋友说,你们知道中国还有个流行的网络媒体,会为残疾人的性权益撰文立说吗?西方人总把 “包容性” 挂在嘴边,但我也没见着多少……而 BIE 打破了我们对中国的所有偏见。能出现在你们这样独特的平台上,光是想到这件事就让我们感到骄傲了。 我们期待着在中国能有人在看完《斯拉帕爸爸》这部电影之后,受到某种鼓舞,并带着这种鼓舞去真的自己开始做些什么 —— 比如做个疯狂的合成器,一场打破常规的演出,一个艺术作品等等…… 但,既然是梦想嘛,我最大的梦想还是能通过这个项目,开启一段中俄之间沟通共演的乐章,在不同场景下相互交流,共同举办活动,甚至是做些跨国的音乐节。 比如做个横跨黑龙江的双国音乐节怎么样?想象在江的两边,噪音演出同时上演,用舞台上的激光灯作为信号,挺好。
我们将在本周末和下周三,在上海、宁波、阳朔举办三场《斯拉帕爸爸》的线下放映活动。具体的放映信息及报名详情都在今天的次条内容。映后还能跟导演本人线上聊天,名额不多就是了。我们还带了点 BIE 的周边准备在现场免费送给大家, 欢迎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