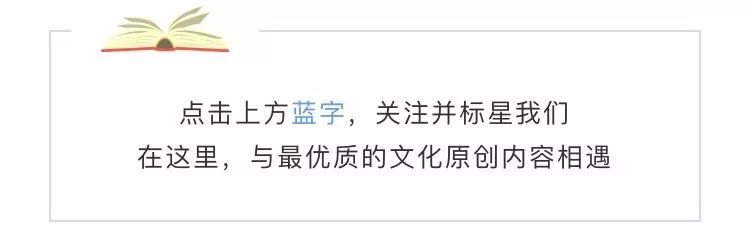

051期主持人 | 尹清露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独居人群增加,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无论是猫猫狗狗,还是时下流行的蜜袋鼬和鹦鹉,宠物给人带来了许多陪伴,也与我们建立起深刻的情感联结。小时候读《我在雨中等你》《忠犬八公》的故事时深受感动,并开始想象拥有属于自己的小狗,得偿所愿之后,我家的小狗每晚趴在床前睡觉,我白天带它出门遛弯,这种为另一个生命负责、逐渐形成的信赖关系想必是养狗人的共同经验。
但是人宠关系并不是毫无问题,有时,这些想象更多是人类在希求来自动物的治愈,却可能忽视了动物自身的视角。就像地理学家段义孚在《制造宠物:支配与感情》中提出的,对宠物的宠爱和权力控制有时是一体两面的,“宠物必须学会静止不动……要学会的一种最重要的招数是立即服从‘坐着’和‘卧倒’的命令。” 这也显示出人对待动物时的某些观念,比起人类,动物仍然是低一级别的生命。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同时,在近两年来,国内商业宠物克隆服务的火热也牵扯出了深层的伦理问题,这种行为已经伤害到了供卵的母猫,它们被长年累月关在笼子里,似乎活着的意义就是成全别人家死去的宠物。这也促使我们反思:对于宠物的爱,是否能够等同于对动物的关怀?倡导动物解放的活动家彼得·辛格显然不认同这一观点,我们此前的采访已经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所有动物都应该是平等的,用作食物的动物的问题,显然比宠物问题更重要。
我们一起聊了聊养宠物的经历,以及随之而来的思考——除了“宠爱”和“控制”,还可以怎样想象我们与宠物以及动物们的关系?
潘文捷:小时候亲戚把刚孵出的小鸡放到我家暂住几天。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小鸡!在散发热量的巨型黄色暖光灯照明下,它们在几张大报纸上走来走去,鹅黄色的,毛绒绒的,不停地啾啾啾叽叽叽!我哀求爸爸把它们养在家里,当然是惨遭拒绝。小鸡再可爱,也是用来吃的,不是宠物。小鸡和小猫有什么差别呢?人类是一种感情用事、不讲逻辑的生物,吃鸡就心安理得,吃猫你会被网友批评到下地狱。人类也按照自己的喜好区分害虫、益虫,凡是对自己有利的就可以讴歌赞美,不利的就要赶尽杀绝,这根本毫无道理,因为也许那些虫子早就在我们还是猿猴捶胸顿足嗷嗷叫的时候就称霸地球了。对宠物的区别对待让我想到到了上学时选举班干部,有个同学说选某人的理由是他帮我拿过东西,所以他是好人,所以他应该当选。我们真的该好好看看自己千疮百孔的逻辑。林子人:我从来没有养过宠物,小时候是爸妈不允许(现在偶尔和他们聊到“好想养宠物啊”,他们也是一脸嫌弃,“你有这闲心不如早点生娃!”),独立生活后一度非常想养一只猫,我家附近的商场里有一家宠物店,我和先生每次路过都会贴着宠物店的玻璃窗看很久各种小猫咪,直到内心被柔情填得满满当当才依依不舍地离开,我还关注了领养流浪猫的机构,读了养猫科普书。但因为种种顾虑我们迟迟没有展开行动,比如房东不允许、疫情期间充满不确定性担心照顾不好“毛孩子”等等。于是我退而求其次,用其他方式“吸猫”。前几天看了日本漫画家Kyuryu Z的《与猫共度的夜晚》,漫画记录了他与宠物猫丘尔嘉的种种趣事。猫可真是一种神奇的动物啊,我才知道猫的舌头上有倒刺(事实上猫科动物普遍舌头上有倒刺,这能帮助它们更好地咀嚼消化食物),白天和夜晚瞳孔的形状会改变,身体柔韧性强得惊人,而且不喜欢被人触碰须须。漫画书的书腰上有这么一句推荐语:“万千‘铲屎官’的简单愿望:结束疲惫的一天回到家中,整晚跟猫咪腻在一起。”我想着,如果我也有一只古灵精怪、我行我素但又无比依赖自己的猫,我肯定也会想一直和它腻在一起的。

《与猫共度的夜晚》
[日] KYURYUZ 著 谭晓莹/潘郁灵 译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22
叶青:曾经和前室友一起养了两年多的猫,是一只名叫小咪的黑色长毛猫。接回来的第一天我非常兴奋,我妈不喜欢小动物,所以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养过宠物,现在家里终于有猫了!但现实与想象相差甚远。短视频中的猫咪温顺可爱,随便摸随便抱,还会撒娇,有的还会安慰主人。真正养猫以后才发现都是假的(怒取关一堆摆拍萌宠号)。猫是非常独立的生物,大多数猫咪并不喜欢被人类抱在怀里,因为它们会失去安全感。冬天猫喜欢往人怀里钻,不是因为喜欢你,单纯是为了取暖,冲你喵喵叫大多数时候也不是在向你撒娇,只是饿了在索要食物。你会发现养猫其实和养小婴儿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他们都会半夜闹着要吃的(或是要你陪玩),都会不可避免地在你的床单上留下一些液体,而你只能无怨无悔地跟在后面铲屎铲尿,并且他们还不会领情,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左:几个月大的小咪;右:两岁多的小咪
最让我崩溃和后怕的,是有一次小咪上厕所没有断干净,屁股上粘了一坨排泄物——相信所有养长毛猫的人都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她大概也急了,开始屁股朝地满屋子蹭,我改完稿子出来一看,差点当场晕倒。当下特别生气,抓小咪去洗澡的时候动作有些粗鲁,她显然吓坏了,清理时应激反应非常强烈,她越反抗我也就更恼火——明明是你的错,你还不配合我!
事后我被自己的愤怒吓到了,为什么我觉得我有冲她发火的权利?我是不是把自己的坏情绪因为这件事投射在了她身上?可明明是我们自己选择养猫,她只是一只猫,她能懂什么呢?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变成了我最讨厌的“中国式家长”,我没有把她当作一个平等的个体对待,而是下意识地把她当成了我的所有物。因为我养育她,所以她就得听话;因为我这么做是为了她好,所以她就得照办。这种思维实在可怕,事后我试图和小咪道歉,但她当然听不懂,并且有些记仇,直到我用她最爱的零食贿赂她,她才消气。
养猫的两年时间里,类似事情时常发生,但现在回头看我一点都不后悔,和小动物近距离地相处后我才更懂得如何尊重它们。虽然经常要拖地洗床单,但看到小咪躺在沙发上,毫不设防地露出最柔软的腹部,睡得呼呼作响,就觉得这一切都值得,不就是地板和床单吗,我拖!我洗!
尹清露:我也养过猫,只不过是帮别人短暂寄养。这只小猫名叫老换,它在家中来去自由,应该过得还算快活。某天我和男朋友在楼下大厅又发现了一只蜷缩在角落的小灰猫,是从很高的楼上掉下来的,一只腿瘸了,还伴有很严重的应激反应,看着特别可怜。我们起初想要收养,但无奈老换对它充满敌意,遇到它就又怂又凶地弓起后背,陷入一山不容二猫的境地,我们僵持了几天后只好放弃,另外再找领养的人家。
所以,在养宠物这件事上,并不是自己有爱心就可以无限收留人家,比如老换也有它的脾气和性格、有领地意识。就像叶青说的,猫不是人的所有物,人和猫需要时不时坐下来谈判并尝试彼此理解,这很难,但也因为如此,才能让我们反思人与动物如何在同一方天地中更好地相处。
徐鲁青:大多数动物保护界人士都提倡以“同伴动物”代替“宠物”这个词,因为“宠物”本身就包含了物化的色彩。很多人也建议不用“宝宝”“崽崽”等拟人幼稚化的说法称呼同伴动物,避免将它们简单化,塑造成天真幼稚的形象。我之前采访动物文学研究者黄宗洁的时候,她观察到,在现代社会里,人对宠物的“人格化”与“物化”不是此消彼长,而是呈同时并进的状态,宠物虽然被比喻为人类的“孩子”“朋友”,但是也越发成为人类不断干预的“产品”。现在看似宠物权利高涨,宠物能享受高级玩具、服装,甚至按摩、美容、生日派对等服务,甚至被很多人讥讽“人不如狗”,但背后大多只是为满足人的欲望。把狗染成各种各样的颜色,表面上看好像是为它们美容,实际上是动物们更加被物化的表现,不代表动物权利的真正提升。人类在挑选自己未来宠物时,总会倾向于纯种血统,市面上有大大小小的猫狗血统贴牌认证比赛。很多机构会人为干预,让宠物猫狗的眼睛更大、腿更短,打造成无辜可爱的形象,但一旦进入野外,离开了人类,这类体型会让它们非常难以存活。不仅如此,很多改造过程本身也让动物们痛不欲生。以宠物狗作为例子,几乎所有的纯种犬都是基于人类审美被形塑过的——骑士查理王猎犬的头骨被人类刻意调小,但因为大脑来不及跟上骨骼变化,只能被迫塞在过小的头骨中,可以想象一下40码的脚塞在36码鞋里一辈子的感觉;德国狼犬被人类改造后驱角度的体型,造成了后腿关节的问题;巴哥的鼻子形状改造也让它们一生患有慢性呼吸道疾病。这一切如果放在人类身上,谁都会说是升级版法西斯,那放在所谓“人类的朋友”身上为什么就可以?狗的“血统”也成为了流行文化的一种,这导致某些种类的狗会突然大受欢迎,然后快速被“淘汰”,比如现在上海时尚街拍里,灵缇和阿富汗犬都站在凹造型的鄙视链顶端,很多网红为了拍照会特意养这些品类,十多年前“流行”(流行这个词也有非常浓重的物化色彩)的泰迪犬现在则面临时尚浪潮的淘汰。这种市场流行趋势让很多狗遭到遗弃,如果只是无生命的商品,不要它们了就只是浪费和环保问题,但对于依赖人类的生命来说,问题就要复杂得多。黄宗洁还批评过很多主流的动物叙事,比如《忠犬八公》中典型的忠犬护主的故事,狗的忠实与牺牲奉献形象似乎是人狗关系当中最核心的标志,也被用来鼓励民众爱护狗狗,但是为什么动物一定要“奉献”或“伟大”才值得珍惜呢?想象一下我们亲密的人类同伴们,无论是朋友、亲人还是爱人,互动关系远比爱与控制这两种极端情况复杂得多,一旦放在动物身上,我们对关系的理解好像就变狭隘了。姜妍:我在看鲁青做的段义孚那篇《制造宠物:支配与感情》书摘时也蛮有感触的。很多时候人类对宠物的情感里包含了许多控制与想象,落实在行为上是一种选择与塑造。比如我记得以前在路上经常会碰见的是京巴狗,现在几乎看不到有人遛京巴了,取而代之的可能是柯基和柴犬,那我不免会想,京巴去了哪里?不被人类喜爱以后,它们是以怎样的方式在减少数量?我希望背后真实的情况不要太悲惨。另一方面,我觉得没办法要求每个人都喜爱动物,但即便不喜爱,是不是也可以做到不伤害、不介入、不干涉,让动物也可以和我们共享一片天地?比如流浪猫的平均寿命是远低于家猫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死因是肾衰竭,因为它们很难喝到干净的水,所以会有一些爱猫人在隐蔽的地方,比如墙角、树叶下放置小铝罐,定期更换干净的水源,这对流浪猫来说真的很重要,但是现实里总会有人把这些小水罐挪走掀翻。我很喜欢清晨大批游客还没进入天坛时那种人和动物的关系,就是大家共享一片空间,彼此不互相介入。晨练的人蛮习惯身边有松鼠跑来跑去,或是野猫蹲在草丛中晒太阳,相对于游客来说较少会想要去逗弄或驱赶。在这种状态里,人可以观察到很多动物更自然的反应与行为,比如会看到小松鼠搂着妈妈的脖子被带到树上,妈妈自己下来,鼓励小松鼠学会下树,比如乌鸦之间的反哺等等。当然也不是所有画面都很美好,也会遇见野猫捕食松鼠,或是鸟儿擦着地面飞过,地面只剩下一个空空的蜗牛壳。尹清露:之前读书的时候,我接触过学者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伴侣种”概念,大意是重新想象人与其他物种(如宠物狗)的关系,二者不应该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而是在和彼此的相遇中互相改变的关系。另一位人类学者爱德华多·康(Eduardo Kohn)也在民族志《How Forests Think》中提到,人类和动物的交流系统是全然不同的,人类习惯通过象征符号来沟通,而动物们是通过索引(index)——也就是事物的物理性关联——来达成交流的。当狗狗看到一颗树倒下,它就能感受到危险临近;如果狗狗咬了人的拖鞋,让它看到咬痕,它就知道自己八成是做错事了。我们想当然地以为人类的系统更高级,但这两类系统并没有高下之分,如果人可以去观察和理解动物的交流系统(虽然这能在多大程度上达到还未可知),那我们是否就能去反思对动物的种种暴行,并且加以改变呢?上述的理论也可以用很朴素的想法来理解——不要把人类的欲念和偏好投射到动物身上,在理解物种差异之后,用更平等的姿态与之相处。姜妍提到天坛里人和动物之间互相尊重、互不介入,在我看来就是这样的一种实践吧。但遗憾的是,当我们将目光转向现实,当人的手触碰到动物,并为之赋予“可爱”“可怕”“恶心”等评判标准之后,权力关系就已经形成了。看到鲁青说的“改造动物”,不禁想起自己家养过的狗狗也被残忍地“改造”过。几年前我爸带回家一只活泼可爱的雪纳瑞,叫声十分沙哑,原来是因为前主人嫌吵,把它的声带割掉了。那句“人生来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对动物来说何尝不是如此,而且它们的困境往往是更尖锐、更根本的。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主持人:尹清露,编辑:黄月、尹清露,未经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