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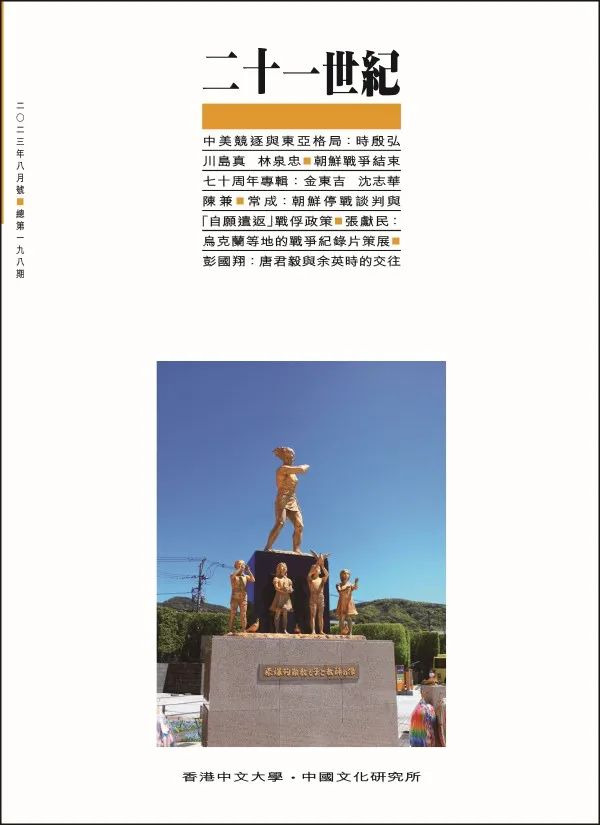
战争纪录片是一个古老的电影类型。电影胶片的现场性开始于1930年代中期西班牙内战、终结于1970年代中期越南战争末尾西贡的美国大使馆被攻陷的画面。
西班牙内战催生了两部截然不同的纪录片,一部来自布努埃尔(Luis Bunuel)的《无粮的土地》(Las Hurdes, 1933),它是千年 — 永恒存在的纪录式样与超现实主义对此的怀疑的结合,引来弗朗哥(Francisco Franco) 政权对巴黎放映此片的抗议;另一部是伊文思(Joris Ivens)的《西班牙的土地》(The Spanish Earth, 1937),它代表一个声音(voice),但也是战地摄影第一次出现,画面来自卡帕(Robert Capa,卡帕及同伴后来还发明了苏联用于拍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地摄影机),画外解说来自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等人。这两份「证词」来自共产党阵营;来自保皇党阵营的声音在纪录片经典中缺席,只以新闻短片的方式存在,就是经过大幅剪辑的画面和短促的声音。
1970 年代中期西贡的「陷落」(这个词本身反映着一个视角),在纪录片中也是单向叙述的,来自越南北方共产党阵营的声音缺失,与西班牙内战恰成强烈对比。它的强冲击例子有两个:一个是美国人拍摄的美军撤离西贡时大使馆楼顶、航空母舰上的直升飞机起降(这些记忆最近被美军撤离喀布尔时大量阿富汗人攀爬飞机的画面更新了),它也强烈影响了好莱坞科幻电影中的灾难或撤离的概念性画面/场面组织;另一个来自一位澳洲摄影师拍下的北越坦克撞倒美国大使馆围墙的画面,它是没有声音的, 而且是从使馆内往外墙方向拍摄,当时北越军队可能已经了解到美国人的撤退或南越军队的消失,处在火力静默中,否则这位摄影师和那一卷胶片不可能存活下来。电影胶片时代的末尾是16毫米正片拍摄,视觉效果偏暖色的日光,光线反差小,没有同期声(拍摄时的同期录音)。1898年出生、跨越了世代的伊文思在此前于北越拍摄的《北纬17度》(17th Parallel: Vietnam in War, 1968)使用了同期声(有关战争的后方、高射炮兵群的声音)录制方法。
 伊文思的《北纬17度》使用了同期声录制方法(资料图片)
伊文思的《北纬17度》使用了同期声录制方法(资料图片)
越战末尾的战地直击,直到第一次海湾战争(1990-1991)时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实时转播才有所突破,或者说CNN改变了纪录片的存在必要,战地摄影脱离了电影的范畴、脱离了图片摄影的范畴,归属于电视和卫星传输。这又要等待Tik Tok的出现才又有改变,此改变从传统角度看是声音层面的,就是战争影像的个人化、给予了个人一个声音。
纪录片缺位原因之一是胜利者的自信,实体以疆界的方式存在,这也暗示弗朗哥、北越等胜利者将纪录影像归属于一种阐释:现实就是现实,现实并不需要对它的复刻。此时图像进入皮尔斯(Charles Peirce)和尼科尔斯(Bill Nichols)的阐释范畴,就是索引(index)性质,中文也曾翻译为表征或指涉。(1)
我们似乎面临纪录片图像生产的三重境地:第一重是未剪辑的素材,以前它没有同期声,现在的复刻性质在于它还没有加字幕、没有配上拍摄者的画外音、没有先期观众的「弹幕」(对影片即时发布评论),就是对原始素材不仅阐释为零,声音也接近零,这是复刻(2);它对应于艺术史中曾经的匿名性质。第二重是索引性质,就是将直接改为间接(直接电影 [direct cinema]的古老称谓此时显得回响悠长),同时使得素材作为语词/短句材料可以被重新发现和引用,从而成为被阐释的材料;目前电影的主流理论之作者论就在这一过程中,被解释为一个雕刻、折叠、探索等留下痕迹的动作(3)。第三重是彻底的符号化,目前的影像工作有两个倾向符合这一标准,一个是「表情包」,另一个是比新闻短片更短促的视觉片段的无限重复,例如火箭发射或核弹爆炸镜头的无限复制和无限播放,这是影像语词的固化,类似古代史诗中反覆回到太阳、沙丘、宫殿、海洋等超级词汇。它大体对应于实体和疆界的胜利者对图像的兴趣寡淡,胜利者只重复口号(4)。
二战以降,武装冲突类的纪录片在渡过玛格南图片社(Magnum Photos) 模式的战地摄影阶段之后,与文化外交联姻了(5)。文化外交本身,经历了宣讲式的「岁月静好」阶段之后(影像的「三个世界」理论可以是这样的: 定制影片不用说「我很棒」就是第一世界,或称文化发达国家;定制影片必须说「我很棒」就是第二世界,或称文化发展中国家;不定制影片就是第三世界,或称文化欠发达国家), 在环境污染、文明差异的张力、资源短缺、「热冲突」等几者之间徘徊。战争问题上,大体分为「我们在干些什么」和「他们在干些什么」两类。巴以冲突题材的纪录片产量最大,反复展现「我们到底在干什么」;乌克兰疆界内的武装冲突,在纪录片领域内(电影和电视领域内、不包括网络短视频),大体是「他们到底在干什么」的类型。中间地带的例子有叙利亚,它包括这两个大类。乌克兰话题在这方面「我」和「我们」缺失的原因是由于他们都上了短视频自媒体。这也显出纪录片需要资源,包括拍摄的资金、充裕的拍摄和剪辑时间、保持相对客观态度的空间距离和思想距离、播放的渠道等。文化外交的崛起缘于经济和军事的有限性,或者说殖民主义的侵略排序是军事、经济、文化。典型的有英国和法国两个模式:英式的是「你爱怎样就怎样」,就是不管,假设殖民者没有破坏当地的文化;香港曾经基本是这个模式。法式的是「我爱怎样你也得怎样」,假设殖民之前当地没有文化。按侵略时间顺序的这三者,军事的载体是枪,经济的载体是数字,文化的载体是语言。军事和文化都不可以内循环,所以军事行动的目的是促进经济,如果经济自身循环不够,还需要文化来帮助销售。香港主要从事贸易,第一个环节与第三个环节都很弱。以俄罗斯为例,其遭受诟病的原因之一是这个外向型的国族在军事行动之后,一向没有经济和文化跟上。本文更需要讨论的是其图像生产的内卷——不是为了向境外传播,而是让本国国民坚定信念,即前述的「第二世界」。一些幅员辽阔、人口复杂的国族,图像生产往往如此。反例是巴以,土地太狭小、人口有限,所以图像生产更多是为了让他者理解一点「我们在干些什么」。本来这种图像生产的内卷,乌克兰与俄罗斯差不多,乌克兰也可以算是「幅员辽阔、人口复杂」,但2022年2月俄军的「特别军事行动」促使乌克兰采取了新的走向。这并不是说俄罗斯在图像生产方面什么都不做,俄罗斯联邦文化部资助像《远东各各他》(Far Eastern Golgotha, 2021)这样的女性导演纪录片处女作:全片致力于揭露地方政权的腐败,以及俄罗斯人某种意义上的整体愚昧。这证明俄罗斯的文化政策越过了「岁月静好」的阶段,允许批判现实主义的存在。但这还不够,顶多能证明俄罗斯回到了十九世纪沙皇时期那种批判现实也不至于丢命的境况。它还应该向更广泛的拍摄敞开,同时也应实践更广泛的拍摄。这两者,等军事行动已经开展就太晚了。普京(Vladimir Putin)政权允许过对1930年代乌克兰饥荒的反映、反思和纪录片放映。它的「开放」也引来了一些文化发达国家和地区对此问题的进一步讨论,这些讨论让俄罗斯/俄罗斯人很不痛快,经典争议问题有到底死了多少人、饥荒延续了一个春天还是两个春天;尖端提问有如果斯大林不阻止托洛斯基(Leon Trotsky),是否饥荒还会恶化、此实践是否已在以色列复活,等等。这些讨论不可能让人舒服,万一觉得自己是当事人的后代,更不可能舒服。俄罗斯在图像生产上的态度、方式和形成的事实,非常接近1930年代的弗朗哥政权和1970年代的北越,就是漠视。漠视的根源之一是资源短缺,还有图像的理念、媒体的地位等原因。比如图像既不应依附神权、也不应附属于国家权力,国家权力在把媒体从经济寡头手中夺回来的时候如何把它「还给人民」。媒体在俄罗斯有一定自由度,但还远远不够。这就形成接近弗朗哥或胡志明的事态:普京变成了表情包,全民依赖这个形象,或俄罗斯国族塑造全俄罗斯的形象就是一组表情包。它取消了素材的证词价值、取消了图像索引性质中可以被讨论的部分,只留下了符号和象征。乌克兰在影像生产上并不是一个诱人的区域,它似乎过于平板,不曾深刻检讨它在排犹历史中的核心地位。它并不努力与外界增加勾联,其语言与俄语的差别让外人莫名其妙(至今有些高校仍大量使用俄语教学),乌克兰在美国人所写的历史书中成为东欧国族主体性变幻的例子。它是全球化中的「中西部」,原野、种植、宽阔的河流、战争的历史等,使得它像是世界各国的「背景板」,就是别人的故事在它的前景发生,它本身并没有故事。以乌克兰为背景的别人的故事的一个例子是:侨居加拿大的伊朗人帕哈米(Shahin Parhami,因为共产党身份在伊斯兰革命期间被迫流亡)回到伊朗,拍摄一个青年音乐家致力于保存西南部游牧民族Qashdai人的传统音乐,他在基辅留学、有一个胖胖的乌克兰女友在努力地学习意大利歌剧女高音。这部纪录片叫《阿明》(Amin, 2010,又译《阿敏的乐章》),拍得很不错,而且有中文版,音乐很动听。一位乌克兰女性编导拍摄的《雨永不停歇》(This Rain Will Never Stop, 2020)与之类似。在这部诗意的纪录片中,她以叙利亚青年男性为主角,把叙利亚的段落放在最后,而且是从库尔德人的角度切入的;影片前段并没有聚焦叙利亚的俄军,而是直接进入莫斯科街头的阅兵场面,中段部分是乌克兰的「和平」生活——婚姻、餐饮、朗诵会等。影片标题来自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和普雷维尔(Jacques Prévert)的诗歌,难说他们谁抄袭谁;因布莱希特的诗歌经常被引用,在此引用普雷维尔《芭芭拉》(Barbara)一诗的片段:
和平并不足够让人幸福,战争足够让人不快乐。
乌克兰东部在2008、2014年后一直在局部的动荡中。欧洲的文化外交和影像「扶贫」延伸到这里,经常由一些几乎没有过殖民历史的「小国」操作,如丹麦、瑞典、挪威等。最近几年,波兰、拉脱维亚等国也加入了联合制作局部武装冲突题材纪录片的行列。亚洲范围内,西亚、波斯湾地区对此议题更有兴趣,可能因为地区冲突对它们是近切的事,无论从空间上还是时间上。东亚承平日久,似乎群体心理上与此隔断较深。西亚参与出品或制作此类纪录片的常有卡塔尔、阿联酋等,也是小国;若论传统,西亚的科威特、黎巴嫩似乎更应该参与叙利亚、阿富汗、乌克兰等地区冲突的纪录片制作——这两个国家到底还是被最近几十年的侵略蹂躏过头了,无法恢复的表征之一就是难以他顾。乌东纪录片常常反映一些人道话题。当地一个小镇还有人试图维持一个乐队、定期组织电影放映等。苏联解体前,苏维埃体系中曾有文化宫,后来部分得以保持,并相对活跃。如果改造成影迷俱乐部,放映已经搬走的邻居的家庭录影,挺让人睹物伤神。女性和儿童是一个重要话题,毕竟大家都同意孩子是无辜的,如果几年被迫无法上学,丧失掉的是什么,恐怕孩子自己到更大的时候才能领会一些。《远方的狗吠声》(The Distant Barking of Dogs, 2017)就是这样一部纪录片,主角为十岁左右的乌克兰男孩,纪录片工作者跟拍了一年。该男孩的日常是跟随两位同村男性少年去野外躺在草地上看「烟花」——冲突中敌对双方互相发射的炮弹在空中的划痕。战乱之下,村中已经十室九空了。影片中的人道主义是延续的,2022年战端重启,制片人和导演几度想办法让这些男孩彻底离开那个危险的顿涅茨克(Donetsk)村庄,后来他们在奶奶的带领下离开。此片并不涉及该村的成年人是否有俄罗斯认同、战乱中哪一方军人更恶劣,主题只是「这一另类的童年可能很特别,但还是最好不要这样」的温柔提醒。《德涅斯特河畔》(Transnistra, 2019)有关德左地区(德涅斯特河左岸)。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是摩尔多瓦的一个地方行政区,毗邻乌克兰。摩尔多瓦语与罗马尼亚语的关系有点像俄语与乌克兰语的关系,外人可能弄混,但其实并不相通。1991年摩尔多瓦独立之后曾数次有与罗马尼亚合并的传言,但均被否认了。德左传统上是俄罗斯族聚居地,斯大林晚期的「掺沙子」式民族融合时期才归入当时的加盟共和国摩尔达维亚。摩尔多瓦是传统农业国,我喝过两箱那里生产的葡萄酒,色味俱淳,只是不能喝到最下面,沉淀物不少,显示他们用的可能是一种很古老的过滤工艺。德左是全摩尔多瓦的工业集中区。2008年乌东冲突爆发后,这里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有人指责这批俄罗斯人阻碍了摩尔多瓦与罗马尼亚的合并,有人猜疑德左即将成为指向乌克兰西部的进攻策源地。摩尔多瓦作为一个中立国,拒绝任何外国军队的驻扎,全国军人不足万人,德左地区的俄罗斯族军人只有千人左右,不构成威胁,而且摩尔多瓦政府完全支持抵抗的乌克兰。但德左的尴尬一目了然:由于地区狭窄,人口失去了流动性,也形成了原材料和制成品长期无法流通的局面,工业不断萎缩,导致致命的人口流失,这里的人只有远走他乡;返回俄罗斯只是一个选项,但如果下黑海,终点是哪里?

此片中毫无故事,几个少年人在原野里无止境地游荡,去寻找另一个无所事事的少年,个别异性出现时也可以一起跳入河中畅游,去工业废墟「冒险」,议论没有答案的未来,想像长大之后的人生方向。他们最有仪式性的活动是集体的军装典礼,定期举行,伴有军乐,这个仪式替代了欧洲一般的周日宗教仪式,但性质是一样的:追思某种古代的圣贤和失乐园。此片继承了俄罗斯诗性电影最优秀的传统,也是欧洲非叙事、自由电影的杰作,人性附体、一片灵晕。东南欧电影在过去几年发展出一个亚类型,姑且称为「不良少年团伙暴力片」,目前还以短片为主,以虚构或非虚构的方式讲述混居的男女少年在混杂着金属和化学废料的郊野生活的内卷型暴力故事,如轮流尝试吸食毒品、团伙要求的投名状是烧死一条狗、无理由地抽签决定团伙某成员必须执行对自己的伤害等。影片以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为主,但也延伸到波兰等地。《德涅斯特河畔》可能受到此亚类型的影响,但它做出了一个和平主义的版本:世界虽然动荡和荒谬,未来完全缺位,但几个郊野中的少年并没有对自己或他人施以暴力。他们的不上学就是自由,恋情像风一样刮过。乌克兰纪录片的下一个阶段可能是跨民族的个人对个人的和解努力、军人放下屠刀之后的梦魇、基础公益的重建等。大型人道主义灾难纪录片在历史中的发展进程大体如此,它跟随社会和群体的节奏。我们为何对乌克兰感兴趣?以发现为目的的对远方的观看也是一种接近殖民主义的视角,可是完全内卷的审视又回到封建的一亩三分地。我们在殖民主义与封建的视角间切换,一度期望华语地区创立一个新模式?或花大钱就可以把自己从观看者的地位挣脱出去?被战争纪录片疗愈的主要是观看者,而不是经历战争的人。如何在心理上治疗战争亲历者,整个东亚都没什么经验,我们只是在等待经历了战争的那些人全部去世,如慰安妇。那么,至少我们可以做观看者,以微薄到不能再微薄的力量,让战地的人们知道有人在关注他们。如果对军人反感,那就看一些女性和儿童的纪录片吧。有时我也希望有人出来反驳这个推论。但事实相反,观众往往只是不看而已。这也涉及我个人以什么视角写作本文——应该是一个电影策展的视角,我的部分工作是把影像作品组织起来给观众看。比如我在2005年前后观看了巴以冲突的纪录片百部左右,从那时直到2015年左右观看了亚洲各地的纪录片几百部,中国内地的长短纪录片每年也能看到百部以上。看片的目的是经过过滤、筛选、排列、组织,使得影片能与观众见面。以前感谢前辈林旭东、同辈单万里等人,后来感谢年龄略小于我的左靖、刘智海、杜海滨、林立等人,我断续有机会在中国大陆和海外举办一些集中的或分散的放映,也有幸邀请过欧洲、美国、亚洲的数十位导演、艺术家、策展人到访中国。基于尊重对等的原则,我也在十多个国家举办过中国不同电影的专题展、回顾展或电影周。在网络的时代,坚持举办线下活动,非常吃力、不讨好;做的是类似文化外交的事情,但没有文化外交的实质,一切都以民间方式进行。时至今日,举办这些放映的巨大阻碍,彷彿就是它的意义的证据。电影策展工作有基础的分类,这些分类涉及地缘和民族分野,但它不排斥乃至需要一点理论,需要阐释和一丁点抽象化。影展是什么?就如同古代战争抢夺的是硬资源,如土地、人口、珠宝等,后来只是为了确立有疆界的实体、让对方不要侵入。影片或文化只是无疆界的实体,影展、书展等就是划定疆域。影像创作工作只能对巨大而深刻的创伤进行一些周边的心理治疗。我们需要这层疗愈,即使那些创伤似乎只发生在远方。(1)王迟指出;「尼科尔斯借用符号学家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 Peirce)的术语,将摄影影像视作一种索引符号,即承认影像与被拍摄物之间具有一种点对点的『物理性的』的对应关系。」参见王迟:〈译序:在纪实主义的阴影下——谈比尔.尼科尔斯纪录片理论在中国的接受〉,载尼科尔斯(Bill Nichols) 著,王迟译:《纪录片导论》,第三版(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20),页21。再者,皮尔斯当年区分的三个基础概念为象征(symbol)、索引(index)、符号(sign),三者在物体与物像的关系上分别象形、关联和抽象。尼科尔斯不大赞同复刻类的影像本体理论,故而使用「关联」作为纪录片的基本特征之一, 纪录片作为物像是物体的关联物,关联意味着间接关系,是分析的对象,如因果关系。(2)「复刻」的概念产生自电影史较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当时较多运用的概念之一是「拓片」(l’estampe)。它也来自早期图片摄影的阐释,当时部分评论阐释图片是物像的拓片,拓片的理念来自中国的碑文,也来自日本的浮世绘。「拓片」的概念在后来电影理论中退潮了。(3)「作者论」在本段落中至少可以有以下的解释:(1)在它彻底成立之前,电影的创作以集体或资本的名义在匿名状态中。(2)作者论有版权+劳动保护、文艺、名誉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在华语范围内一直没有实现,甚至共识也没有; 第二个方面就是本段尝试说明的、以浅度动作加工、对物像进行「索引」;第三个方面是指通俗文化中作者论已经替代了演员明星制,或者说现在的明星制围绕着导演。(4)这不仅是有关用语审慎,也牵涉片长的问题。所谓「话语即权力」指的是“discourse”,但在媒介的发展中它一直短小化,就是“slogan”——或者现在叫「标题党」。它以无限量复制、不知疲倦的播放为特点。(5)文化外交一直存在,如何成为了主流尚待研究。大报导是一个媒体格式,起源于古代的游记,伴随着整个大航海时代,文字未免带有殖民主义视角。大报导衰落的历史缘由之一是飞机的出现,或者说自从1967年最后的欧亚定期邮轮停止服务之后,大报导就走向了尾声。现在取而代之的是一般称为「深度调查」的媒体格式。▲▲▲
推广/合作/活动加微信号:directubeee
伊文思的《北纬17度》使用了同期声录制方法(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