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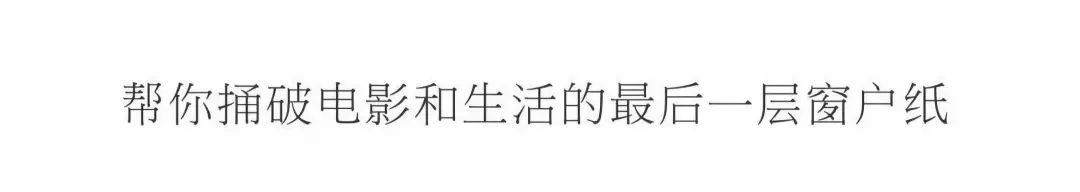
写在前面
距离上一次《隐入尘烟》正式破亿时我们的「再谈」,仅仅过去了20天。当时的我们还在感慨:一部文艺片居然能在上映62天,上线流媒体10天后,票房不降反增,一路逆袭连续多日拿下票房日冠,最终成功破亿。那时候的我们会说:无论你是否喜欢这部电影,你都没办法否认,这是中国电影史上一次绝无仅有的奇迹。
但这次微小的奇迹,就这样在20天以后,正式腰斩——就像它的片名那样,真正地隐入了尘世的烟云之中,不见踪影。原因我们无从得知,也不敢猜测,只是又听到了一些熟悉的叫好的声音,这些声音无外乎是对电影选择“现实题材”以及“负面事件”的争议。所以,我想改写一下上次为《隐入尘烟》写的第二篇稿子,小心翼翼地去反驳一些东西。看过那篇文的读者可能还记得,上一次聊《隐入尘烟》的时候,我在那篇文章的末尾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但一片土地上的人的精神觉醒,永远是要归因于他者的。在一些时刻,他者的负面性,恰恰让人类的精神得以存活。”“当我们将目光着眼于他人,开始跳脱开固守的世界以外,懂得去接受其他个体的负面性、从而懂得什么是承受痛苦的能力时,我们才开始真正有了精神。”这段的话重点其实就是第一句中提到的“他者的负面性”,它包含的就是所谓的“现实题材”以及“负面事件”,只不过这六个字回归到了最本质的东西,既他者所指的人,而非事件。漩涡中的人需要被注视着,这种注视是一种引导,引导着我们认识到它们以及他们的存在。而那些藏在礁石之下的漩涡,只有被看见、被长久地注视着时,才有唯一被救赎的可能,因为认识本身,就是一种救赎。当过去的我们讨论着《隐入尘烟》中的人物是否“有点太干净了”,讨论着这部片子中的视角是否过于刻板、太过局限的时候,至少在影院的我们,在那两个小时内,真正把目光转回了最初的大地和大地之上的人们。人有义务看见不同境遇中的眼泪,这是一种无关肤色、无关人种、更无关国别的,仅仅关乎人类朴素价值观的本能。如果将世界比喻为一座巨大的百货商店,那我们、及我们作为个体所代表的经历,则是这座店里满满当当的存在物。这些存在物或许令部分人感到陌生,又或者令部分人感到恐惧,但至少——那些情绪引发的一系列争论的前提,是我们的目光,至少真正停留过与注视过。而不是简单地消除一切他者的否定性——使得任何语言、任何表达方式都不许触碰“悲伤”这样的消极情绪。在上一次谈论《隐入尘烟》的票房奇迹时,我们曾经强调过一件事,即是这一次的票房推手与以往都大有不同——他们是抖音、快手,这一类常被我们描述为下沉市场的短视频平台里真实的用户。这些平台上的用户在《隐入尘烟》上线流媒体之后,自发开始做二次剪辑的短视频,正是这些看上去下沉、土气、浅显的短视频,开启了《隐入尘烟》真正的票房奇迹。这一次关于《隐入尘烟》的二创,我从短视频软件上看到最多的两种文案:另一种是:“全片没说苦,却苦出了天际;全片没说爱,却爱到了极致。”归纳下来无非是两个关键词:苦难,以及苦难下的爱情;对应到大众情绪,就是愤怒,以及感动。如果只是停留在这两个词里,我们或许也会纠结于这些受众群体,到底是真感动还是打卡式感动的偏见里。但显然,《隐入尘烟》这一次的票房,远不是击打出受众情绪就能完成的,它还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在短视频给予观众第一次进入影院的冲动后,它们还需要走出影院的人,自发的、接力般地让身边人买票。我们经常说,大众文化的传播一定是需要集体的认同性,是要求它一定是具有社会性的,我们无法否认的是,《隐入尘烟》中的某些议题切中了这种“社会性”。这种情况下,我们便无法在讨论中忽略,影片出现之前本身就存在的大众情绪。当下我们所面临的很大一部分情绪,在电影出现之前,就在努力寻找出口,《隐入尘烟》的出现或许只是给到了我们一次意外的情绪选择,一次流泪的机会,而这才是最重要的传播土壤。说《隐入尘烟》获得了观众,不如说是观众的情绪找到了《隐入尘烟》。那么在意识到情绪的来源之后,我们要去证明这种情绪是否是一种高高在上的俯瞰、是一种伪善,其实只需要去验证一个最重要的前提。我们正在共情的这部分群体也就是来自农村的人们本身,是否认同这种叙事?在写这篇文章以前,我抖音和快手的首页,都多次给我推荐了《隐入尘烟》的各类剪辑视频,在这些视频底下,我发现有两类评论颇多,一类是在说“拍得好,这拍的就是我们农村生活”,另一类在说的,却是我之前从未想过的一个视角——他们说《隐入尘烟》里,只有海清一个人是明星,其他都是素人,这真好。在《人物》对李睿珺的专访中,李睿珺提到,《隐入尘烟》的演员,几乎全是他老家所在的农村人。演老四的武仁林,是他的小姨父;运输粮食的那个老板是他的亲哥哥,他一直担任李睿珺的制片,同时也演戏;组织大家去开会、献熊猫血的村长是李睿珺的父亲;演贵英嫂子、提醒她去撒尿的,是李睿珺的母亲。这样一个草台班子,是从09年李睿珺拍《老驴头》开始的。这些年来,李睿珺拍了《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拍了《路过未来》,再到今年的《隐入尘烟》,花墙子村里的村民,从不相信李睿珺这样一个从小光着腚、露着肉在黄土地上奔跑的小孩儿真的会拍电影,到他入围釜山电影节、作品开始登上本地的新闻报刊后,他们才真正意识到李睿珺是一个可以拍电影的“导演”了。李睿珺说:“很多人突然意识到,假如活了一辈子,在某一个时刻,能在电影里留下来这么一个片段,他就永远留下来了,这是有意义的事情。”这种被留下的渴望,恰恰就是我们过去一种所忽视的,这些被区隔在黄土地的漫天黄土里的最普通的人们对于被记录的渴望。这也是为什么,快手和抖音里,会有那么多普通人注意到了这部电影中只有海清一个“明星”,因为对于大部分的普通人而言,他们都同样有着这样被记录的渴望,他们同样想被看见,且希望抬头看向银幕里的人时,被留在那里的人,是和他们一样的普通人。而这种互文,至少构成了一种尊重,一种对于想留在影像里被记录的人,一种对于吸饱了水的黄土、在烈日中升起的由土地垒砌的屋厦的朴实的尊重。在李睿珺的口中,老四和贵英是两个属于农业1.0世界的人,他们是两个遗留在农业1.0世界里的、无法离开这片土地的留守中年人。如果有一天,老四和贵英从这片土地上消亡了,那么也意味着农业1.0的时代结束了,这种结束,不仅意味着房屋的坍塌,更意味着一些固守的东西也烟消云散了。这些年,中国的乡村在发生剧烈的变化。有一些村庄的消失,也许就是从村口一棵百年老树的消失开始的,那是一棵曾经需要几代人站在一起才能够环抱住的大树,就那样在工业化的进程中被拦腰斩断。从一棵树开始,到村子里任何能够出走的人,村子的消亡是显而易见的。那些从村庄里出走的人,像无数条涓涓细流,就那样无声无息地汇入城市的洪流中去,他们隐匿在城市的各个角落里,呐喊的声音却无人倾听。在数字转向的进程中,我们之中的许多人,似乎都离开了土地,离开了土地的秩序。可是这样,我们是否就摆脱了大地的沉重真相和它的变幻莫测?精神、行动、思想或者真相,诸如此类的概念均归属于土地的秩序,在这个来自于土地的秩序逐步被数码秩序的范畴取代的时代,《隐入尘烟》总会让我想起列维纳斯笔下那些没有脸的人,这些失去了面孔的、没有社会性生存的人的特征,就是隐匿于社会,当他们彻底地消失在历史的痕迹里,他们的社会性就被褫夺了。《隐入尘烟》里的贵英与老四,就是这样两个如空气般的被褫夺了社会性的人。在戴锦华老师与李睿珺的访谈里,戴锦华老师将李睿珺对他们的记录形容为“赋予人性”的过程。李睿珺的视角,让我们看见了这两个可能被孩子们扔石块、被成年人任意笑骂的人是如何依土而生的,他让我们看见两个具体的人如何生产、怎么生活。在李睿珺的家乡——那些花墙子村里的人,和花墙子村本身,在李睿珺的电影里,成为了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一般的拥有了真实生命力与部分幻想的结合体,它是一个村庄的记录,更是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的只言片语。哪怕这种记录是有些失真和视角欠缺的,我们都无法否认一件事,《隐入尘烟》仍旧是一种稀缺且需要被看见的记录。甚至在一些时刻,透过那些过于刻板的性别视角的记录——例如那个被姐姐嫁给一个完全陌生的男性的曹贵英,那个从小被殴打致残、最后在新婚夜上沉默地面对着这一切的最普通的农村女性的时候,我们恰恰能窥见当下这片土地上仍在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些刻板的固有的,恰恰就是每分每秒都在走钟的现实世界。在戏外,许多人无法理解电影中的最后贵英生命的结束的情节设置,有人认为这是在有意塑造一个完美的受害者,认为这是一种生命的漠视。甚至连戴锦华老师都在访谈中问李睿珺,是否认为《隐入尘烟》中的人物“有点太干净了”?但一片土地上的人的精神觉醒,永远是要归因于他者的。在一些时刻,他者的负面性,恰恰让人类的精神得以存活。当我们将目光着眼于他人,开始跳脱开固守的世界以外,懂得去接受其他个体的负面性、从而懂得什么是承受痛苦的能力时,我们才开始真正有了精神。今天的我们,无论是在讨论关于《隐入尘烟》中的人物是否“有点太干净了”,还是在讨论这其中的视角是否过于刻板、太过局限的时候,至少在这短暂的时刻里,我们都站回到了一起,回到了那片最初的土地上,把目光一齐投向了老四和贵英。我们都清楚地注视着他们自我的对自然的理解,甚至哪怕是他们身旁的农具。这才是这场票房奇迹最大的意义。我们有义务看见不同境遇中的眼泪,哪怕它只是滴落在黄土地上的一滴人工泪液——因为把目光转回最初的大地上这件事,本身就已经足够具有意义了
参考资料:
1、伊曼努尔·列维纳斯:《从存在到存在者》
2、韩炳哲:《倦怠社会》
3、韩炳哲:《在群中:数字媒体时代的大众心理学》
4、韩炳哲:《爱欲之死》
5、韩炳哲:《他者的消失》
6、李睿珺:《在日常中提炼电影在电影中还原日常》
7、人物:《〈隐入尘烟〉,失语者的爱情》
8、戴锦华、李睿珺:《戴锦华对谈李睿珺:“〈隐入尘烟〉让我们看见不可见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