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美元汇率、高美元利率的周期魔咒中,新兴市场遭遇股债汇三杀。亚洲货币汇率与人民币汇率存在联动,在国内库存周期尚未切换前,亚洲货币汇率难言触底。亚洲金融危机后各经济体注重积累外汇储备、控制外债杠杆率,使得本轮强美元周期中,亚洲经济体普遍具备更稳健的基本面和更健康的外债结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重演的可能性不大。土耳其、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面临较大的基本面及债务风险,庆幸的是巴基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短期外债的比重较低。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分别拥有较高的总债务负担和短期外债比重,其风险值得关注。日本、韩国由于能源进口依赖度高,深陷于贸易逆差与低增长。房地产或许是本轮冲击中亚洲经济体的薄弱环节。韩国、泰国、中国香港地区的家庭部门杠杆率较高,地产风险需要特别关注。美元指数和10年期美债利率双双来到近20年来从未“踏足”的领域,俄乌冲突不仅加大了地缘政治不确定性,还为全球高通胀再添把火,英国养老金困境则率先昭示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身处周期的魔咒、四面的楚歌中,亚洲经济体基本面和债务情况如何?经济体系中最脆弱的一环在哪里?是否会重现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21年以来,美国从疫情冲击中恢复,美元汇率和利率开启流畅的上涨行情。2022年全球高通胀展现韧性,这使得美联储在鹰派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截止2022年10月17日,美元指数突破112,创2003年以来新高;10年期美债收益率突破4%,创2009年以来新高。高美元汇率利率的魔咒下,新兴经济体的脆弱性再次凸显。新兴经济体实际经济同比增速自2021年第二季度开始急转直下;EPFR资金自2022年起从新兴市场流出。进一步聚焦亚洲,2021年起亚洲市场广泛出现股债汇三杀,其中亚洲货币汇率在2022年年内已经自高点回落11%,接近2008年次贷危机时期的最大跌幅(12.9%),但远不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亚洲货币汇率在5个月内贬值26%的速率。判断亚洲经济体是否会发生类似1997年程度的金融危机是分析预测未来金融市场走势、资金流动方向不可或缺的一环。这部分内容我们将在本文第二、第三章节展开。中国大陆作为体量最大的亚洲经济体,其经济的起伏将很大程度上影响整个亚洲经济体的复苏,同时人民币资产也会受到亚洲市场动荡的外溢影响。一方面,国内需求是否反弹是观察亚洲货币汇率是否触底的一个维度。历史经验来看,国内名义GDP增速触底反弹同步于亚洲汇率的触底,而2010年后国内库存周期的见底要早于亚洲汇率见底。目前国内库存周期尚未切换,加之美联储鹰派加息、主动缩表的推动下,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尚未明确见顶,亚洲货币的贬值恐将延续。另一方面,亚洲货币普遍贬值的背景下,人民币难以“独善其身”。我们发现随着人民币市场化程度加深,2014年后人民币汇率同亚洲货币汇率之间呈现高相关性。计量模型显示,亚洲货币每贬值1%,往往对应美元兑人民币上行1.11%。以2014年至今的时间段进行回归,相对于亚洲经济体货币的贬值幅度,当前人民币汇率存在少许高估,详见图表 8。在图表 2中,我们择取五个亚洲货币汇率贬值到低位的时点——分别是1997年、2001年、2008年、2016年和2022年——进行横向对比,以此来考察这几轮冲击中亚洲经济体所面临的外部压力和内部基本面情况。综合考虑经济体量和金融动荡的外部性,我们选取21个亚洲经济体作为研究样本,分别是阿富汗、中国大陆、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俄罗斯、沙特、新加坡、韩国、斯里兰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泰国、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越南。外部压力方面,历次亚洲货币汇率“大底”均发生在美元指数阶段性“大顶”,而美债利率除2022年外,均处于下行波段或是阶段性低位。从美元指数和美债收益率的取值来看,当前新兴市场所面临的外部压力仅次于2001年,较1997年、2008年和2016年更大。考虑到海外面临2000年之后未见的顽固高通胀环境,美联储紧缩力度更大,叠加发达经济体利率共振上行,此轮亚洲经济体最终承受的外部压力将超过2001年。对比各经济体的股债汇市场跌幅和资金外流情况可以发现,2022年内,斯里兰卡、俄罗斯、土耳其、巴基斯坦股债汇跌幅最大,其次是菲律宾和韩国,其中土耳其股票“反常”大涨主要受“宽”货币驱动,2022年俄罗斯卢布先贬后升;其余经济体中,日本国债收益率受YCC控制而波动率有限,但股票跌幅达9%,日元贬幅超过25%;越南、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中国大陆股市跌幅也超过20%。俄罗斯(76%)、巴基斯坦(46%)、沙特(40%)、菲律宾(36%)、日本(29%)、韩国(25%)外资持有资产总市值已从2022年峰值跌超25%。本轮强美元周期中,股债汇市场相对韧性的经济体包括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印度。政策利率方面,除俄罗斯、土耳其、中国大陆降息,日本维持政策利率不变外,其余经济体均跟随美联储加息,这会加剧基本面的压力。内部基本面方面,横向对比各经济体在五轮冲击中的基本面表现,结果见图表 11到图表 18:- 实际经济增速:中国大陆2021年经济增速处在近30年来的最低值,其余经济体2021年经济增速表现尚可,增速压力最大的时期往往是1997年和2001年。
结合能源进口依赖度来看,日本、韩国一次能源进口依赖度较高,韩国、中国台湾、印度、日本等原油与天然气进口依赖度较高,这些经济体在本轮供给冲击中承受的压力要大于能源出口国。日韩经济负增长和贸易逆差问题值得关注。- 通胀:由于俄乌冲突拉升能源价格,大多经济体当前的通胀增速处于历史高位水平,其中斯里兰卡、土耳其已经陷入恶性通胀的旋涡,而巴基斯坦的通胀增速也已接近20%。
- 外汇储备:从外储占GDP的比重来看,除斯里兰卡外,绝大多数经济体处于历史高位水平,远好于1997年;中国大陆、中国台湾、马来西亚、沙特2021年外储占比不及2008年。从外储对进口额的覆盖率来看,将亚洲新兴经济体视为一个整体,其外储与进口额比值已经降至200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但仍显著高于1997年;从样本经济体来看,绝大多数经济体外储与进口额比值好于1997年和2008年,但不及2016年。
- 经常账户:阿富汗、尼泊尔、乌兹别克、泰国、土耳其、巴基斯坦经常帐恶化严重;日本经常账顺差为历史最低,但占GDP的比重尚小;其余经济体经常账户表现普遍好于1997年。
- 主权CDS:从可得数据来看,斯里兰卡的主权信用风险最高,但仍不及2008年;其次是俄罗斯和土耳其,这二者主权信用风险均位于历史高位水平;其余经济体截止2022年10月,主权风险均不及2008年,且处于几轮冲击中的较低水平,反应市场对亚洲经济体的信心较充足。
整体来看,各经济体基本面的表现显著优于1997年,这将是亚洲经济体抵御本轮强美元、地缘政治风险和贸易不确定性的“底气”。样本经济体中,土耳其、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尼泊尔基本面相对脆弱,更容易遭遇“危机”。而泰国(贸易逆差和低增长)、越南(低外储)、韩国(低增长)、印度尼西亚(低外储)的局部风险也需持续关注,详见图表 19。针对相同的样本经济体[1]、采用同样的方法,我们考察本轮冲击中各经济体的债务负担情况。结果见图表 20到图表 29:- 外债总量角度,亚洲新兴经济体中,哈萨克斯坦、斯里兰卡、马来西亚、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当前外债总额占GNI比重为历史高位水平,其余经济体当前外债杠杆率小于1997年。再考虑外债的偿还能力,除斯里兰卡外,绝大多数亚洲经济体的外债总额/外储规模处于相对低位,且远低于1997年水平。若以反映中长期外汇收入的经常账户总收入做比较,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尼泊尔、印度尼西亚的外债总额/经常账户总收入规模为历史最高值。
- 外债利息角度,外债本金高的经济体利息负担同样重,但除哈萨克斯坦、斯里兰卡外,其余经济体外债利息占GNI比重不及1997年。再考虑外债的偿还,除斯里兰卡、哈萨克斯坦、尼泊尔外,其余经济体外债利率/经常账户总收入规模远低于1997年。同时考虑外债本金和利息,外债总偿债负担(与中长期外汇收入相比)较高的是哈萨克斯坦、土耳其、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
- 外债结构角度:按部门划分,哈萨克斯坦、土耳其、泰国、越南私人部门举债较多;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则主要是政府加杠杆;乌兹别克斯坦、马来西亚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外债占GNI比重均在20%附近。
按期限划分,中国大陆短期外债占比较高,其次是马来西亚、泰国、土耳其、越南;其余经济体,包括债务总杠杆率较高的经济体短期外债的占比亦不大,这代表这些经济体短期偿债压力相对可控,强美元对其的冲击将有所减弱。考虑外债偿还后,我们考虑短期外债与外储的相对比重,土耳其、斯里兰卡短债规模超过外储,马来西亚和巴基斯坦略小于外储,其余经济体不及外储的一半。- 财政赤字方面,斯里兰卡、印度、中国大陆、土耳其赤字稍大,其余经济体基本在红线(3%)以内,且基本都低于2008年水平。
整体来看,各经济体债务负担情况整体好于1997年,结合基本面表现,本轮强美元中亚洲经济体有较大的概率逃脱亚洲金融危机的“命运”。基本面脆弱的经济体——土耳其、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同样面临较重的债务负担,但“庆幸”的是,巴基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短期外债的占比不及15%。除此之外,还需关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的外债风险,前者总债务负担相对较重,后者短期外债的占比相对较高,详见图表 30。相比较亚洲金融危机后各经济体注重积累外汇储备、控制外债杠杆率,使得本轮强美元周期中,亚洲经济体普遍具备更稳健的基本面和更健康的外债,我们发现,部分经济体当前房地产市场存在更大的脆弱性,且这些经济体在全球金融体系中也占据更重要的位置。房贷作为家庭部门信贷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BIS公布的家庭部门信贷占比指标近似可以衡量各经济体房地产市场的杠杆率水平。如图表 31所示,韩国、中国香港和泰国家庭杠杆率偏高,家庭信贷占GDP比重均在90%以上,且几乎都是历史最高水平;其次则是马来西亚、日本、中国大陆和新加坡,均高于新兴市场平均杠杆率水平。考虑利息后的家庭部门总偿债负担率(相比收入),BIS仅公布了日本和韩国的数据,其中日本总偿债负担率自2000年下降,韩国则在2000年后逐年攀升。私人部门(家庭和企业部门)总偿债负担率中,中国香港、土耳其、韩国负担较大,但中国香港当前的总偿债压力尚不及1997年。房价方面,我们使用BIS公布的实际房价指数(取2015年=100)与人口指数(取2015年=100)作商,以此剔除人口自然增长对实际房价的抬升。结果如图表 34所示,哈萨克斯坦、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日本、土耳其、中国大陆在2015年后实际房价涨幅较快,其中哈萨克斯坦和土耳其的家庭债务率并不高。UBS(瑞士联合银行)编制的房地产泡沫指数显示,中国香港当前的房地产泡沫还要超过1997年;日本房地产泡沫水平已接近1990年,远高于1997年;新加坡房地产泡沫自1997年起逐年回落。从中国香港和韩国自行公布的房贷负担率(即房贷按揭/收入)数据来看,中国香港房贷负担率已经接近1997年的最高水平,而韩国房贷负担率则在2020年后出现迅猛提升,见图表 38。此外,韩国实行特殊的“以押代租”租房政策,名为Jeonse。该模式下,租客在租期之初需要支付购房价格(折算至租期)60%-80%不等的押金,并在2年租期满后获得押金的全额返还;房东则利用这笔押金进行投资,投资收益代替传统租赁房屋的租金。Jeonse模式在韩国租房市场中的份额约50%。图表 39显示,在本轮韩国家庭部门加杠杆、房价飙升的过程中,Jeonse-房价比——即期初租房押金与房价的比值,或可以理解为另类的“首付比例”——反而在下降,这或许意味着房地产市场的脆弱性在上升。[1]考虑到中国香港地区和大陆的关系,本章节未将中国香港地区单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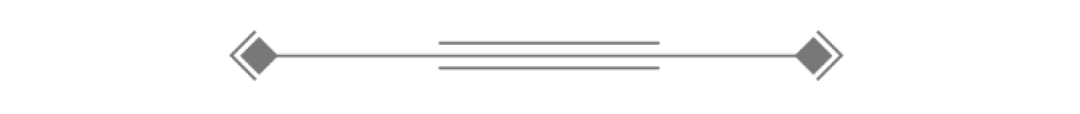
本报告内容仅对宏观经济进行分析,不包含对证券及证券相关产品的投资评级或估值分析,不属于证券报告,也不构成对投资人的建议。